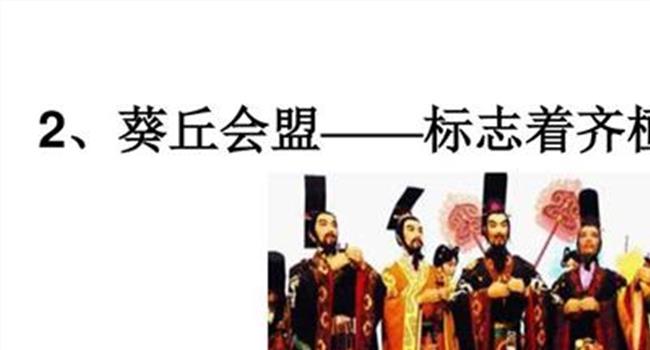【鲁仲连辞封赏】【望军专栏】望军读史记·鲁仲连
鲁仲连这个人,在战国,并不算一颗耀眼的星。我知道、关注并琢磨鲁仲连,都是因为李白—— 李白的政治悲剧和他的政治偶像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
《史记》记录了鲁仲连两个高光时刻:
义不帝秦,替赵国劝回魏国客将军辛垣衍。辛垣衍是魏王派来的说客,劝说赵王尊秦为帝。平原君束手无策——长平之战惨败,赵国元气大伤;秦围邯郸,赵国岌岌可危。鲁仲连对辛垣衍慷慨陈词,申诉了尊秦为帝的危害:不仅赵国,而且魏国、梁国,而且所有诸侯国,都将成为秦国的仆人,任秦宰割——那么,你辛垣衍也难逃此劫。辛垣衍灰溜溜地离开赵国,秦军后退五十里,魏公子无忌救赵,邯郸之围解除。

射书救聊城。燕国大将乐毅半年之内攻下齐国七十余座城,后来乐毅被燕王猜忌、免职,齐国大将田单数月即收复绝大多数失地。聊城被燕将燕冲固守,田单围困聊城一年多、久攻不下。燕冲之所以固守聊城,实在是无处可退——有聊城人向燕王进谗言,燕冲回国,极可能被诛。
久攻不下的原因,并非是兵力和战术的悬殊,而是,田单收复失地乃尽力而为,燕冲固守聊城却是全力以赴。鲁仲连写了一封信,绑在箭上,射入聊城,即《遗燕将书》。《遗燕将书》首先指出为人须智、勇、忠而燕冲固守聊城不智、不勇、不忠,然后指出齐国对于聊城的志在必得而燕冲之聊城绝不可守,接着给燕冲谋划了归燕或者降齐这两条可以建功立业的出路,最后为了打消燕冲的顾虑指出归燕有曹昧的先例、降齐有管仲的先例——逻辑严密,步步为营。
“燕将见鲁连书,泣三日,犹豫不能自决”,最后选择了自杀。田单收复聊城。
解救邯郸,平原君欲封赏鲁仲连,鲁仲连固辞不受,且辞平原君而去,终身不复见;解救聊城,田单欲爵鲁仲连,鲁仲连逃隐于海上。这两种方式,都是彻底的辞谢、避逃—— 我帮了你的大忙,我不放在心上,也不给你放在心上的机会,因此,你不必终身心怀感恩,负重前行。这是真君子。
鲁仲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鲁仲连不战屈人之兵,鲁仲连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鲁仲连“与富贵而屈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 鲁仲连有纵横家的辩才,有墨子兼爱非攻的义气,也有庄子宁做曳尾之龟的人生通达与心灵自由。
鲁仲连,大概就是金庸笔下的大侠,艺高胆大,自来自去,功成身退,飘然独立于天地间。
这形象,正是李白在《侠客行》中塑造的侠客形象:“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这形象,正是鲁仲连成为李白的政治偶像的根本原因。
天才李白有两个巨大的人生目标,功成,身退。
功成是初级目标,身退是高级目标。功成是为了在现世建立盖世之功,身退是为了在后世留下不朽之名。我们也可以说这只是一个目标,那就是——自我完成。
天生我材必有用,李白无疑认为自己是天地间一等一的伟丈夫,无须杜甫预言“千秋万岁名”,李白对自己有绝对的自信。这个动辄以大鹏自诩至死仍觉得自己是折翼大鹏、言必称三千尺、几万里的天才男人,只有“自我完成”这唯一目标。
李白也真诚,也深情,但是他的深沉和真情,既不因父母兄弟而生,也不对妻子儿女而发,甚至也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在他的诗作中长期占据一席之地——洛阳一别,杜甫终身念念不忘李白,而李白再也没有一句诗言及杜甫。不是李白绝情,也不是李白耍大牌,是李白有真情但无常情。李白如水,浩浩汤汤,变动不居,他永远在向着他认为的伟大自己奔涌而去,不会为任何人停留。
李白想要完成的自己,是功成身退的自己。
这样的自己,如果有精神偶像的话,一定是鲁仲连这样的高士。
“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李白说。
“我以一箭书,能取聊城功。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李白说。
“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李白说。
“谁道泰山高,下却鲁连节。谁云秦军众,摧却鲁连舌。”李白说。
隔着九百多年的时光,如此赤裸裸地表白,这在李白,绝对是唯一真爱。李白是什么人呀!“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与其说李白在众多的前辈中选择了鲁仲连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不如说是鲁仲连的精神言行,契合了李白的气质和追求——这个天下第一天才、宇宙第一狂人,连偶像都是他自己。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总是觉得李白特别迷醉“拂衣”这个动作。在李白的想象中,这个动作一定特别潇洒,特别淡定。这样飘然而去的感觉,几近于羽化登仙,因而有一种神异的光辉,让李白终身向往。
功成身退的人生目标,功成是第一步。李白是急吼吼地想要功成名就的,最好是立刻、马上。当然,在皇权时代,读书人所谓的功成名就,就是当官,不像现在,发个大财或者发明东西造福人类,都算功成名就。放在李白的时代,马云排在末流,朗朗根本算不上入流。士农工商,读书人算士,但还算不上官,还没有进入帝国权力体系、角逐功名利禄的资格。李白诗才绝伦,自视如此之高,怎么可能不想当官、不想当大官?
如果当道士能够让自己当官,那么他就去当道士隐居名山,唐朝不是有卢藏用之流走终南捷径而平步青云么?李白也曾在终南山晃荡一段时日。
如果干谒名流可以让自己当官,那么他就可以暂时纡尊降贵、干谒名流。但李白肯定打心眼里觉得他所干谒的名流是远不如自己的,所以你看,同样是干谒名流权贵,朱庆云说“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孟浩然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但是李白说的却是“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这口气,也是狂得没有第二了。
如果行侠仗义、重义轻财能够有助于自己当官,那么他就能够维扬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
同样,如果与官宦联姻有助于自己当官,那么他就与官宦联姻。李白的两任妻子,都是宰相的孙女,而且李白都选择了时人所不耻的方式——入赘。李白如果不是急吼吼想当官,很难解释他的选择。
在唐朝,想当官,最靠谱的是科举。但是,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有研究表明是因为家庭出身导致李白不能参加科举,而我,更相信,是李白飞扬跋扈的性格不愿意参加科举。李白愿意像杜甫一样,从一个左拾遗做起吗?不愿意。
他愿意的是像鲁仲连一样,飞书救聊城。写几句话,即可立盖世奇功,李白想想,就很过瘾。至于写几句漂亮的话,对于李白,可那是倚马可待。
他愿意的是像阮籍一样。李白曾这样赞美阮籍:“阮籍为太守,乘驴上东平。剖竹十日间,一朝风化清。”阮籍一代名士,正儿八经地上班就是在东平太守任上。这十几天,阮籍下令拆除衙门各部门之间的板壁,大刀阔斧地改革,十几天就整出了一个高效、清明的办公风气。这种干脆利索、不枝不蔓、一蹴而就,正是李白期待的官样生涯——正像他的诗歌,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一气呵成而浑如天成。文如其人,诚哉斯言!
但是,李白既没有当成鲁仲连,也没有当成阮籍。
李白生活的大唐盛世,是个大一统的帝国,普天之下、四海之滨都是李唐王朝的地盘,没有辩士、纵横家、门人食客的立锥之地,李白想像鲁仲连一样,飞书救聊城,功成而身退,无异于痴人说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李白才气纵横,但艺术幻想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幻想。幻想是艺术的情人,却是政治的死敌,不知道李白晚年流放夜郎途中,有没有想明白这一点。
据我所知,没有。
当然,李白也没有当成阮籍。假若李白真能够得到一城太守这样的职位,李白有没有可能做出阮籍这样的政绩?我觉得,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人,不可能胜任一城一县的父母官。
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李白不用面临科举名落孙山的巨大羞辱,而科举制度也不必遭遇录取大诗人还是录取政治家的艰难权衡。
状元榜眼探花郎的文章未必很好,甚至可能很烂、很臭,但是,这样的人于经世济用,大概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科举制度尽管错过了李白这样的天才,也选拔了范进这样的庸才,但我们完全不必谴责科举制度——王维、柳公权、文天祥、杨慎都是状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都是通过科举得以走上仕途。
科举制度的目的,是选拔文官。
如果用苏轼和李白对比,就知道纯粹的文人和文官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哪里。苏轼在徐州治水,在杭州疏浚西湖、在儋州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些事情,李白可能一样都做不来——其实可以去掉“可能”做不来,李白一定会做得一塌糊涂。 李白的诗才,与极端浪漫密不可分,而政治,却几乎与浪漫绝缘。
但是,李白既没有当成鲁仲连,也没有当成阮籍。
李白生活的大唐盛世,是个大一统的帝国,普天之下、四海之滨都是李唐王朝的地盘,没有辩士、纵横家、门人食客的立锥之地,李白想像鲁仲连一样,飞书救聊城,功成而身退,无异于痴人说梦。“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
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李白才气纵横,但艺术幻想毕竟不能等同于政治幻想。 幻想是艺术的情人,却是政治的死敌,不知道李白晚年流放夜郎途中,有没有想明白这一点。
据我所知,没有。
当然,李白也没有当成阮籍。假若李白真能够得到一城太守这样的职位,李白有没有可能做出阮籍这样的政绩?我觉得,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人,不可能胜任一城一县的父母官。
李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应该是一个两全其美的选择。李白不用面临科举名落孙山的巨大羞辱,而科举制度也不必遭遇录取大诗人还是录取政治家的艰难权衡。
状元榜眼探花郎的文章未必很好,甚至可能很烂、很臭,但是,这样的人于经世济用,大概是可以独当一面的。科举制度尽管错过了李白这样的天才,也选拔了范进这样的庸才,但我们完全不必谴责科举制度——王维、柳公权、文天祥、杨慎都是状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司马光、范仲淹都是通过科举得以走上仕途。
科举制度的目的,是选拔文官。
如果用苏轼和李白对比,就知道纯粹的文人和文官之间的巨大差异在哪里。苏轼在徐州治水,在杭州疏浚西湖、在儋州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这些事情,李白可能一样都做不来——其实可以去掉“可能”做不来,李白一定会做得一塌糊涂。 李白的诗才,与极端浪漫密不可分,而政治,却几乎与浪漫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