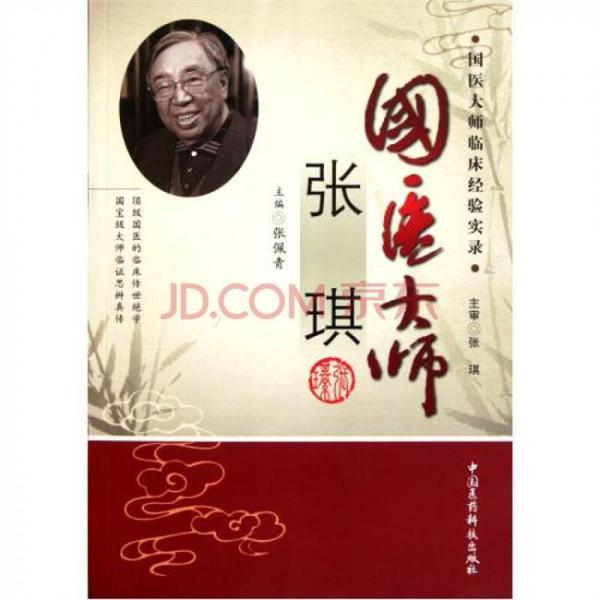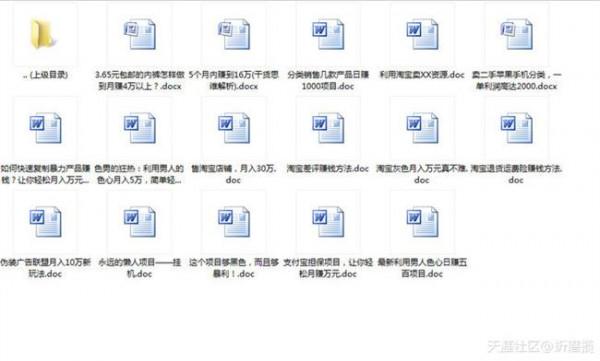【王志纲忽悠大师】"首富制造者"王志纲:不要对商人有太多期望
玩票才是最高境界,孔子说过一句话,"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才是最高境界,就是票友。
现在人们都在追求时尚、追求表面的东西。影视圈里我遇到的所有投资人都说,什么都不缺,就缺好剧本。我说既然什么都不缺就缺剧本,为什么没人去做剧本呢?这就是一个悖论,它是一个"下地狱"的活。剧本剧本,一剧之本,剧才是本,为什么没有人去做本而是热衷末呢?因为这个时代太泡沫化了,谁都想取巧,走捷径,选择光鲜的生活。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当人们都选择光鲜的生活,生活就不光鲜了。很多人都选光鲜的东西时,一个人只要沉下心来敢于下地狱,那出来了就了不得,就是稀缺资源。
80后这代人,我也看出来了,他们是痛并快乐着,乐此不疲。我儿子是个记者。春节的时候为了赶一个稿子都虚脱了,累了一两个晚上。我说既然这样你还干这个做什么?是不是很痛苦啊?他说痛并快乐,我说那就没办法了,这是吃饱了撑的。像他们这代人起来以后你别小看,当他们真正对这个乐此不疲的时候,金钱打不倒他。
当很多人所追求的名利、地位和虚荣都打不倒他的时候,可能中国就开始产生大师了。
王志纲 (摄影:吕海强)
我同商人无缝对接二十年,应该说对商人有很深刻的了解。有一天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老板说,他买了八百本《第三种生存》四处送人。我说:"这不是骂你们这个阶层的吗?"他说:"骂得太好了,骂得太绝了,骂得我心服口服啊。"这个人是谁呢?原来哇哈哈最大的对手、广东乐百氏的老板。
其实我骂这些商人并不是要彻底否定他们,只是要剥掉他们的外衣,把他们的本质讲出来。最后我还是肯定他们的,肯定商人的力量和商业的力量。他们冷酷、他们理性、他们追逐利益、为了利益可以六亲不认,但在最后其实是推动了这个社会的前进。你可以不当商人,但你要理解商人,而且你要善于跟商人共处,"与狼共舞"。
商人是个很功利的群落,你不要指望和他们成为朋友,他们只有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才会来求你,没有困难他求你干什么?每天有多少人簇拥着他?他们的骨子里是想当百兽之王的。每个老板的心里都有一头熊在咆哮,都想当狮子王,特别是那些所谓的行业大佬都想称王称霸。
"万般皆下品,唯有老子高"。大家都围着他转,凭什么他们要拜在你王志纲面前?凭什么像刘皇叔一样三顾茅庐?凭什么把你称为"王老师",围着你转?因为你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记得我那本《第三种生存》要出版的时候,一个部下说你这样得罪了所有客户,生意还从哪里来?我说我之所以敢这么写,是因为我是稀缺资源。商人是很实际的,马克思早就说过,"有百分之十的利润,资本就蠢蠢欲动了;有百分之百的利润,资本就忘乎所以了;而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那么上绞刑架的事都干得出来"。
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们是会算这个帐的。黄文仔的北京星河湾项目我取了多少?记得项目成功后他请我吃饭,我打趣说:"黄老板,你真是商人啊,我们辛辛苦苦帮你三年把这个项目做成了,你赚了大钱,而我从你这里收的钱为买你的房又让你一把赚回去了,什么财智时代啊,做梦呢,那是文化人自己宽慰自己的,还是财富时代、商人时代"。然后他就哈哈大笑。
金钱只是一个结果,三百万、五百万是无所谓的,那个时候黄文仔天天陪着我打高尔夫球。我把他的公园搞成了迷你高尔夫球场,他成天陪着我。为什么要陪着我?这就是商人的特点,只要你能给他赚到利润。但是一旦商人成功以后你赶快走开,他不找你你就别找他。
过河拆桥是商人的本性。很多人作怨妇之状,我觉得可笑。如果你有这个本事就继续前进,走在他的前面不就行了?
我对人性看得很清楚了。有句话传得很广,"我们是火箭送卫星上轨道",十五年前我就说过这句话。哪个火箭把卫星送上太空之后还抱着卫星渴望和它一起在轨道上运转的?那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你的任务就是自动脱落。
你知道王健林是怎么找我的吗?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刚开始我不想理这个事的,还跟我攀老乡。我说:"我们怎么是老乡呢?"他说:"我们都是四川人吧"。我回答:"我不是四川人,我是贵州人"。他又说:"听说你爸是四川人"。我说:"对"。他说:"那就是老乡嘛!"后来我去了他的万达广场。商人是考虑得很周全的。他把几个大老板都请来了,黄光裕、郭广昌、还有泛海的卢志强。
王健林这个人很厉害。当出现根本性问题的时候就会撇开所有的一切,直接自己来解决。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说:"志纲兄,我可以先打几百万过来,咱们把事情做了,我们以后还希望合作三年五年"。后来还出了一个笑话,我们的财务傻乎乎的,天天追我,说是要把发票给人家,不开发票这个钱就是不义之财,没法做帐。
搞得我三次问王健林:"财务怎么天天追着我说要给发票?"王健林问:"什么发票?"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事后才反应过来,王健林为了加快项目节奏,摆脱大企业病的低效,从自己的私人账号直接打出来的钱。
这很有意思,商人的成功是有他的道理的,平时他可以睁只眼闭只眼,但是关键问题上自己肯定要把握。
我从来不指望商人感恩,哪有什么感恩?我只唱《国际歌》,不唱《东方红》,这是贯穿我一辈子的哲学。国际歌是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东方红》就要倚仗于"人类的大救星"。
要不断地领跑、不断地超越,慢慢地就会在江湖上形成一个神话。
我坐在这里,老板大多会过来拜访我,我原则上不会去老板的公司跟他们见面。他们每次过来都问:"找你们太难了,怎么像搞地下工作一样?";"你们怎么不把买卖开大一点?是怕钱砸你吗?"他们就是不明白,我基本上就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你愿意来,我经过甄别以后确认你这个人能扶得上墙,大家又很愉快我就跟你合作。如果不是这样,在商言商我毫无兴趣。
二、要独立、要自由就不能发财?
我当记者的时候人家叫我"记者王",当时名声的确很大。我认识很多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的大佬,比如健力宝的李经纬、白云山的贝兆汉这些顶级企业大佬。
离开新华社之后,有两年是很痛苦的过程。就是高台跳水转型。
我决定离开新华社的时候,有段时间天天在广东从化骑马荡舟吃野味。那段时间心里是很痛苦的,我在寻找我的下一个生活方向。大的方向没有变,但是具体的方式变了。我的自尊心太强了,我离开新华社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传,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说王志纲原来那么牛就是靠这个牌子,离开这个牌子他就完了,甚至有人断言以后我还会用新华社这块牌子招摇撞骗。
为什么叫做"王志纲工作室"?我的自尊心强,特别敏感,既然离开了就一刀切,就用"王志纲"三个字,跟之前没有关系。到今天为止跟我打交道的百分之九十九老板,根本不知道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历史,我也不想讲。
当时离开的时候给自己设计了一个头衔,叫做"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市场策划人",三位一体。有一次我拿名片给一个老板,那个老板看了之后就说:"要独立、要自由、要发财,哈哈,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不当孙子能发财吗?"但是现在我见到他,他就说"王大师啊,你是对的,要独立、有自由、得发财,哈哈!"。
我离开新华社跟碧桂园的杨国强合作三年告别的时候,他说了句话:"王老师,我们两清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们谁也不欠谁的了"。包括都说好了碧桂园学校给我的孩子是免费的,后来也变卦了。一事一议,决不记情,这就是商人。
就是这种力量刺激着我,我后来帮助星河湾,杨国强又要重修旧好。我就扔下这么一句话:"要珍重知识,敬畏智慧"。
所有的商人都是功利的,昨天你的利用价值是记者,他认识的是"记者王",你能呼风唤雨,能给他省掉广告费,这是很实际的。他的失误在于不知你废了新闻武功后还能再生出其它功夫。
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来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从来不拣便宜。当然,还要自身功力强。
我很感激这个时代,我活一辈子相当于别人的几辈子。我爷爷以前是大士绅,我爹大学毕业从事文化和教育,其实我是把几千年承上启下的都经历和跨越了。
说得难听一点,我们这些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在为时代承上启下,通过承上为后来的人启下,也让他们少走弯路。说得好听一点,可能五百年以后我们的故事也是个传奇。今天单单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别人听,别人都不相信,编都编不出来,等到五百年、一千年之后,那是多精彩的故事啊。
我非常讨厌别人把我当商人看,这一点上我很敏感。就是那句话,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从这一点讲我不是商人。商人应该是利益最大化的,这才是商人,我不是。
我想做的是战略思想库。中国人搞战略思想库,一类是纯粹照搬美国模式,但在中国没有市场。因为美国的战略思想库是不需要挣钱的,有美国的大资本家支持和国家委托。中国人学的结果就是养不活自己,死掉了。另外一类就是纯粹市场化的机构,但是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纯粹得看别人的眼色行事。没有角色独立哪有科学决策?
你可以说我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但是我们在探索一条道路。我的兴奋点还是在于宏观和中观的问题,是比较超前的战略性问题,要植根于中国的现实。我们肯定要有委托,委托人有可能是商人,也有可能是国家和政府。
这二十年让我感觉最自豪的是,前十年我教会了老板购买知识产品是要交钱的,而且还要交大钱;后十年我教会了政府购买知识产品是要交钱的,而且还要交大钱。我们的委托人包括很多省市一级的政府。全中国都开始懂规矩了,这也是我们做的贡献。
我们的战略研究院也在研究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和模式。我就发现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觉得洋人的东西就了不得。我觉得基辛格说得非常好,美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在于美国人是下国际象棋,中国人是下围棋。国际象棋每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中国人不是,下围棋只有最后收盘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胜负。
中国需要很多创新和创造,直接从国外移过来是不行的。迈克尔·波特的理论在美国那种定量化的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位是有存在价值的,但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就会出现问题。波特自己的咨询公司不是也垮了吗?
中国人不是这样的,中国太复杂了,中国是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行驶,有没有规律?有,但绝对不是美国人的规律,这是我们跟他们最大的差别。
中国以后真正的奢侈品洗牌就要开始了。中国的奢侈品从哪里破题呢?陶瓷估计是个重要的突破口。
我们有句话叫做"非新勿扰",不是新的你别找我,因为是新的,大家都很陌生,我们反而具备了优势,因为你总是在准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当记者的时候,很多建议受到了中央的重视,包括关于特区的完善、关于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与冲突是怎么回事。当时觉得自己是个专家。但是等到二、三十年回头再看,开句玩笑,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写戏的人是骗子。
如果人生是个舞台的话就是这样。那你是什么呢?我说我曾经当过写戏的,也当过傻子,但现在我是一个舞台监督,我站在第三方可以全部看清楚。舞台监督从演员的演出到观众的表现再到写戏人的效果一目了然。原来也不是记者当得不好,而且当时都是很有针对性、很积极的,但那个时候的成就感是很简单的,只要是被采纳、变成中央文件,革命就成功了。但其实离最后的改造还有十万八千里。
我的印象很深,当时的总理说过一句话,"学者总想使他的研究成果被政治家采纳,从而流芳千古,而政治家却要为后果负责任"。
一个记者一定要永远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如果不好奇就干不了这个行当。现在手机上的微博、微信我也在了解,就是一种好奇。另外要保持一种哲学家的思辨,还要保持一种历史学家的理性。我们不能听到风就是雨,严谨很重要,所谓大胆想象、小心求证。
三、整个中国很好玩,我们躬逢其盛
如果精英指的是鲁迅所说的"民族的脊梁",这种人应该是在企业家当中。任正非这些人是了不起的,虽然我担心他退任之后,华为能不能延续下去。尽管我不是很喜欢他,但这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另外一个搞实业的人,李书福,他能够颠覆国有企业几十年都做不好的汽车业,甚至把外国企业收购了,是很值得钦佩的。还有哇哈哈的宗庆后这样的老知青,一个骑板车的能通过做水做成中国首富。
有些商人,我开玩笑说, "掌声响起来",他很害怕没掌声,他是为掌声而活,生怕你忘了他。就是营销、营销、营销,通过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效果。
"作品"是什么? 有些人想追求完美,希望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再出来作品,我是一边走一边唱。先完成,再完美。现在我已经出了十五本书,在我看来这十五本书都是建筑材料,等到一定时候我就有条件盖这个房子了。至于房子怎么盖,现在我是五十八岁,距离六十五岁还有七年,这七年时间里我就在过渡,不断地超脱,让我的员工成长起来。
中国的八十年代太有趣了。它很贫寒,但不贫穷。衣服是有穿的,饭是有吃的,但是穿不好吃不好。每个人的精神都非常丰富。山也美水也美,那是一个充满憧憬的理想主义年代。邓小平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给了舞台上的所有人一种可能,去展现自己、去释放自己。
那是一个纯真年代,很伟大很纯真,都渴望中国好,只是早产而已。那时人性没有现在释放得这么充分。现在这种人性释放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那时每个人都很美好,虽然纯真,但是幼稚。
九十年代是一个泥沙俱下的年代。所有的人都失去了方寸,这是很好玩的。特别是邓小平南巡之后。
"九二派"算什么?什么叫下海?我才叫真的下海,我下海是不系安全带的,光着屁股跳下去。有些"九二派"是先把船打造好了,这边下海那边就上船。还有些人是想当官的,后来碰了壁当官无望被迫下海。真正的下海是高台跳水,我们就是这样的。
不过九十年代也挺好,每个人都在探索,特别是整个中国面临"知识分子商人化"。1993年之后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很有意思,中国很多人淹死了,很多人逃回岸上来了,包括《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很多下海的,最后都逃上来,求爷爷告奶奶请求组织把他接收回去。
整个中国是很好玩的,我们是躬逢其盛。
现在的社会都是浅薄化、平面化的,追求的是一瞬间爆红。这是转瞬即逝的,包括现在"中国好声音"也罢,湖南卫视搞的那些东西也罢,节目成功,得到一些票房但很快就会过去。这个时代的确是个易碎品时代。
中央电视台请我去跟易中天对话,我是作为神秘嘉宾出场的。我一出来他就说:"哇,志纲兄,是你啊!"我就说"老易啊,你用不着再问我怎么赚钱了吧?"我之所以如此调侃是因他在未爆得大名前,一次在论坛上曾对我说:"志纲兄,你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啊。"随后问我怎么才能用知识赚钱。
人海茫茫,大家都是黑暗中的舞者,照射的灯光就是名利之光,当它照到谁的时候观众就看到了他,这个人就是明星。但是灯光是会移动的,被灯光照亮的可能是幸运儿,没有照住的可能就是失落者。在这个过程中,当灯光要转换的时候,瞬间照到一个周杰伦,可能在黑暗中舞跳得比郭富城还要好,灯光要移走的时候台下的观众不干了,"不准不准",灯光只好把她锁住,一个明星就如此诞生了。
这是舞台、灯光和观众的关系。大家都是明星,有些人就变成了流星,有的人就变成了恒星。流星本身有幸运的因素,但恒星是必然的。
我跟易中天说,中央电视台是一个超级名利场,也是一个卫星发射台,这里每天都在把各种动物发射到太空上去,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还只是猴子,你却成了齐天大圣?
我看到易中天一夜成就大名的时候就为他捏了把汗。因为我是过来人。我曾经一夜获得大名,后来我消化这个大名用了五六年。当一个人一夜成名,这时候其实是骑虎难下的,他有点超前透支了。就看你能不能成为恒星了。
所有的人恭维你的同时也会对你寄予更高的、甚至是神话般的期望。也有人会攻击你,无形之中你增加了很多对手,恨不得把你打死。很多人是一夜成了大名。如果他能够消化得了就是个幸运儿。
碧桂园最红的时候,名利巨大,分赃者蜂起,我自然成了拦路石。一些人要打倒王志纲,有人甚至说我对碧桂园是贪天之功,好像都是他们做的,我只是拣了便宜一样。这些被炒作多了,就逼着我进行"星河湾之战",告诉健忘者和被误者。
想到钱我脸就红,嘴巴都说不出话来。你不知道,我是从来不谈钱的,就是"你看着办",都是这样。到现在我还有这个毛病。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派手下去谈判。他们就说:"王老师从来不谈价的,我们来谈",就是这么分工。这一关我还没迈过去。
一个商人向往成为文人是个好事。
做地产的人是脚踩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更多的是社会大学,更多的是和制度打交道的能力,长袖善舞,需要更多的是社会阅历,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你们说的那三个做互联网的巨头反而像试管婴儿一样,更多可能是在一个相对单纯的环境里面做事情。这是他们最大的不同。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果讲他们当中有个承上启下的人,那就是马云。这个人真别小看,牛头马面,虽然他形象怪异,但是不可小觑。这有点像人类社会从冷兵器时代到了热兵器时代,前面那些做地产的是冷兵器时代的高手,个个身怀绝技。然后突然冒出一批洋枪队。你武功再高,也奈何不了大炮子弹吧?他们完全是两种企业家。新一代的企业家动不动就买飞机买游艇,你说老一代的怎么会想去玩这些东西?
它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问题。不是玄学,是我们阐释它的时候叫它玄学。其实它是有规律的。比如全球化,风水轮流转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变成了优点,包括我们讲的人口红利、后发优势,包括人民改变命运的冲动,所谓的聪明勤奋勇敢这些东西。
但是也把人的另一面唤醒了。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只求吃饱不求吃好的水平。因为中国这个国家没有殖民主义的条件,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传统。但是在这三十年来,邓小平把中国人几千年压抑的妖魔放出来了,就是贪欲。由于贪欲,中国迅速地发展到今天,但是贪欲所造成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了。这个平衡点要怎么找?从大历史来看我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从小历史就很难说乐观不乐观了。
中国这个国家不能用零和游戏的角度来说,"是"还是"不是"。它有前提条件,你把前提条件设定好了才能谈这个话题。这个东西不是玄学,也不是诡辩。谈问题不能说简单的"是"或"不是",而是要一分为三。我经常找到的答案都是在"是"和"不是"之间。
现在这个时代人们都追求短线,这是最大的问题。要问我人生最大的经验,真的就是傻瓜哲学。我遇到过很多聪明人,跑得特别快,就像飙车一样,结果跑得距离最短。因为他在方向未明时就开跑,定是在断头公里上。我是很笨的,为什么走得远,因为重视目标,所以基本上没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