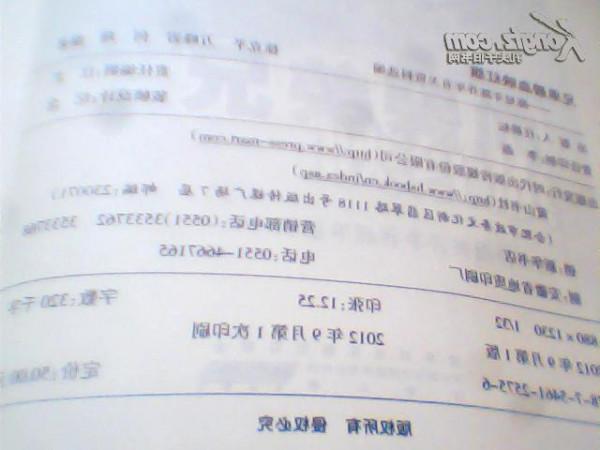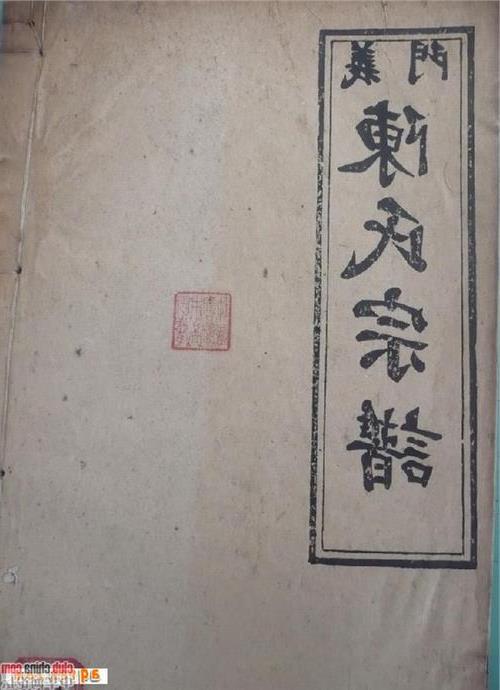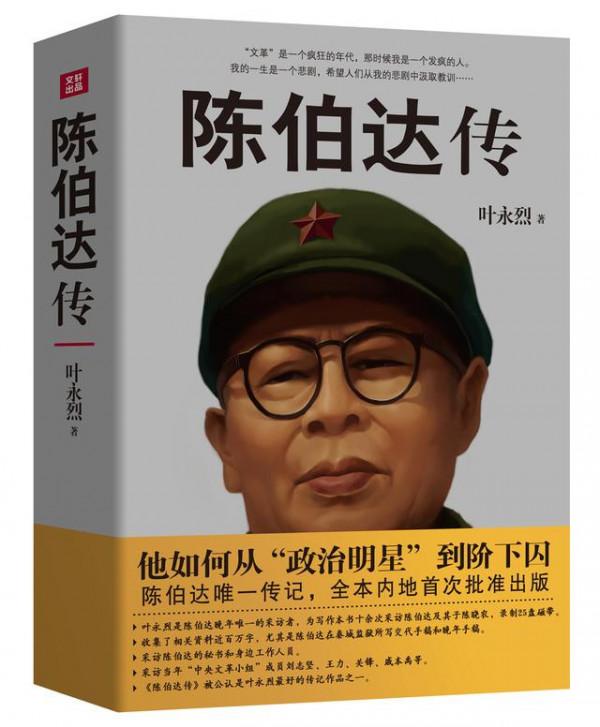陈长捷后代 陈长捷黄剑夫离世
为了躲避造反派的骚扰和侵害,宋希濂和杜聿明躲在了家里。可是,自从居民委员会也成立了造反派组织,这个办法就失效了。那天,宋希濂与杜聿明合住的四合院里突然闯进来几个造反派,其中一人张口就问“谁是杜聿明?”杜聿明正在院里干木匠活,听见有人问话,立即放下锯子,摘掉眼镜,“你们找杜聿明吗?我就是。

”造反派们打量着对方的汗衫、围腰以及卷起来的裤腿,异口同声道,“你不是,你哪像国民党头等战犯,你是给杜聿明打家具的。
”造反派们转向身着白衬衣、蓝裤子、黑皮鞋的宋希濂,其中一人说“看来你就是杜聿明了。”宋希濂来不及答话,就被人左右开弓狠狠抽了两耳光,杜聿明箭步上前,“我是杜聿明,你们凭什么打他?”“你这个臭木匠,胆敢包庇大战犯?”造反派边骂边踢了杜聿明一脚,宋希濂见状不妙,立马又站到杜聿明前头“你们要打就打我吧,我是杜聿明。

”造反派们围住宋希濂,个个摩拳擦掌,正欲大打出手之时,院外进来几位民警,好说歹说总算把造反派们请出去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文强还在功德林战犯改造所里。自觉获赦无望的他开始特别思念已经去世的两任妻子,而第一任妻子周敦琬留给他的那份遗嘱,尤其让他刻骨铭心,没齿难忘。

这是一个戏剧性的往事,抗战之初,上海沦陷后,文强以军事委员会前方办事处处长的身份,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那日晚上,刘姓参谋向他报告说,这里发现了一个中心学校,里面有个女教员叫葛世明,复旦大学毕业,现在学校停办了,她没有工作,没有钱,有钱也回不了已被日军占领的宁波老家。

出于怜悯。文强见了葛世明,给了她路费,让她去长沙找自己的妻子周敦琬,给她安排一个教员的岗位。长沙失守不久,周敦琬病故,文强远在上海,来不及回老家奔丧,以后调回重庆,见到了周敦琬的大姐。
大姐告诉文强,周敦琬重病期间,一直有葛世明精心照顾,晚上伏在病榻打盹,白天还要料理两个儿子吃饭上学,累得骨瘦如柴,非人非鬼。大姐交给文强一封信,这是亡妻留给他的遗嘱,里面写到“天底下再也没有比葛世明更好的女人了,我死后,你一定要跟她结婚,把她留在我们家,把她养得胖胖的,再为你生儿子。
”于是,文强娶了葛世明。还在在洛阳为她盖了一幢大房子,她在那里生活了六年,为文强生了三个儿子。
国民党政权垮台前夕,葛世明带着儿子去了台湾,文强在淮海战役被俘的消息,葛世明是在台湾收听到的,电台广播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按照国际公约,国民党将领的生活待遇与过去保持不变。听到这里,葛世明毅然带着儿子,趁着天黑,连夜离开台湾回了上海。
上海市市长陈毅既是文强在淮海战场上的对手,也是当年革命生涯中的朋友。那时文强随朱德的部队到四川,他是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而陈毅是师政治部的宣传干事。得知葛世明到沪,陈毅亲自作了安排,首先把没收了的文强私宅发还给葛世明,然后安排她去立信会计学校当老师,还介绍她加入妇联,加入中英友好协会。
可在1953年开始,中国有个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关方面派人冲进葛世明正在讲课的教室,当众宣布她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然后五花大绑,由来人押走。葛世明没有被押进监狱,对她实行监视居住。居住了一年半左右。1955年春天,当有关方面派人再次前来索取交待问题的材料时,发现葛世明已经在拧开的煤气罐旁自杀身亡。
让文强痛心不已的是,葛世明自杀被人发现后,在急救站里人还活着,可是医生请示医院领导时被告之不予抢救,因为国民党战犯家属兼“潜伏特务”的必然下场就是自绝于人民。
文强在秦城精神萎靡,沈醉在外面却是忙得不可开交。自从《文史资料选辑》22、24辑分别刊登了他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保密局内幕》,然后由群众出版社将这两篇文章合成一部单行本公开出版发行后,但凡涉及到军统特务的机关问题,便会有人登门拜访,找沈醉提供材料。
每天有十几批,每批有三五人。由于住房面积小,屋里坐不下,许多人便站在门外排队,人多的时候,从楼梯过道一直排到院子侧门。文革中有个名词叫做“内查外调”,所谓内查,就是各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时,要把有历史问题的人查出来;所谓外调,就是各单位派人外出,找到相关的人,去核实问题的真假。
与沈醉打交道的,便是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外调人员,虽然军统特务有数万之众,沈醉认识的不及十分之一,但他还是硬着头皮,热情接待,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直到粉碎“四人帮”,沈醉才在他的《我这三十年》里,披露了当时的无奈与烦恼,“1967年夏天以后,大部分找我写材料的人,都不再通过政协而是直接找上门来。他们当中,有的是真想把别人的情况弄清楚,以便正确地作出处理,有的却是想通过我来帮他们去打击诬陷一些与军统无关的人;也有的是明明过去与军统有关系,却想通过我的证明给予否定。
总之,各种各样的人怀着不同的目的而来。老实说,找我写材料的人,绝大多数态度很好,但也有极少数的人,简单粗暴,不讲政策,不近情理,特别是带着某种目的来强索材料的人,引起我的反感,彼此发生争吵,甚至闹到动武的程度。”
一次,来自外地的几个外调人员,把一份事先写好的材料,放在沈醉的案头,要求沈醉照抄一份,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沈醉摇摇头,“我有罪,但不会嫁祸于人,所以干不了你们交办的事。”来人大吼一声,“你干脆我们也干脆,走,现在就跟我们走!
”沈醉点点头,“好呀,北京住久了,闷得心慌,正想到外地走走。”说完,他打开房门,对在门外排队等候的众人说,“他们叫我现在跟他们走,你们就改天再来吧。”一群人冲进屋内,把那几个外调人员团团围住,吵吵闹闹,推推搡搡,沈醉却乐得闭目养神,呷了一口沈美娟端来的热茶。
沈美娟是前几天才从宁夏回到北京的。她所在的兵团开始有人写她的大字报,批判她不忏悔,隐瞒身份……沈美娟在宁夏呆不下去了,她请病假回到北京。继母杜雪洁也不好过,她所在的医院成立了造反派掌权的革委会,革委会下达的正式文件说,鉴于杜雪洁的丈夫是大特务,她进行阶级报复的可能极大,为了保护"革命群众"的安全,从即日起,停止她护士的工作,改为保洁员,负责清洗病房的床单,打扫病房的厕所。
杜雪洁每日回家,除了唉声叹气,还不时把怨恨发泄到沈醉身边,“嫁给你这种人真是倒霉,倒了八辈子的霉!”
近来有几位获赦人员相继离去。溥仪死了,死于膀胱癌;康泽死了,死于脑溢血。陈长捷死了,死于非命。陈长捷离开前夜,红卫兵冲进了他的房间,二话不说,举鞭就抽,痛得陈长捷在地上打滚。适逢他的儿子出差在外,老伴无力制止,只好跪地求饶,可是伴随着她凄楚衰鸣的,竟是几个红卫兵的哈哈大笑。等到红卫兵们扬长而去,陈长捷大哭不已,“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在监狱呆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放我出来呀!”
陈长捷之死,给邱行湘以沉重的打击,也给了他明显提示。于是,邱行湘先让妻子张玉珍把五岁的宝贝儿子邱晓辉带回娘家,再请潥阳老家两个身材魁梧的亲戚来南京暂住,所以,此时此刻,当红卫兵破门而入,冲进屋内的时候,邱行湘索性主动迎上前去,双方稍有僵持,红卫兵看见客厅坐着两个彪形大汉,不得不后退了,虽然边退边喊“邱行湘,你着到,老子明天还要来!
”邱行湘关上大门,苦苦一笑,喃喃自语说:这只是权宜之计,没有办法的办法,过一天算一天吧。
邱行湘在南京躲过一劫,在重庆江津的黄剑夫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劫难。他被红卫兵弄来游街,而且走在“地、富、反、坏、右”的前面,边走边敲脸盆,以示鸣锣开道,仍被当地的造反派视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个成果。
!随着这种“成果”的增多,黄剑夫的罪名也加重了,起初站在东门广场台上挨斗时,脖子下面的吊牌写着“大军阀”三个字;以后武斗爆发,这里兵工厂生产的登陆艇、水陆两用坦克全被派用上了,造反派当中的两派在长江边上打了一仗。
这一仗打下来没过几天,黄剑夫的吊牌上面多了三个字,“黑后台”;最终“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强加在黄剑夫的头上,使他失去了自由。黄剑夫被逮捕后,在县看守所里遭到连续几天的严刑拷打,直打到人事不省,奄奄一息,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人才被送进县人民医院抢救。
抢救无效之后,看守所军管人员通知“现行反革命”家属来医院处理后事。邱行珍来了,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来的,但是知道黄剑夫走的时候穿着一件干净的白衬衣。
现在白衬衣脏了,除了好些汗渍,还有好些血迹。邱行珍问这是怎么回事?“我没有时间跟你啰嗦!”军管人员疾言厉色道,“鉴于死者黄剑夫系现行反革命,我代表军管会,现在向你们家属宣布三条规定。第一,不准开追悼会;第二,不准戴黑纱;第三,不准哭。此规定如有违抗者,一切后果自负!”
下期预告:黄剑夫去世后他的家人如何生活?有哪些遭遇?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