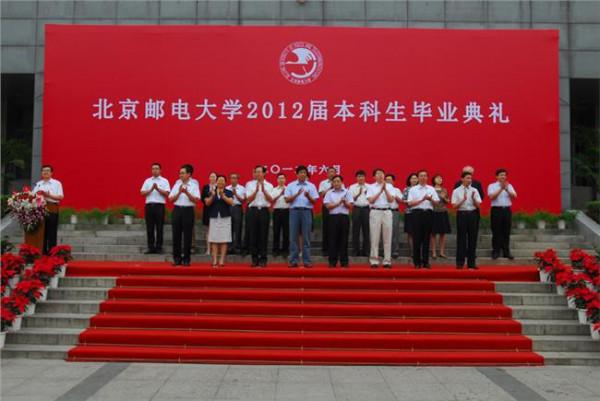上海理工大学工作40年杂记
2006年,上海理工大学(追溯到沪江大学),将举行百年校庆纪念。校庆筹备会叫我写篇稿,盛情实在难却。的确,在目前还在职的教工中,我算是校龄最长的了。从1965年我来到此校,已经有整整40年,回顾往事,感触甚多。我40年的“创业”就是在这块土地上。
写杂记就一定要涉及一些人和事,可我的记性又特别差,只得翻阅历年的记事本。可惜有些记事本找不到了;有些事又没有详细记载,甚至一个字也没有。因此,此文中凡有确切日期的事,大概没有大问题;其余的人和事就很难保证不错了。反正这是“杂记”,又不是“档案”,我想不必太认真了;否则就无法下笔了。写杂记总要有点议论,或者写点感想,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一)进校不久就遇上“***”
我1956年进入清华大学,读了五年半制的本科。62年2月份毕业留校,后考了研究生,又读了三年。我们这一届可能是解放后首次通过考试招收、国内培养的研究生。1965年我完成研究生论文后,王补宣老师(后来评上学部委员)告诉我,学校“分配”我到上海机械学院去工作。
当时高教部规定,那年清华毕业的研究生一个也不许留校,全部由国家统一分配。第一机械工业部,通过高教部,向清华大学要一个学“热工”的研究生,到该部所属的上海机械学院工作。我同专业的这一批研究生共3人,另外2位是张政和范天民,因为他们的研究题目较大,拖到66年***开始,67年才分别被分配到兰州化工机械研究所和兰州化工研究院。
1965年7月,我到学校来报到。这个学校,从1960年起,引来了大量新人、强人。当时学校有二个系,仪表系被称为一系;动力系为二系。60年前,动力系老教师有龚洪年(锅炉界的元老,2006年将是他诞辰100年、冥辰20周年)、楼惟秋(气轮机界的元老,40年代留美);较年青的有中央大学48年毕业的陈之航和上海交通大学52年毕业的顾景贤等。
60年初,进来了一大批精干教师,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王乃宁、李燕生、林俊灿、徐昂千;哈尔滨化工设计院的茅以惠;西安交通大学的卓宁、叶振邦、张昌煜;哈尔滨建工学院的赵学端、沈承龙、钟声玉;清华的沈炳正、周启瑾、刘正武等。还有搞机械的吴崇德、殷鸿梁、唐金松(70年代,殷、唐调往上海工学院的机械系;而上海工学院的蔡祖恢、李美玲调至我校的动力系)。
这些人都是50年前后毕业的,30-40岁,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业务又很强,因此动力系发展很快,在国内地位迅速上升。同时也有些“文人相轻”,相互都不买帐。用上海话讲都是些“魁兄”,存在着矛盾和竞争。
与我相近时期进动力系的也很多,有哈工大的伍贻文;西安交大的张志刚、孙家庆、陈祖耀;清华的陆龙云、黄希程;北京工学院的丁一鸣、贺镇华;中山大学的廖其奠;华东化工学院的余国和等。
这样的师资队伍,在国内是很强的。尽管当时还没有似今日这样明确地提出“人才建设”、“师资队伍建设”,但可以看出当时的学校领导办学的指导思想是相当明确的。那时的系主任是龚洪年和楼惟秋;总支***是孙万宜和沈长荣。他们对新来的人相当了解。大概他们觉得我刚来时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翘尾巴。
有一次,沈长荣和我谈话,很清楚地讲出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做了那些工作,还有那些工作没有做。这件事确实让我很惊讶,一个工农出生的党务工作者,竟能对系里教师的业务情况了解地如此清楚。也许这也是当时动力系蒸蒸日上的一个原因。
的确如此,我在清华的研究生论文是研究含氨混合气的导热系数(后称热导率),这是化工部有关合成氨反应塔的题目。我做了理论分析,找到了计算方法,计算了各种组分在不同压力和温度下的导热系数;建立一个测试导热系数的实验台,对单组分气体作了实验。由于当时的条件限制,没有做不同的组分配比。即使在40年以后的今天,是否能在1毫米的间隙内保证混合气的组分,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其实在当时的条件下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1965年7月,时任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在大会说,“清华毕业的研究生水平要高于苏联的副博士”。可是到了80年代后期,上面传达,苏联的副博士水平相当于美国的博士,在填表时可以填“博士”。
而我们在清华的读了9年书,却什么学位都没有。1988年,我曾经找过时任清华研究生院院长的过增元(后来评上院士),希望补我们学位证书。他也向上反应过,但有的领导说,“您们已经是博导了,还要博士学位干吗”。真是的,连学位和职务都分不清楚。
1965年我进的是“热工和工业热工”教研室,当时的室领导是蒋能照和徐昂千,是徐昂千从清华把我要来的。第二年,***就开始了。基础教研室被取消,我被分配到锅炉教研室。锅炉教研室中的陈之航是***中被斗得最厉害的一个。除了出身、经历外,“顽固”是他挨斗的重要因素。后来他被罚长期打扫厕所,做得很认真。至今他还经常讲起他扫的厕所,比现在某些清洁工做的,要干净得多。
我们属于年轻的,没有被发现有什么大问题,加上地处上海的机械学院,也远没有在北京的清华那么“左”,所以还没遭大罪。虽然我也被莫名奇妙地抄过二次家,但仍算是“可以教育好的”,被派到吴泾热电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当时正在建设国内第一台12万5千KW的发电机组。
我被分配热工班,为高达数十米的锅炉铺设测温用的电缆线,经常搞得满头大汗、浑身是灰。工人们看我们干得既辛苦,又很不错,常表扬我们。那时,一有毛***的批示,如“七二一”、“九五”批示,都要组织游行,报纸要组织稿件,大加宣转。
有一次,解放日报、文汇报已拟好稿,准备将我作为“可以教育”的典型加以报道。文中写道,“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上海机械学院的华泽钊,他….”。发稿的前几天,报社到学校“政审”我的档案,发现我的社会关系“复杂”,立即取消此稿。我当时吓得要命,幸好后来学校没找我麻烦。原因可能是学校里“牛鬼蛇神”太多了,我只能算个“小巫”;要么就是学校干部“严重右倾”。
按当时的观点,我的社会关系确实是“复杂”的。解放前夕,我母系和父系的亲戚几乎都去了台湾,后大多又去了美国。由于这些“关系”,我连进上海科技情报所的阅览证都办不到。当时,申请办情报所阅览证,是需要经过政治审查的。其实,科技情报所里有的只是些国外的期刊和专利而已,不知为什么要对国人保密。
我刚到学校,在热工教研室,跟着徐昂千做换热器的传热试验,是上海气轮机厂的题目。(这个厂校合作的关系搞得很好,一直保持到现在。)***开始,我被调到锅炉教研室,到吴泾搞“一二五”工程。后来参加过水电部和一机部联合组织一个课题组,是研究新工质循环的电站。
这个项目是属于“机密”的,一共只有十几个人。组长有2位,一位是上海锅炉厂的工人出身的技术总负责;另一位是兰州西固发电厂的厂长、老工人技师。两人都很好,一点也没有“造反派”的脾气和当官的架子,可能也是挨斗过的。课题组的工作地点就放在我校动力馆一楼。
我校有3人参加,另2位是工人、贫农出身的实验员。对于此项目,我还是比较有思路的,研究主要是按我提的想法做。后来,我被“清理”出课题组,两位组长还一直把我拉进去,讨论问题。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项目组就“消失”了。
大约从69年开始,沈志光、俞梅琴和我等,到位于周家嘴路近公平路口的上海东风制冷设备厂劳动,发现许多年青工人渴望学习专业知识。我们就办起“短训班”,后来越办越旺。这使我们萌生了办制冷专业的想法。高校恢复招生后,1972年我们就招了第一批制冷专业的“工农兵学员”。
在这段时间,也进来了一些很强教师,如缪道平、顾锡章、韩鸿兴等。从1972年到76年,制冷专业共招了5届学生。我们这里的学生,并不像某些学校学员那样喜欢闹事,他们大都是老老实实地勤奋读书。我带他们搞微型低温制冷机和低温绝热,倒也热热闹闹。
还给他们补些课,讲些物理、数学等基础知识。在那段时间里,我花了很大工夫写了2份讲义;又请蔡祖恢老师写了1份。这些讲义,今日看来仍然很有深度、很有参考价值;比现在某些装潢精致的“新世纪”教材要强。
我开始搞制冷,专业不熟悉,化了很多的时间、很大的精力阅读制冷的书籍和期刊。当时没有复印机,也买不到书,资料全是靠手抄的。读书笔记写了有5-6厚本,还加了一些心得和评语,至今有的还在动力馆二楼的书架上。在***期间,上海图书馆(那时在南京路)偌大的参考阅览室,读者总不超过10人。周启谨和我是经常出现的两个。
一天,周老师给我看一篇国外期刊论文,是关于测量窗式空调器制冷量的新思路。此文引起我的兴趣,不久我就拉了几个同事,在动力馆建起了一个“风管热平衡法实验”的装置;并且在首次在国内期刊上发表了论文。以后又经过多人改进,这个试验装置至今仍然是制冷专业的一个重要的试验设备;同时也为外单位研制了多套。现在我校制冷专业在制冷装置性能检测方面居国内领先,可能与当时起步早有关。
(二)1978年以后的大好形势
1976年10月,***倒台,国家开始“拨乱反正”,进度是相当快的。1978年5月4日,是劳动节假的最后一天,听到弄堂里的阿婆叫,“x x号三楼华泽钊,传呼电话,是学校来咯”。电话通知我,次日去学校考外语。后来才知道,中央指示要改革开放、要派留学生。
教育部5月1日发文,全国选首批200名出国留学。此事特急,要求各单位5月6日前将名单报市教育局;5月10日报教育部。我从“社会关系复杂”,一下子跳到“公派出国”,变化之大,简直不可思议。
5月4日学校里的外语考试,主考官是外语的戴鸣钟教授(1936年清华毕业,1940年获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我校副校长)。然后,去北京语言学院参加笔试和口试。幸好,被刷去的名单中没有我;于是8月25日集中到北京语言学院学习半年的口语。
当时,上海工学院(后来的上海大学)和我校合并,两部分就我一人。这一批中上海大约有12-14人。现在记得的有复旦化学系的高滋、数学系的李大潜、吴立德,上海科技大学的郭本瑜,上海交通大学冶金系的高明等。不过学习的语种不同,有法语、德语和英语。
接着就是联系出国。当时规定只能去“第二世界”的国家,不能去美国和苏联。一天,科学院的洪朝生院士(当时是数理学部学部委员)打电话给我,说英国的南开普敦大学低温超导实验室欢迎我去。我因一心想去美国,加上女儿刚出生,就放弃了。
80年,开放可以去美国了。我申请联系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机械系主任、国际传热学权威罗塞诺教授。他请了一位好友、该校“系统工程”的权威西格教授(犹太人)对我***。***是在上海锦江饭店,谈了约半小时。西格教授很满意,当场就表示他可以代表罗塞诺教授,同意接受我。另外还说,“如你愿意搞系统工程,我也欢迎”。我当时实在是对“系统工程”一无所知,否则动了心,转了过去,今日可能又是另一样的局面了。
插几句话谈谈那时我校的系统工程。介绍我和西格教授见面是我校的车宏安老师。西格教授是应邀来我校讲系统工程的。车老师工作十分勤奋,能量很大,办法特多。我校系统工程能搞起来,他和戴鸣钟教授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他们在国内能请到钱学森先生;国外能请到MIT与我校合作办首期系统工程班,实在是够成功的了。这件事的成功,本身就可以算是系统工程的范例。当时上海机械学院留下的一批人,有一些是十分能干的。我刚进校时就听说学校里有2个“安”,一位是车宏安;另一位是任迪安。
到了MIT, 系主任罗塞诺让我用2周的时间,在系里看看,选择导师和课题。我选择了跟科拉法侯搞低温生物医学。他是机械系的教授,同时也在MIT和哈佛大学合办的健康科技中心兼职,是这个中心的低温医学生物研究室主任。他是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田长霖教授(后任过那里的校长)指导的第一位博士。我和他有相近的学术背景。
为了“显示”我的实力,刚去3个月,我就在国外期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冻结过程中细胞膜内外的温度差及其对水分传递的影响”。此后,他和我的关系很好,让我参与他的研究。我也就从由国家资助,转为由MIT资助。当时国家经济条件很差,我们去美国拿过一次性的60美元的安置费和120美元的购书费;每月生活费(包括房租)只有350美元。
在MIT研究的项目是奶牛胚胎低温保存,企业投资了800万美圆。奶牛胚胎是用直升飞机从农场运来的;直径只有0.1毫米的胚胎,每粒竟100美圆。在这段时间,我不但学到许多新知识;学会了科研项目该怎样“经营”;更重要的是认识了科研的真正目的。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他们认可我是他们“队伍”的人。对于这点,我当时并不认识,事后多年才越来越体会到,他们和国际学术界都把我算成他们“MIT派”的人。
1991年我又到美国低温医学科学公司工作一年,任顾问。那是常兆华和他的导师布斯特教授两人创建起来的公司,研制用冷冻方法治疗前列腺肿瘤的医疗器械。此公司成立不久,就被一个犹太人财团控股,总裁原是石油财团的犹太人。
公司出钱给纽约州立大学;大学再请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纽约州立大学,为公司工作。我每月有2/3的时间在纽约州的学校;1/3的时间在马里兰的公司,两头都是研究公司产品的问题。就是那时,我买了辆二手车来回跑。我在研究技术问题的同时,知道了不少公司运作的事情。这些与本文关系不大,就不详谈了。
还是回头来谈上海理工大学的事吧。陈之航先生比我大11岁,80年代已经当学校校长。1983年我从MIT 回到学校后,对我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我大加表扬。不知是我变了,还是他变了;或者两人都变了,我变得更多些。
以前,我们曾一起吴泾,相互很熟悉。他说我“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后来还有人跟我说,当初要派我出国时,陈是提出过意见的(这是完全正常的)。不论此话是否真实,陈先生那时对我的评价不是很高的。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是成熟多了,能干多了。
科拉法侯教授叫我再做几年,拿个MIT的博士学位。当时我国驻美使馆多次通知,访问学者的家属不得探亲;进修人员不得延长或改读学位。我想,做人总要有个信誉,讲好回来还是应该按期回来的。于是就向他要了个美方资助的访问学者位置,孙仲秋接我的班,去了美国。可能是由于这件事,陈校长对我的看法有了“突变”。
尽管一些人对陈校长有非议,但平心而论,在我校几任的校长中,他是做得最出色的。他有事业心,有想法;他又敢于用人;能给想做事、肯做事、能做事的人,给予扶植、提供条件。在当时,即使是精神上的鼓励,也是十分重要的。
学校有什么学术方面的大事,如教授申报、学位点申报、学校发展规划等,他都先找些有想法的教师商量。而后来的校长们就不一样了,他们的“组织性”太强了。凡事,先是“校级”,再是“处级”、“科级”;下到教师这里,就只是“执行决定”了。
1985年高教部开始教师学衔评审(当时是叫“学衔”,以与“职务”区分),我校幸运地被定为学衔制的试点单位。当时为保证质量,教授的评审权在上海市,各高校只有申报权。向市里申报,先要通过学术委员会。当时校长是陈之航,他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直接申报正教授。
我当时只是讲师,生怕落空;就问,如评不上“正”的,能否评“副”的;答曰“不行”。当时沈炳正先生是学术委员会主任,他比陈小一岁。两人之间可能有些矛盾,陈担心事情会有麻烦。一天,沈对我说,陈建议我越级晋升,他觉得很好,全力支持。
在学校学术委员会上,我被全票通过;陈校长发表了十分激动的讲话,对大家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因为当时的校学术委员许多年长的都只是副教授。那时教授是很“稀罕”的,记得60年代的清华大学,全部教授、副教授才只有“108将”。
86年元月14日,上海市学衔委员会举行的评审会,通过我为正教授。次日,陈校长就要我填写申报“低温工程”博士点和博士导师的材料。当时,博士导师是要通过***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如果是新申请的博士点,那么新的导师是一起批的。
我校“热能工程”博士点和陈之航教授的博导是1984年取得的,那时我校就成了博士点授予单位,属于整个全国的第2批。陈先生成为“博导”后,积极组织一些人当副导师,而且是带不同方向的博士生。我也被他列为“培养对象”,负责制冷与低温方向。
1986年是我校学科发展最显著的一年。当年6月1日,***学位委员会一下子批准我校新增“热力涡轮机械”、“工程热物理”和“低温工程”3个博士点和4位博士生导师(刘高联、蔡祖恢、王乃宁和我),使我校的动力机械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博士点数挤入全国的最前列。那年批准了首批“低温工程”的3个博士点(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和我校)和3位博士生导师(吴业正、尉迟斌和我)。
当时有人说,我是全国高校工科中最年青的博导,因为其他大多是1952-53年以前大学毕业的。那时我的声誉较高,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中国科技大学等都请我去作报告;中科院低温中心让我代培了2个研究生;解放军军事医学院等单位派人来进修。
当时博士生的生源也很多、很好,除我校的优秀硕士生常兆华、陈愈外,上海交大夏安世老教授(被誉为我国制冷的创始人)推荐了王德荣,浙江大学林理和(时兼任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推荐了陈锡浩,以及西安交通大学的俞国新、曹前,西北工业大学的韩润虎等。
上海交通大学的长江学者王如竹,去年和常兆华一起被评上上海市十位科技精英,对我说他曾想报我的博士生,后来出国了。我原以为这是客气话,这次在翻阅记事本时,见到1986年4月确有这样的记录:“上海交大8402班王如竹,1964年生,要考我的博士生”。
我的第一个博士生王德荣是1985年4月年进校的,根据其志愿,导师陈之航教授让我任其副导师,从事低温生物医学技术方面的研究。1986年“低温工程”博士点批准后,陈即让我“转正”为“正”导师。王德荣1988年毕业,成为国内第一位“低温工程”博士学位的获得者。
1987年元月,上海市市高教局出版了《上海高等教育系统教授录》。此书中列出我校正教授共22人。他们是王乃宁、王伯年、卢思源、刘高联、朱继梅、华泽钊、沈炳正、李燕生、陆景云、陈之航、赵永昌、赵学端、俞征、顾去吾、徐昂千、韩鸿兴、楼惟秋、端木时夏、蔡祖恢、缪道平、薛培桢、戴鸣钟。其中有1/2左右是1986年评上的。
(三)走自己的路,开展与临床医学结合的研究
我从美国回来后,一心一意要搞与临床医学结合的研究。当然困难是很大的。学校没有生物、医学等相关的学科;没有资金、队伍;没有实验室。有些年长教师好心地劝我,这样搞大跨度的跨学科研究太难、太累了;搞得不好,可能到退休时连副教授都评不上。我那时并没有想得很多,只想搞感兴趣的事。如果时间推迟到今日,按现行的科研考核办法和强烈的功利观,我可能自己也不敢走;别人也不会跟我走这条路了。
我决心搞与临床医学结合的方向,是有一定思想根源的。我6岁时,父亲就在从上海逃难到江苏张渚期间病故了;母亲千辛万苦地我们姐弟妹6人,拉扯到大。待我们大学毕业后工作,家庭情况开始转好时,1975年母亲发现患了晚期肠癌,当时的医生误诊且束手无策,母亲很快离开人间。此事对我触动很大,决心研究些新的医学技术,希望能为拯救病人有所贡献。
陈校长对我很支持,主要是精神和舆论方面的。经费也给了些,但不会很多,因为已经记不得了。那时学校还没有工作量考核,我找了几个肯跟我“冒险”的人。当时有姚柯敏、邬申义、陈儿同、赵林、丁德俭;研究生有王德荣和常兆华。全是20来岁的年轻人。陈校长又把医务室的丘萍珍医生(后来是忻雅雯)请过来,做我们的“医学顾问”。后来,这些年轻人大多都出国了。王德荣去了美国。
常兆华到美国拿了个生物学的博士,和他的导师创办了低温医学科学公司;6年前回到上海,在张江创办了一个做心血管支架的“微创医疗器械公司”。赵林是1978年毕业的女教师,靠着在我们这里的工作经验,在美国西雅图的一个很有名气的癌症研究所找到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她的“老板”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邬申义是我的第一位在职的硕士生,后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拿了博士,留在该校任教。姚柯敏去澳洲,拿了MBA, 回国创业,现任新澳公司总裁。他很关心学校发展,捐款支持学科建设。
由于是新方向、新班子,没有实验室。84年9月,学校也想方设法在家属楼里给我们搞了一套作为实验室,是家属宿舍的326号603室。我们就立即动手自己改装,可是第2天就停工了。因为楼下就是刘高联老师(1999年评为科学院院士),他主要做理论研究,大部分时间在家工作。我们在他的头顶上敲敲打打,确实使他无法静心。作为置换,我们在近校门一个老式宿舍的底楼找到一间,约20多平方米。
我这个人性子很急,干事有点“玩命”;下面的年轻人也乐意跟我干。很幸运的是,在我们开张2-3年内就拿到了几个重要的项目,一个是上海市重点项目“低温显微镜系统的研制”;一个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前身)“生物材料低温保存的热分析和热控制”。
87年又得了国家七五重点项目的子项目“鱼精子和胚胎低温保存及其专用设备的研究”。1987年我们承担的“大型低温显微镜”获得了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有了这些项目的资助,我们就积极寻找与临床医学结合的研究内容。当时的“合作”还不怎么讲经费,不用签合同。大家都“义务地”做科研。合作的第一家就是瑞金医院的烧伤研究所,合作者是史济湘、冯世杰、李映月,还有小孔。冯和李分别是南京大学生物系和上海二医毕业的,年龄与我差不多。烧伤所所长史济湘教授是1947年的医学博士,时任中华医学会烧伤外科分会主任、法国外科科学院海外院士。
他与杨之骏等,于1958年成功抢救了烧伤面积高达98%的钢铁工人邱财康,名气很响。1984年,正当史医生想搞皮肤低温保存的时候,正好我去他的研究所寻找结合点,两方一拍即合。我出生在瑞金医院的,当时这医院是法国人办的,叫广慈医院。
瑞金医院我家离很近,只有步行5分钟的路程,我经常去。博士生常兆华就索性住在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就在那段时间,他和该校的女学生交上了朋友)。皮肤的研究取得很好的成果,史济湘教授也给我们讲了许多好话,为我们进一步与医学结合,造了很好的舆论。
接着,在瑞金医院我们又和外科的蒋吕品教授合作搞了肝细胞的保存;配合张圣道教授指导博士生胡海进行低温保存和移植的研究。蒋医生是52年同济医科大学毕业的,人品和医术都极好。当时任瑞金医院“大外科”主任。张教授是胰腺外科的专家,后来同济大学校长吴启迪患胰腺病,就是他抢救成功的。
1986年5月30日学校体检时,发现我患甲状腺肿瘤,外科的医生大多劝我要手术割除;内科的则建议保守治疗。我这个人心特别急,6月27日就住进瑞金医院准备挨“刀子”,主刀的就请蒋吕品主任。当时史济湘教授正在美国讲学,还专门托他的妻子,找蒋主任关照。
蒋比史小6岁,对史医生很尊重。蒋对史太太说,“我和华老师早就是好朋友了,请史医生放心”。手术十分成功,而且刀疤很不明显,内行看就知道是高手动的刀子。可惜,过了没几年,蒋主任自己患癌症病故。他的儿子蒋尧现在是很有名的骨科医生。
后来我家搬到海宁路,就和新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合作多一些。在新华医院,我们和应大明、丁文祥、刘锦纷、黄惠民等教授合作,先是搞血液成分保存;后搞动脉的断裂防止。另外,也和胸科医院周允中院长、赵珩医生搞人气管;和妇产科匡延平搞人的胚胎保存等。
第一人民医院有个糖尿病研究所,希望用胰岛移植来治疗糖尿病。初时是用流产胎儿的胰岛,但数量太少。于是张洪德主任、王熠非医生就想用异种的(即其他动物的)胰岛。为防止强烈的异种排异反应,我们一起成功地研究了一种膜技术。
近三年,我们又和上海市组织工程中心(最近升格为国家组织工程中心)合作,实现了人干细胞的保存,和组织工程化皮肤的低温保存。该中心的主任曹谊林教授就是用组织工程技术在老鼠身上长人耳朵的那位。他个性很强、人也很“牛”,但和我们的关系很好。2005年他和我们还合作的“组织工程化皮肤的体外构建、低温保存和临床应用”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一面在校内抓基础研究,另一面在医院搞临床应用,我心里很满意,也有些“成就感”。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在86-98年期间,对我们的研究也有过5篇专题报道。按照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动机学说”,我自认为已进入了“自我实现”的程度。
到目前为止,我拿到过1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此前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有2项是重点项目。我们研究室的大多数年轻人也都拿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其中,任禾盛、刘宝林各拿过2项;邬申义、俞国新、陶乐仁、周国燕各拿过1项。这些年来,我曾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12项;其中的9项我为第一完成人。
关于评奖,有2个小故事。1996年,当时我校属机械工业部,我以“低温技术在生物医学中的应用”,申报机械部的二等奖。科技进步奖要讲项目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的。而我们的成果没有经济效益,只有“社会效益”;就只能作为“理论研究”的成果,也只敢报二等奖。心想大概拿个三等奖就可以了,没想到竟被评上了机械部一等奖。
当时参加那次“理论组”评审的徐福缘教授后来跟我说,评审委员们认为,申报一等奖的几个项目水平都不很高,“还是华泽钊这个较好”。他们向徐老师询问了我的情况,徐说“在我校教师中,华是我最敬佩的老师之一”。就这样,此项目被“理论组”提名申报机械部的一等奖。10月7日,由机械部组织对申报一等奖的项目进行答辩;作为“考官”的专家,有2/3是院士。
我被排在最后一个答辩,但专家们对我的报告很感兴趣,问题集中在有哪些科学问题和技术难点;是如何解决的;有什么创新。我答辩得很实际,又很自信。从他们的眼神里,我感觉专家们对我们的工作是满意的。过了1小时,机械部教育局科研处的李伟民处长告诉我,‘大家评价很好。你介绍得很精彩;主审是湖南大学的徐校长(至今我还不认识),讲得也很好。“你画龙,他点睛”’’。
最后评审会的结论是“个人申报二等,初评一等,保留一等”。李对我说“你可以放心回去了”。我觉得还不甘心,还可以试试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就马上去找部科技司。得到的答复是国家科委只给了机械部一个名额,已经内定有“主”了。
但3天后,接到部科技司成果处的紧急电话,要我们二天内备全申报国家奖的材料,飞机送北京。就是这样,我们获得了1996年机械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99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四等奖。那一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共有51项;技术科学部有7项:3等奖4项;4等奖3项;1等和2等奖空缺。(2000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奖改革,只设1等和2等奖)。
还有一个小故事是关于教材奖的。我们化了4年时间,写了一本《低温生物医学技术》,199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来此书是中国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的专著,后来才被用于研究生和本科生教学。没有想到,竟被评为1996年上海市优秀教材一等奖,和1997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对此事我很纳闷,不知是通过哪个学科评上去的。数年后,遇到上海第二医学院基础教育部主任汤学明教授,才知道是他提议,通过医学口,评上去的。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大概是医学的教科书太多了,我们的这本到它们那里显得“新鲜”吧。
不过说实在的,我们写书是化了很多精力和时间的,内容是有深度。在国外,搞低温生物学的中国人,几乎都带了这本书。后来,我化了4-5年时间写了一本“冷冻干燥新技术”,也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出版基金资助的专著,2006年1月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自信,这本书是高质量的、有深度的,会得到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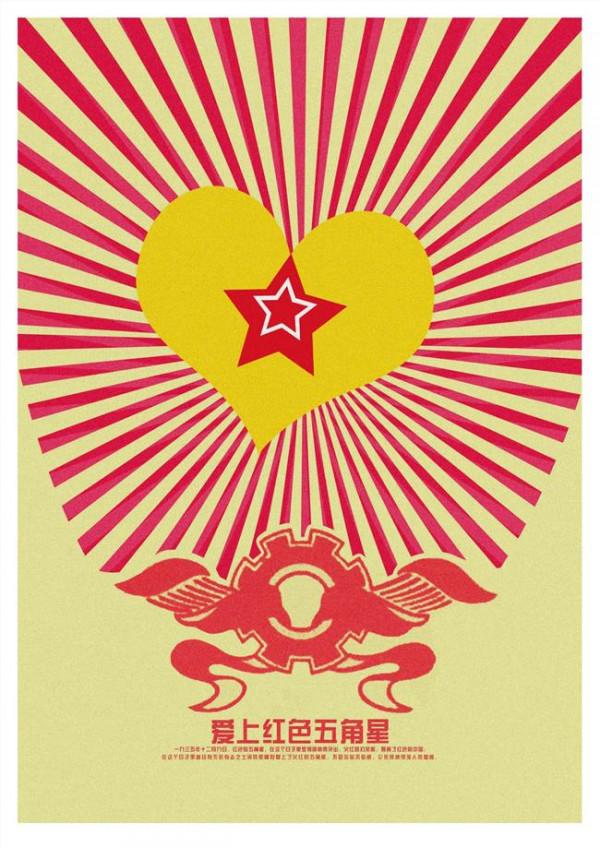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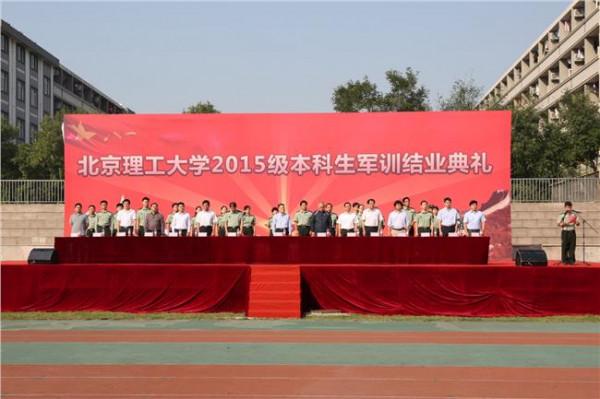



![>王新兵上海交通 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2017届本科生毕业典礼举行[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5/a9/5a905c8cf21fdc594dc044df183fc595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