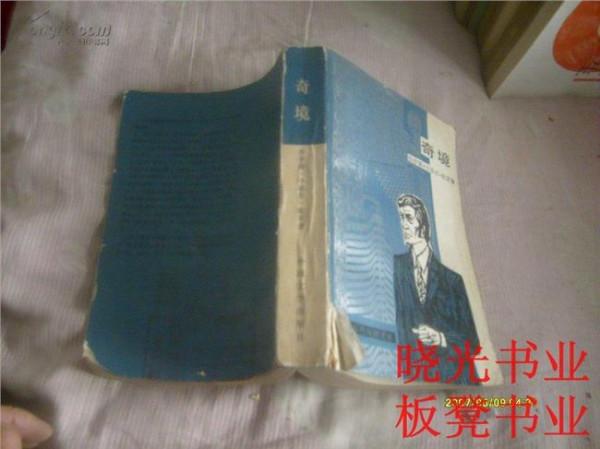乔伊斯卡洛尔奥兹 乔伊斯·卡洛尔·奥茨:你为什么写作?
有时,问我这个问题的也是从事写作的人,因此是很认真,甚至他非问不可。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问我这个问题的人块头有我两倍。在宴会上他一发现坐在旁边的是我,便想不出有别的什么话可说了。你为什么要写?他问道;尽管我并没有问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卖力干活?或者你什么要做梦?甚至也没问他你为什么非得问这个问题不可?虽然外表上我彬彬有礼,可内心里却一片茫然,而且碰到这种时候,我便显得格外的忸怩。
这一般只回答说因为我喜欢写。
这么说无伤大雅,而且无懈可击。那些莽汉们听了也觉得心满意足。他们老是用这样的问题缠着我(最近一年来平均每周一次):言下之意在于:(1)表示写作者对现实世界问题无能为力;(2)显示提问者的优越感,因为他的确不需要靠想象力的产品来糊口谋生。
你为什么要写?
这问题真是引人入胜。虽然在公开场合我从来没有为自己做过任何解释或辩护,但私底下我一直为写作或其他艺术创作活动的动机而苦苦思索。我苦苦思索着人的思想和想象的深处,特别是那种处在半意识状态的想象深处;这种想象每日每夜都会显现出一些使我们惊诧的怪诞而又可爱的画面。
那些怀疑主义者带着挖苦问我为什么要写作,但同他们相比我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也在“写”,在创作,每天晚上都做梦,可能连白天也做梦,他们的梦是些具有真情实感的艺术作品。
写作和做梦的道理一样,因为我们不能不做梦,因为做梦乃是出自人类想象的本性。我们这些“写作狂”为了探求隐藏在现实事物中的各种意义,在有意识地对现实进行安排再安排,做的是比较认真严肃的梦;或许我们已做梦成瘾,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们害怕或藐视现实。
如弗兰诺利·奥康奈所说(参见她逝世后结集出版的那本非常出色的文集《神秘与神采》),写作并非逃避现实,而是“投身到现实中,并对现实的体系产生很大的震动,”她坚持认为作家对世界是寄予希望的,心中没有希望的人不会从事写作。
展现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常常会给人一种混混沌沌、可怕无聊的感觉;我们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赋予这样的世界一个较为连贯、较为简约的形式。怎样来处理这种常年的,日常的,或是每时每刻都会出现的暴风骤雨呢?世界没有单一的意义,我很伤心地承认了这么一个事实。
但是,世界有多重的意义,有许多独特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可把握的意义。人生在世的历险就在于发掘出这些意义。我们想尽可能勾勒出生活的模样。我们同我们大名鼎鼎的对立面科学家并没有很大不同。
科学家同样也想勾勒出事物的模样,使生活较为连贯一致,一步一步地把事物整理得有条不紊,拨开各种各样的迷雾。我们写作是为了从时间或者从我们自己生活的混混沌沌中理出各种意义: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相信意义是存在的,我们要使之适得其所。
弗洛伊德说,“艺术产生了自我把握的幻觉。”他同任何见多识广的人一样关心内心的神秘的象征(因而也就是艺术)所能达到的广阔范围。这句话使我感到惊异。万象包罗其中,什么都说到了。艺术像梦那样“使人产生幻觉”。
艺术是使人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因此恍然大悟的梦,偶然地,也会被安上精装封皮出版了,而且毫无疑问,总是定价过高。如果这个梦当真是件紧俏货,就可以卖给电影界。电影可是个神奇的模拟我们做梦的现代艺术形式。
黑暗中夸大了的形象、脸庞、动作在平展展的一片银幕上动来动去,对于传达各种恶梦真是太合适不过了。如果这个梦不是特别有销路,那就永远得不到发表。但是,正如人类的许多尝试一样,这个梦将被搁在哪个偏僻的角落,无害也无弊,也无人过问,但也没有价值,没有一个梦是是无价值的,它是一个幻觉,而所有的幻觉,像所有的景象一样,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们应该忠于自己的梦,”卡夫卡写道。
人们在“开始”写作时(虽然我觉得“开始”写作这个说法很怪,就像说“开始”呼吸一样),受到了自己内心活力的驱使。这活力是一种意识,觉得有一种独特的东西要说,而且非我莫属;这种内心活力,这种神秘的信念,便是所有艺术的基础。
但是,人们开始从事这样一种从外面看起来是如此考究形式、如此专业化、甚至在1969年或许还显得如此颓废的技艺后,很快就吓坏了,深恐自己技巧欠精。因此,他们就参加写作讨论会,上“创作课”,买了许多书,想从中学得“小说的性质”。
此类活动并没有使初学者上当受骗,因为所有能得到的材料对写作者都是有用的。但是,写作者的艺术基础不在于他的技巧,而在于他有欣然命笔,有要写作的愿望,实际上也就是觉得自己不能不写。
我向来要我的学生多动笔——写手记、做笔记。觉得灰心丧气时要写,觉得内心好像要崩溃时也要写……谁知道这时候会涌现出什么东西?对梦的魔力,我是个厚脸皮的崇拜者。梦增加了我们的价值。甚至恶梦都会有销路——这就要谈到对恶梦的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祓除加工,要是这些恶梦所产生出的作品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塞莱恩和卡夫卡的作品相提并论的话。
所以最重要的是要写,几乎天天动笔,不管是身体健康还是病魔缠身。
过了一阵,或者几周,或者几年,你总会从这一大堆杂乱无章的印象中悟出其中的意义……或许有一天,这些材料的意义会突然自己显现在你眼前。西沃多·雷得基会匆匆记下一句“诗意”盎然的惊人之语,带在身边几年后才在一首诗里派上用场,或者以这个句子为核心,一首诗也许就随之诞生。
这又有什么不同呢?活力是神圣的。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内心有过剩的活力,因为我们比旁人对生活更敏感,更充满热情,或者更富有好奇心。为什么不尽量利用这一点呢?
如此说来,艺术“产生幻觉”这话不假。因为,当然了,艺术并不是“现实”。你不会靠艺术去寻路,而要靠地图,因为地图真真实实再现了地表的状况。你不会靠读书去找人,而要靠查电话簿。艺术并不是“现实”,也不必是现实。
艺术家不屑于表现世俗的现实,他们爱这么说(我很喜欢把他们想象成是在宴会上,不肯忍受我老是遭到的那种欺侮而说这种话的):“现实那就更糟糕!”现实——真实的生活——报纸、新闻刊物,还有街头巷尾的传闻——这些都是伟大艺术的素材,但不是艺术本身,尽管我们意识到了“艺术”一词在语义上固有的难解之处。
让我们假定“艺术”指的是一种文化(而不是美学)现象;一只干瘪的蜘蛛不知怎么的被放到一个画框里,不可思议地变成了一件“艺术”的作品,但同样一只蜘蛛,没人去理它,没人去碰它,就仍然是一件“大自然”的作品,得不了什么奖。
给艺术下的这个定义使传统派大为恼火,但很合我的心意。因为这句话使人觉得生活是多么像格式塔,又没个定形,也表明我们作家(还有科学家、地图测绘员、历史学家)是多么有必要把生活安排得合情合理。
你为什么要写?为了发掘出隐藏着的生活的意义。我们很可能这样回答;这样回答显得乐观,皆大欢喜,虽然可能有些浮士德的味道。我一向是从平常的生活中撷取素材的,对报纸,对恩·兰得尔的专栏文章,对《真心忏悔》,对以“闲话”的名义流传的轶事奇闻,我都深感兴趣,令人惊叹的启示!
世界上充满了启示,充满了悲剧——信手拿起一份报纸,翻到第五版或者第十九版,你的视线落到一条标题上,随便哪一条,这里面就有一个故事。我无法计算我自己根椐最简单直捷的报纸写出的作品有多少……我想,正是报纸这种不加雕饰的性质吸引了我,在我心中激起了一种需求,要给像这种讲得一是一,二是二,干巴巴的故事添血加肉,要给这种已成了明日黄花,不重新体验,不重新进行戏剧性加工就没人能懂的事件注入新的生命。
报纸上登载的某人的生平片断会吸引作家写出一整部有头有尾的作品。这种事有点像在地上找一块拼板玩具片,找着了这一片,整个就拼成了。只要花上一点气力,为什么不找呢?说不定你会想象出一个比“现实”更好的故事来,为什么不这么去做呢?
因此,艺术的“梦”,或者幻觉,或者沉思,根据的则是现实。无意中听到的一句话,一股突然涌来的揪心的情感,一番心灰意冷的感觉,一阵怒气,《真心忏悔》中读着活像做场恶梦的一则故事,这些都是我们的素材。那些《真心忏悔》不能首先收入的东西我不想写;那些不能先以某种形式,不能以民谣这一最简单直捷、最富戏剧性的艺术形式唱出来的东西我不想写。
我不想写一个难得成为艺术的梦。批判性写作同有理性的人一样对我很有吸引力。也许是引我去干些劳而无功的傻事吧。我会忍不住拿自己的智力去同别的作家比个高低,分析钻研他们的作品,想悟出其中的意义——但是,最重大最神圣的任务不是批评,而是艺术,而艺术可能是比较容易达到的。
艺术产生了自我把握的幻觉。什么是自我?是我的自我在写这篇文章,是你的自我,你自己,在读这篇文章。你就像圈住在某个界限内的细胞质——你的自
我并不固定,而是流动的、多变的、神秘的。它绝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同一个自我,但也绝不会是另一个自我。你死了没有人能接替你。要是我死了,我这个特定的存在,我的个性,也就永远消失了——这也许是件好事——但这是不可弥补的。
我们的自我期望得到控制;我们期望得到“把握”。现实总是捉摸不定,因为,正像我们自己一样,现实也是流动的、神秘的,隐隐还有些吓人呢。我们总是掌握不了现实,甚至那些我们喜爱的人、那些喜爱我们的人、那些我们自以为对他们有控制的人,到头来还是昂然独立,非我们所能掌握;注定了的生生死死全是他们自己的事,非我们所能左右。
但我们企求,拼命企求这种把握。而且,因为企求这种把握,我们就得创造出这种把握。我们做梦;我们创造出一个世界(假定是一篇小说吧),里头住着我们创造的人,我们指导他们的思想,而且我们肯定他们的各种遭遇交织在一起会表达出某种意义。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作为作家,直截了当一句话,我们需要了解自己——我们写作,是为了装出一副把握了世界的样子。不像那些典型的怀疑主义者,他们不喜欢艺术,因为它不“现实”,我倒觉得这很合我的心意。我觉得这是个高尚的使命。
争取对世界,或都对世界的某个断面,进行“自我的把握”,我觉得这很高尚。十九世纪诸如《白鲸》和《卡拉玛佐夫兄弟》那样宏篇巨制的小说会创造出一种神圣的氛围。写这些大部头的人想把一切的一切都写在纸上,巨细无遗!
但哪怕最轻松最纤巧的短篇小说(以尤多拉·韦尔第或契诃夫的作品为例)也会有这么一种神圣的氛围,当然前者会深刻些——因为艺术家也是传教士、魔术师,甚至科学家,同样被隐藏在世界表面下的意义迷住了心窍。发掘出这些意义是一件高尚的使命。
所有的艺术都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可能在于那急风暴雨式的、颇有点荒诞不经的创作过程——比如“行动派”画家波洛克或德库宁的画——也可能在于作品本身的比较传统的结构,说得明明白白,这样学生就可以在“尽你所能去生活吧,不这样就是错误的”(詹姆斯:《使节》)这句话下划一条杠杠,觉得自己毫不含糊地理解了作品的“意义”。
《白鲸》的“意义”不只是在写“白鲸”的那著名的一章,而是在所有的章节——最富有戏剧性的,以及最冗长乏味的章节——纵观全书,意义才现,那就是梅尔维尔对现实的探索。
这样,你为什么要写?再回答一遍这个赫赫的大问题:我们写作,是因为我们肩负着高尚的使命:廓清各种秘密,或者指出我们因为麻木不仁和不求甚解而认为很简单的那些事实的奥秘。我们写作,是要忠实于某些事实,忠实于某些情感,是为了“解释”那些表面上古里古怪的行为……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为什么会变得暴戾恣睢,会去杀人;一个无忧无虑的女人为什么会跟人私奔,结果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头脑清楚的人为什么会去自杀?我承认我这个人老脑筋,循规蹈矩。
我用传统的一套观物行事;我写作的动机也是传统的,而非离经叛道的。荒诞的结构和观点对我很有吸引力,并且可能的话我会把一个故事倒过头来写,或者分成几路,齐头并进。但是,在我所有的那些并不惊世骇俗的狂放手法背后,真正的就只有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使作品有意义……我想知道人类各种情感后面的“为什么”,尽管我只能一再说明,人类的情感是我们最深的奥秘,谁也无法理解。
对在技巧上搞的那类名堂我不那么感兴趣,那是在纸面上下功夫,所强调的是它不现实性(比如贝克特的作品就是对写作过程本身的模仿嘲弄),尽管毫无疑问,立体派和抽象派的艺术家们已经在作为油画的画布而不是作为镜子的画布上画出了美丽的东西。
但是我,作为一个女人,对单纯理智的东西很快就会厌倦。如果一个故事只是以理为胜,那写成一篇小品文,或一封给编辑的信岂不更好?
我的全部心思都用在那些除了显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飘忽不定的性质外别无用处的动词上了。
如果一个故事写得好,是不需要在没有意义这一事实面前强调它的意义或它的难以理解之处的:故事本身就是它的意义,如此而已:契诃夫的任何一个短篇小说本身就是它的意义所在。它是一段经历,一个情感事件,通常具有异样的美,偶尔也具有异样的丑,但它本身是纯净的,不需要任何阐释。
《带叭儿狗的女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中很典型的一篇,讲的是一个饱经世故的男人和一个不谙世事的女人之间毫无希望的恋爱事件,这女人的丈夫呆笨但又有钱。
男女主人公邂逅了,相爱了,不断地幽会……她哭了,他也束手无策。由于他们各自的家庭、各自的社会责任等等因素,他们不能结婚。故事的“意义”就这些。契诃夫使我们感觉到了他们进退维谷,他们极度的痛苦使我们经久难忘。
这就够了,故事不需要再有别的意义。可以肯定,他们不是因为私通而受惩罚!——也不是因为不敢私奔,不够罗曼蒂克而受惩罚。他们是平常的人,陷进了不平常的境遇。《带叭儿狗的女人》是他们情感危机的记录,我们对此也产生了共鸣,因为,可能是老大不情愿吧,我们看到自己也陷进了这种境遇,自己也在欺骗自己,尽管我们聪明伶俐,可还是一筹莫展。
短篇小说的性质是什么呢?它没有单一的性质,而只有多重的、不同的性质。就像我们各人的个性不同一样,我们的个性所做的梦也不会相同。没什么规矩可循。过去有过一条规矩——“不要沉闷乏味!”但这也打破了。今天的作家,像贝克特·阿尔比和品特,就故意写得沉闷乏味(虽然他们的成功之大,也许自己还不知道呢),真是各显神通。
极尽夸张之能事。无所顾忌地说半截儿话。非常简短的场面描写,非常冗长的场面描写……照相式的撷取印象,托马斯·曼式的大段内心反省:不拘一格。
当然啦,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都没有一定的长度标准。我相信任何短篇都可以改成长篇,任何长篇也都可以缩成短篇,或一首诗。现实是流动不定、怪异吓人的,让我们尽可能把它装成各式各样的包包,标上名字,安上精装封皮出版吧。让我们把它拍成电影吧。让我们宣布:一切都是神圣的,因此都是艺术的素材——或者,也许可以说:一切都不是神圣的,都不是碰不得的。
业余作者往往想写大事情,表现严肃的主题。也许他是为社会良心所驱使吧!但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所有的主题都是严肃的,或者愚蠢的。没什么规则。我们无所羁绊。奇迹就在手边,就在还没启封的打字带的油墨里,正急切地等着要跃然纸上呢。
我要我的学生们写他们有真情实感的主题。他们怎么知道自己写的是有真情实感的主题呢?这要看他们写起来是不是得心应手,是不是欲罢不能。还要看他们是不是因为做了应该做的事,和盘托出了认为不足与外人道的情感,说了似乎不该说的话而觉得不好办,甚至觉得内疚、或欢乐。
如果感到难于下笔,就不要写。重新开始,另写一个主题。有真情实感的主题会自成篇章,它是压抑不住的。赋予你的梦,你的浮想遐思以形式,培植锤炼它们,它们神秘的意义将会水落石出。
如果你觉得呆呆地坐着,两眼盯着窗外,是罪过的话,你永远也写不了东西,那干么还要写?如果茫然坐着,望着天空或河流,不知怎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你心底最深处的自我会因此而愉快欢欣,那你也许就是一位作家或诗人,总有一天你会试笔一吐情怀。
作家终究要写作,但首先他们要有感而发。
生活绝妙无比。
(摘自《短篇小说写作指南》/[美] F.A.狄克森、S.司麦斯 编/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