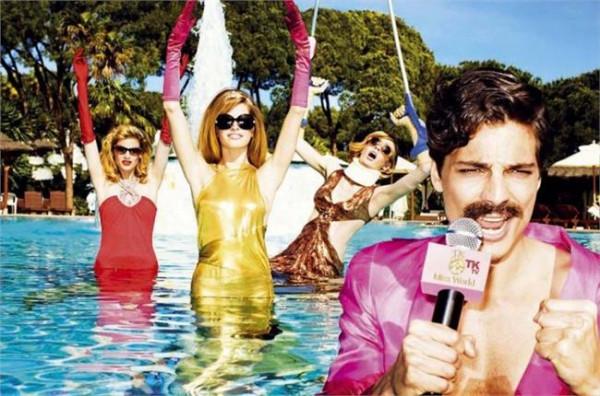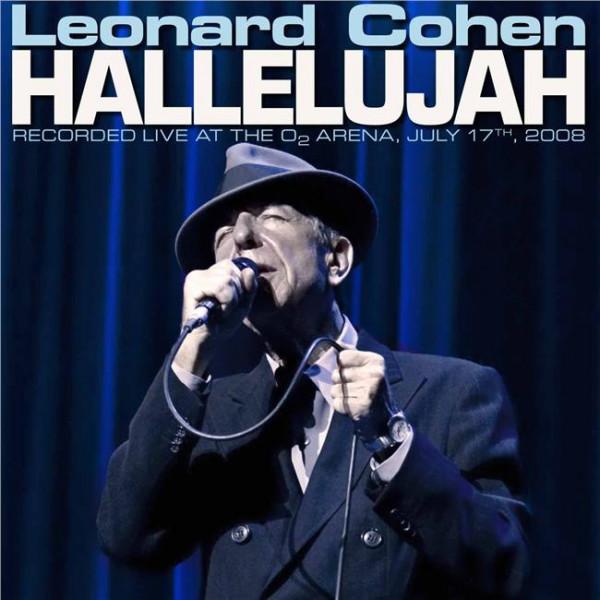诗人于德水 《诗性的纪实》——对话于德水
“我的表述全是源于内心深处的真诚,这是最重要的。”
李媚:前面提到你在“走黄河”时对着光膀子的男人拍了很多照片,还有你拍的麦收,你似乎热衷于表达人的身体形态和生命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力量和美感。
于德水:我想触摸人类自身的原始状态和真实的力量,这种愿望一直存在,而且很强烈。
李媚:很多人在拍摄一个人的形体和动作时其实是有目的性、有叙事性的。而你后期的照片实际上没有对生活进行具体的表达,你没有向观者叙述什么,更多是一种感受性的东西。但你的观察是基于存在的,这个存在本身就有指向性,有内容在发生,我们每一个人截取的只是一个碎片,这个碎片对于每个人的意义不一样。你的作品是纪实的,但它具有某种抽象性。
张惠宾:我觉得你并不排斥叙事,而是借助叙事完成了诗性影像。
于德水:我在影像中确实具有一种形而上感觉的追求。这种东西是我一直割舍不了的,是我一直希望表达出来的。我不在意这个动作、姿态是不是叙述了某个事件,我更在意它是否表述了我内心想阐发的感觉,而且我追求这种感觉的不确定性,它的指向越宽泛,越模糊,感受的容量似乎就越大。
张惠宾:你的影像跟观者之间是否有某种疏离感存在?
于德水:我的表述全是源于内心深处的真诚,这是最重要的。至于读者怎么理解,我不太在意。见仁见智,因为这与每个人的生活经验、兴趣、性格有关。
李媚:我觉得没有疏离感。疏离是一种拒绝、一种冷漠、一种错位。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曾经把于德水和韩磊在题材、内容上相近的影像放在一起给他们讲,学生觉得韩磊的影像更有疏离感。而于德水表达的不是疏离,虽然他的空间很大,但人和空间的关系是和谐的。他更多关注的是黄河这块故土给他的感受。一个艺术家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他的精神和一方地土已经形成一种高度融合的关系了。
张惠宾:寇德卡使用21mm镜头,身体和精神长期处于自我流放状态,也有一种孤独感。有人说你受他的影响比较大,你怎么看?
于德水:寇德卡的影像对人存在于社会之中时其内部世界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揭示。我觉得这是通过画面语言、进而超越画面语言之上的、对人的根本性的东西的触摸和探究。这为我的思考和找寻摄影更本真的力量,对于我的影像实践,对于我要用摄影来表现的主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坐标。
“侯登科赋予摄影太多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也经历过那样一个阶段,但我觉得摄影承载不起这些东西,所以我更愿意注重影像本身。”
李江树:于德水的影像没有发出很大的宣言,也没有给观者造成什么“高峰体验”。他自己说过,“口子开得小才能走得远,水流得细才能流得远”。他就是凭着一股韧劲儿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子,并一直沿着这个小口子几十年不动声色地努力着。
他在很小的事件中还原着生活的原貌,比如《乡村吉普赛》系列中蹬车的孩子那张照片。以前李媚说过一句话,“图盲比文盲多。”的确,很多人看不懂图像意义上的照片。于德水的影像确实有一种抒情的情愫撩拨着观者,历史的陈述就在这种平静的宣叙中缓缓展开。黄河玉成了于德水,于德水也以他独有的方式为自己挣到了一份黄河人的光荣。
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多层次的立体系统。较之同龄人,于德水早就没有了作为一个名人的那份虚荣。但他距一个战士,一个思想者,一个为第三世界和底层百姓吁请呼号的斗士相去甚远。他不是那类人,他没有那么大的气魄,他也仅只限于“独善”,限于坚持个人生活中的操守。
那种平静的韧性与耐性是他性格中的特质。他的作品不是沿着史诗的传统,而是沿着内倾的个人体验的传统。摄影是他精神中最重要的内容,因为摄影不仅是他精神上的一个分支,而且是构成他生命的主要质料。
李媚:他是属于自我消化型的,他的很多东西一定是转换成内心的自我消化。
李江树:有时候我就纳闷,是不是性格相反的人关系反而处得更好?侯登科喜欢饮酒,酒后暴烈,但于德水和侯登科却是最好的朋友,这可能是互补。
李媚:侯登科一天到晚跳着脚问于德水,你怎么不说话?但他就是永远需要这么一个不说话的人在身边。
张惠宾:你自己如何认识这种异同?
于德水:我俩性格的差异是显著的,但在精神领域的理解和认知,是一个连结的缰绳。要知道那是处在一个单一的、封闭的年代。拥有一个不设防的、没有禁区的交流对象弥足珍贵。
张惠宾:侯登科给你《中原土》作的序里有几句话我觉得对你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说:“德水不再从泥土里发掘精神,不再从父老兄弟母亲姐妹身上提纯理想。那种悲壮昂扬的力度消退了,有的是土地的本来。”你由此从《中原土》走向《黄河流年》,这是一个转折。侯登科还说“德水,一定在心灵深处留有一块青草萋萋的空地。”你自己怎么看这句话?
于德水:那些年我与侯登科有着比较深入的交流,当时的外部环境不像今天,我们彼此间都有很深的了解和理解。他的判断大致上也是准确的。
李江树:德水,你和侯登科在拍摄视角上有什么区别呢?
于德水:侯登科赋予摄影太多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我也经历过那样一个阶段,但我觉得摄影承载不起这些东西,所以我更愿意注重影像本身。
李媚:侯登科去世之前我们三个人有一次聊天,他讲得最多的是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村社会的发展。
李江树:侯登科具有“兼济天下”的使命感。
张惠宾:刚才李江树也提到,你更多是“独善”,是“坚持个人生活中的操守”,那么与侯登科的“兼济天下”比较,你是不是更倾向于“独善其身”?
于德水:那时被称为“摄影救国军”的那帮人做了很多事,我也是其中的参与者之一。只是在后来的摄影实践中,我逐渐地校正和改变了“摄影救国”的想法。潘科用一个词总结这段历程:“试错”。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概念。
“影像和这个现实世界有着一种割不断的基因关联,这是摄影令我着迷的理由。”
张惠宾:你怎么理解纪实摄影?
于德水:摄影被赋予的文化功能和存在方式越来越丰富,外延越来越大,但如果把摄影理解为一种文化方式的话,摄影的记录性在众多文化品种里仍然是以带有最根本、最内在的文化特质而存在的。
张惠宾:摄影技术与器材的进步对它有何影响?
于德水:从人类文化史来看,纪实摄影从视觉上满足了人类对历史的记录,这是它区别于其他文化方式的独有属性。它记录了历史,这种历史是真实的存在,即使在数码时代的今天,也不会被改变。人类需要这种记录以作为历史的证据而呈现,对原来的、以往的世界进行辨认。所以从根本上说纪实摄影的记录功能并没有被削弱。
张惠宾:曾有人说到你的照片不能拿来说明历史事件,见证时代发展。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于德水:从大的范畴来说,我拍摄的行为方式还算是属于纪实摄影。在历史长河中一个特殊的时段里发生着的社会变革是我的影像产生的背景。我不会干预对象,拍下来之后也不会再改变对象。但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我有我自己接收信息、记录信息和表现信息的特有方式。我在影像里确实不在意事件。
张惠宾:我提出另一个词,与纪实相对的不是艺术,而是“纪虚”。这个“虚”指个人的情感、生活的滋味,它是镜头的文化内涵。现实生活中有人是叙事的,说的是实的一面,但也有人是纪“虚”的,他要表达人的意识、情感等。
于德水:这个“虚”恰恰是由实而生发出来的。
张惠宾:它们互为一体,不可区分。比如拍一个老人,他的面孔、形态跟他的精神状态,笑也好、哭也好,是不可分割的。现在很多纪实的东西太具象了,缺少这种精神内涵。
于德水:这涉及到了一个较为深入的命题:艺术领域中表现形式“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关系。摄影由于获取影像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它的表现与具体物象的联系。我以为恰恰由此而不能忽视它作为构成形式存在的表现性。
张惠宾:摄影最让你迷恋的是什么?
于德水:摄影和现实世界的关系。早年学美术时,当我用线条、色彩把一个物体在二维空间的平面上,立体地描画出来时,有一种很享受的成就感。对于画家来说,那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创作过程。但后来我莫名其妙产生了一种感觉:在茫茫世界里把一个具体的、非常微小的物体呈现出来,就要经历如此一番复杂的创作过程,那我如何去表现一个世界?我开始惧怕这个世界的浩大,对画画产生一种畏惧感。
多年以后当我手里的画笔换成相机时,我感到了自由和庆幸。
因为它可以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记录下来、表现出来,它消除了我以前的惧怕感,打开了我的心结。这是摄影吸引我的一个重要理由。但是今天我认为,一台照相机完成一个影像的时候,无论从文化性质去看,还是从个人生理或其他方面去看,影像和这个世界具有一种割不断的基因关联,这是摄影令我着迷的理由。
李媚:你觉得摄影让你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把握感,你可以把握住某些东西,把握住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不会让你无所措手足。
于德水:是。
张惠宾:你怎么评价自己的影像?
于德水:刚才谈到我的性格源于小时候产生的自卑心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缺少精神给养,感觉比别人少了很多东西。虽然后来通过各种方式“充电”,但在精神和知识领域,学到的越多,越感觉自己过去的无知。在摄影实践里,我会把自己最把握不定的东西,把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通过某个对象实现某种程度的展示。
与别人相比可能是缺点的东西,但如果我通过影像把它呈现出来,也许恰恰就成了一个人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追求的影像,是一个真实的表达和述说,它表现着一个生命个体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的生活体验和感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