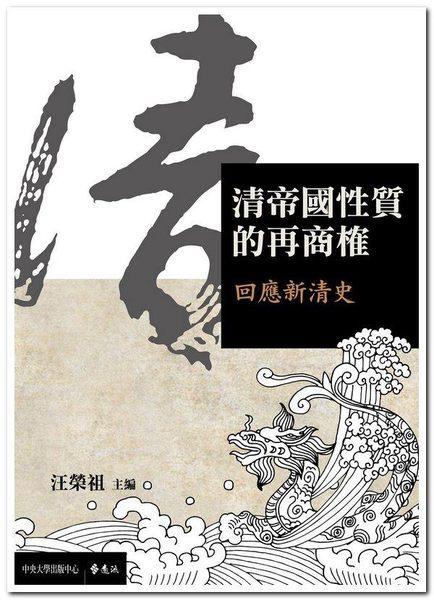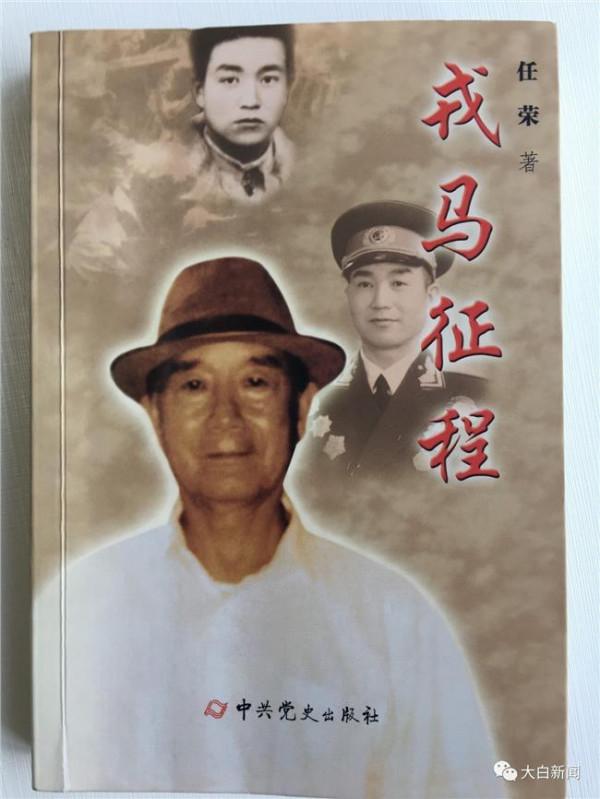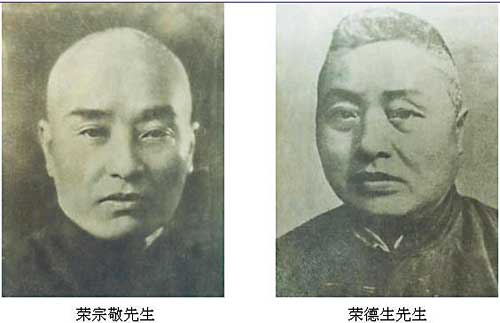姚大力汪荣祖 汪荣祖教授在华东师大谈两岸新文化史研究(ZT明清
(文 新民) 10月29日,在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办的“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台湾中正大学教授汪荣祖做了题为“欧风美雨下的两岸史学走向”的学术发言。
他对当前海峡两岸的史学动向作了探讨和研究,认为当前最值得思考的是如何面对正在蓬勃发展的新文化史研究。 他说,傅柯的研究所提供的具有颠覆性的方法,值得两岸史学界重视,至少提醒我们如何来处理与西方文化相当不同的中国文化,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变动性与特殊性。
他指出,新文化史有别于旧文化史,不仅仅是研究方法之异,研究课题也大异其趣,不再偏重学术、宗教、艺术、音乐等等,而讲求下层文化,群众的日常生活,物质文明,以及一般个人、性别、家庭与婚姻等议题,甚至涉及超越阶级的情绪、记忆、遗忘、感觉、期盼、痛苦、欲望、希望、知识制作诸问题。
这些议题所探讨的问题,不仅仅要追究历史是如何发生的,更要追究发生的事对他、她、以及他们的意义何在? 汪荣祖教授认为,新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不再是大学者、大艺术家、大音乐家,而是市井小民,甚至说文化史是“被压迫的故事”。
新文化史在讲小人物的故事时,采“叙事体”(narrative),重视“论述”(discourse),讲究语言结构与意义之间的互动关系,使无声的语言结构发声,使“文本”与“语境”之间能相互循环发明。
汪荣祖教授指出,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正在带动新文化史的研究,所谓“人类学模式至高无上地统筹文化研究”(the anthropological model reigns supreme in cultural approaches)。
人类学者因擅长诠释文化象征与仪式等课题,新文化史既然重视历史意义,自然有助于解析历史上各种象征与仪式所代表的意义,作为检验历史生活型态的起点。
汪教授说,文史哲原不分家,吾华如是,西方亦然。至十九世纪近代史学诞生,崇尚实证,才严格界定史学为“科学”的学科,与文学以及哲学分道扬镳。
不过,二十世纪以来,史学家不断取用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历史,若继续寻求新途径、新方法,进而参考文学批评理论以及认可历史书写在文字表述与文字结构上的重要性,似势所必至。
文史分而复合,亦势必冲击近代史学的定义,突破近代实证史学在方法上所设之限,从语言运用与修饰上追寻历史意义。 他认为两岸史学界值得考虑文学创作与历史书写在叙事方式上如何重遇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历史书写者是否愿意突破一成不变的叙事方式,愿意虚心瞧瞧现代小说家与诗人在叙事上的成效。
“一个有创造力的作家必具想象力的叙事经验,呈现人物与思想中诸多趋向的微妙互动。”史学家不必去仿效所有的文学叙事策略,至少可从小说家与诗人学到新的叙事经验。
文学与文学理论有助于寻找历史上失落的声音,并不是要把历史书写成为另一种的文学创作。文学可提供历史解释另类眼光,并非治史的唯一途径。 汪教授认为,整体而言,目前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包括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在内,都受到新文化史影响,在视野上以及方法上都得到启示。
政治史久被视为保守落伍的旧史学,但在新文化史的启示下,探讨政治活动的思想背景与政治文化,增添了新的生命。
新文化史所提供的概念、方法,以及研究典范颇多。 汪荣祖教授最后谈了注意克服新文化史的局限问题。他认为,新文化史把重点放在小人物上,以及讲究微观研究,虽开拓了史学研究的视野,但小人物与微观研究有局限性。过去几千年的历史毕竟主要由精英份子或大人物所缔造。他说,微观研究发掘了历史的深度,但微观之余,仍需要宏观来统筹,才不至于见树而不见林,甚至见叶而不见树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