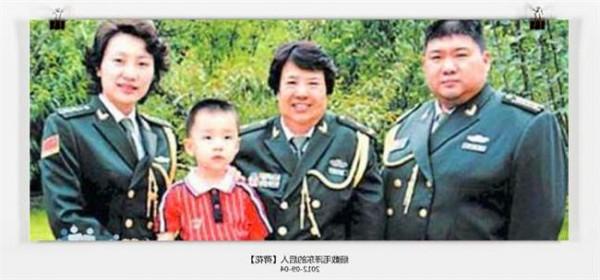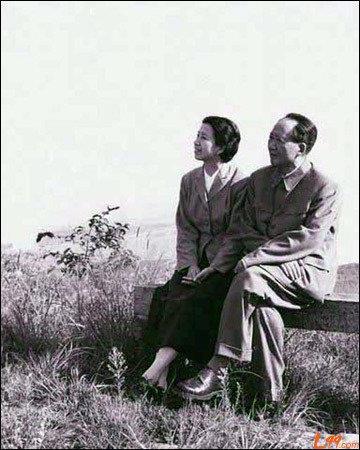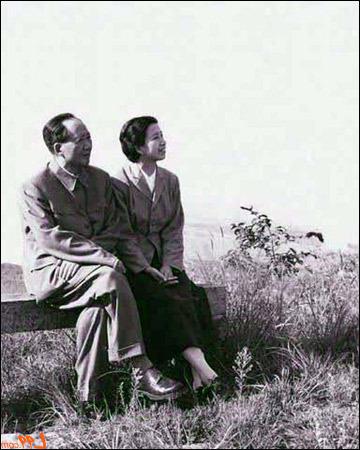毛泽东为何拒绝与贺子珍复婚
原载《实录毛泽东》,长征出版社/出版
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还亲自安排同贺子珍见面。尽管他早已同江青结了婚,但仍在尽自己所能关心贺子珍的生活。这是两位曾经倾心相爱,并且共过患难的战友之间的崇高情谊。
当年受毛泽东委托接贺子珍上山的水静(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的夫人)回忆说:
一辆“吉姆”径直驶进“180”院子,缓缓地停在台阶下面。已经在那里等候的毛主席贴身卫士封耀松,为我们打开车门,小心翼翼地扶出贺子珍大姐。我利索地跳下车,与小封一左一右地把大姐搀进屋,直上二楼。楼上共有三间房,毛主席住了两间,外面是会客室和办公室,里间是毛主席的卧室。紧靠楼口右侧有一间小房,是卫士的值班室。小封送大姐进里间时,我便到值班室稍事休息。
我靠在沙发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总算把大姐顺利地接来了。然而,这次会面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难说呀!我一边品味小封给我泡好的云雾茶,一边漫无边际地作出种种猜测。最终我默默地摇摇头,更坏的结果是不可能的了,喜剧性的结果也不会有。因为行前我听到主席自言自语地说过一句话,而对贺子珍大姐的现状我又非常了解。
我在好几年前就认识她了,而最近的一年多交往更加频繁,因为现在她就住在南昌。
小封走进值班室,给我换了一杯水,接了一个电话,又出去了。我看看手表,主席和贺子珍已经谈了半个多小时了。我为大姐暗暗祝福,希望他们能够谈得来,因为毕竟20多年没有见面了,而且她的身心健康又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至于主席,据我了解,他对大姐一直是很关心的,在一些事情上,还是很尊重的。10年患难夫妻留下的感情不是可以轻易抹去的,或者说,是永远抹不掉的。
贺子珍到江西之后,她的亲生女儿娇娇,多次到南昌来看她。据娇娇说,每次都是主席让她来的,而且总要带些贺子珍喜欢吃的东西和难买的药品。
有一回,娇娇带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同来看妈妈,看那神态,我估计他可能是娇娇的男朋友。娇娇已经二十二三岁了,到了谈朋友的年龄了。
一般说来,母女之间的感情是最为深厚的,何况娇娇是贺子珍的唯一亲骨肉,且又在异国落难时朝夕相处,相依为命。所以娇娇一来,贺子珍便显得非常高兴,而这一次则似乎有些兴奋。我去看她时,她主动告诉我:那个小伙子叫孔令华,是娇娇的同学。
“他们相爱了很长时间,现在要结婚了。”大姐笑嘻嘻地对我说,“主席写信来,让他们征求我的意见。”
“那是应该的。”我说,“女儿出嫁,不能没有母亲的意见。”
“嘿,他们彼此相爱,而且主席也同意了,我还能有什么意见?”她开心地笑道。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小孔各方面都好,就是有点胃病。”
我说:“那不要紧,在饮食上注意一点,很快就可以治好的。”
“我也这样想。”她点点头说,“主席考虑问题总是很周到的,身体是很重要的条件,他不会想不到。”
毛主席是个坚强的人,轻易不落泪,但是,为贺子珍就落过两次泪。一次是1937年底,贺子珍执意要去苏联,主席怎么劝说都没有用,终于走了,于是他哭了。另一次是1954年,贺子珍在广播中听到他的声音,引爆了在心中积抑多年的思念、痛苦与悲伤,严重损坏了神经系统,导致了精神分裂症。得知这个消息后,他又落泪了。这种眼泪,应该说是一种压缩在心的深层的被液化了的感情。
据我所知,主席曾多次给贺子珍写信,有时贺子珍还亲口告诉我,主席让娇娇带信来了,并且也会谈及信中的某些内容,如嘱咐她治好病、养好身体,征求她对女儿婚姻的意见等。这些一般听过就算了,但有一回在她身边的一位近亲告诉我一件事,却使我感触至深。
那位近亲说,娇娇每次来南昌,都带了主席的亲笔信,而且信的抬头总是“桂妹”两个字,这是因为贺子珍是在1909年桂花飘香的日子出生的,小名就叫桂花。可以想象,一声“桂妹”,足以使贺子珍回到几十年前井冈山苍松翠竹所掩映的脉脉柔情之中。
由此我又想到毛主席的著名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吴刚捧出桂花酒”句中的“桂花”,是不是贺子珍这支桂花呢?我想是的。这首词里的杨、柳、桂都是用以喻人的,杨、柳分别指杨开慧、柳直荀两位烈士,已为世人所知,但人们却忽略了桂是何人。因为文艺评论家们从未提及,这也许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贺子珍的小名,或者有碍于江青的忌讳吧。
至于贺子珍对毛主席的感情,更是一往情深、至死不渝。在苏联时,同志们都已经知道主席和江青结婚,有的便向她表示爱意。当她回国之前,又有人重提此事。她毫不考虑地说:“我一生只爱过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我不会有第二次爱情了。”
互相思念而又不能相见,是十分痛苦的,贺子珍的病,就是这棵扭曲的感情之树的苦果。那么毛主席呢?难道就不难受吗?我曾经对尚奎说:“主席为什么不跟贺子珍见一面呢?这对他来说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尚奎摇摇头,很严肃地说:“你不要把见见面这种事看得太简单了。
毛主席是全党全国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是人民的表率;他也要受中央的约束,而他的纪律性是很强的。再说,一旦江青知道了,即使只是见见面,也会大吵大闹,那影响多坏呀!”我仔细想了想,尚奎说的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领袖,他的感情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从这一点来说,远不如普通老百姓自由。
然而,毛主席到底也是人,并不是神,而且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终于决定撇开一切有形无形的障碍,和贺子珍这位曾和他共同度过了最艰难的历史时期的妻子,共同经历了10年峥嵘岁月的战友——尽管现在她已经不是他的夫人——见上一面。
这个使人振奋的消息,是尚奎告诉我的,同时交给我一个不同寻常的任务……
“水静,你马上收拾一下,今天下午就动身回南昌。”7月7日中午,尚奎郑重地对我说。
“什么事?怎么这么急?”我问。
“去把贺子珍同志接到庐山来,和朱旦华一道去。”尚奎说得很严肃,“毛主席要见她。”
我瞪大眼睛看着他,半天才反应过来。这本来是情理中的事,一旦成为事实,又觉得有些突然了。
“啊,这可太好了!”我几乎叫了起来。
“你听我说,”尚奎做了一个制止我大声说话的手势,说道,“这是一个特殊任务,主席强调要绝对保密。汽车上山之后,不要到这边别墅区来,要直接开到我们安排好的住处去。”又如此这般地作了许多具体的交代。
下午2点多钟,我便和朱旦华同志一道乘车下山。在车上,我们商量了一下用什么理由请贺子珍上山,并且统一说话的口径,以免节外生枝。因为尚奎叮嘱:在见到主席之前,不要让大姐知道是主席要见她,主要是怕她过于激动而触发旧疾。并且说,这也是主席亲自交代的。
不到6点,我们便到了南昌。车过八一桥,便直向三纬路贺大姐的住所驶去。
大姐恰好在厅堂休息,一见我们进屋,又是让座,又是倒茶,非常热情。在问过大姐的生活起居之后,我便“言归正传”了。
“大姐,今年南昌太热,省委请你到庐山去休息几天。”我用一种传达指示的口气说,“我们俩刚从庐山下来,省委特地派我们来接你。”
大姐很高兴,说了一些感谢省委关心之类的话。见她欣然同意,我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那就请你准备一下,大姐。”我说,“明天下午3点我们来接你好吗?”
第二天,我们准时把车开到大姐住处,大姐上车后,我们便向庐山飞驰。一路之上,我们和大姐尽谈些轻松、高兴的事,说说笑笑,非常愉快。汽车在成熟中的田野起伏,只觉得芬芳扑鼻,满眼金辉。一片丰收的景象,跟着我们风驰电掣,更使我们心花怒放。几乎在不知不觉间,便到了庐山牯岭。
按照尚奎事先的安排,我们把车子直接开到特地为大姐准备的住处:涵洞左侧的“28”号房。这里附近只有几幢房子,都没有住与会议有关的人员,服务员也只有一人,不会引起别人注意。
朱旦华已经回到自己的住处,只留下我陪同贺子珍大姐。我们住的房间,摆了两张床,电话、卫生间一应齐全。吃过饭,安排好大姐休息之后,我先给尚奎挂了电话,报告我们到达的消息。尚奎叫我陪着大姐,不要随便离开。接着,我又和主席联系上了。
“客人的情况怎么样?”主席问道。他好像有些激动。
“一切都好。”我回答说。
“那好,你等着我的安排。”主席说。
次日中午,我趁大姐午睡的机会,独自乘尚奎的车,到了“180”。主席坐在沙发上吸烟,正在等我。我把如何接大姐上山的事,简略汇报了一下,并且告诉主席,大姐情绪很好,记忆力也还可以,能回忆许多往事。
“很好。”主席点点头说,“今天晚上9点钟,你坐尚奎同志的车,送她到我这里来。”
“好的。”我说。
“这里已经安排好了,身边的几个同志都有事下山去了,只有小封留下值班。”主席又说,“门哨认得尚奎同志的车号,不会过问的,开进来就是了。”
我想起旦华是原毛泽民的夫人,她们之间的感情会更亲近些。而且我又是和旦华一同接大姐上山的,便问主席:“要不要找朱旦华同志一道陪大姐来!”
“不用了,你一个人就可以。”主席回答说。
显然,主席很谨慎,想要尽量缩小知情面。一切问清楚了,我便起身告辞:“主席,如果没有别的事,我就走了。”
主席紧锁着眉头,使劲抽着烟,心事重重的样子。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像自言自语似的说:“咳,希望能一拍即合。”
我不知道主席这句话的内涵,也不敢多问,只是说:“再见,主席,晚上9点我一定陪大姐来。”
待我赶回“28”号时,大姐午睡还未醒。
我很困,但是睡不着,直到我坐在“180”值班室等候大姐时,仍然处在一种十分兴奋的状态之中。
“铃、铃、铃……”
清脆的铃声把我从回忆中拽了出来。这是主席召唤小封。我看看手表,已经过了1个多小时了,我捉摸,也许谈得不错吧,要不怎么谈这么久呢。人哪,总是把事情往好处想。
一会儿,小封把贺大姐扶进值班室,让大姐坐下,然后对我说:“主席请你去一下。”
我走进主席房间时,只见他手里夹着烟,脸色很不好。
“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
我盯着他苍白的脸,不知说什么好。
“她很激动,你要注意她的情绪。”他夹着烟的手朝我点了一下,说,“明天你就送她下山,下山以前,你一步也不要离开她。现在她已经知道我在山上,怕她出去碰到熟人,那不好。延安时期的熟人很多呀,有些就住在你们附近。”
我已经注意到了,在离“28”号不远的河南路,就住了不少参加会议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康生也住在那里。我想,主席考虑问题真周到,连这样一些细枝末节都了解到了。
“主席,请放心,我保证不会离开她一步。”我说。
“还有一件事,最好回去就办。”主席加重语气说,“她拿走了我三小瓶安眠药,很厉害的,吃多了会出事。你要想办法从她手里拿下来。”
“好,我会办妥的。”我说。
我很清楚,这是一件颇为棘手的事。我怎么开这个口呢?大姐是很敏感的,如果说话不当,引起她的怀疑,那就糟了。要是不能从她手里拿下来,后果更为严重。主席睡眠不好,有个吃安眠药的习惯,他吃的安眠药是高效的,如果服用不当,特别是在精神失常的时候,肯定要出问题。否则,主席也不会这么着急呀。
从主席房间出来,到陪大姐回住所,我脑子不停地转,可就是想不出一点办法。
大姐一直处于兴奋状态,睡到床上了,还一直说个不停,如果突然插进一个毫不相干的安眠药问题,非得把事办砸不可。于是,我只好在一旁静静地躺着,偶尔说一两个字表示我在听。至少她现在还没有想到吃安眠药,真要吃了,我再制止不迟。两张床相隔不过二三尺,彼此的一举一动,互相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她又一次提到主席的生活时,我不经意地问了一声:“大姐,你觉得毛主席的变化大吗?”
“别的都和以前一样,就是老多了。”她回答说,“我看他很疲倦,烟抽得很厉害,安眠药也吃得很多。”
听她提到了安眠药,我灵机一动,立即抓住这个话题不放。
“是呀,主席太忙了,休息不好,听说要吃两次安眠药才能入睡哩。”我紧接着说,“尚奎也是这样,工作一紧张,没有安眠药就睡不着觉。”我像忽然想到似的说,“对了,听说大姐在主席那里拿了几瓶安眠药是吗?能不能给我看看,主席吃的是哪一种,我好给尚奎搞一点。”
大姐待人一向很客气,而且我们之间交往很多,已经建立了感情,所以听我这么一说,马上找出那三瓶安眠药,侧过身子递给我,说:“你看嘛,就是这种。”
“这种呀,我还没见过哩。”我接过药瓶,边看边说,然后坐了起来,侧过身去说道,“哎,大姐,这药给我好不好?我给尚奎吃吃看,不知效果好不好。”
“好嘛,你拿去就是了。”大姐说。
我暗暗地嘘了一口气。
第二天一早我给小封挂了一个电话,告诉他安眠药已经拿到了,请主席放心。
近年来,这段曾经鲜为人知的往事被披露出来,成了文学作品的热门话题,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以致以讹传讹。
水静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一些误传作了澄清。她写道:
近些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说的人越来越多了,贺子珍成了一些文章作者的热门题材,许多报告文学陆续问世。关于贺子珍庐山见毛主席一事,成了必不可少的章节。我也曾接待过几个作者的采访,所以好几个作品里都有水静的名字。我认为,写老一辈革命家,写贺子珍这样的老同志,写他们走过的坎坷道路,写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应该提倡的好事。但是,必须严肃认真,必须实事求是。遗憾的是,有些作者却没有遵循这个起码的原则。
我早就想对这个问题表示自己的看法了。因为,一些作品中既然提到我的名字,实际上是告诉读者,我是材料的提供者。既如此,对于其中真伪,我就不能保持缄默。再则,作为一个知情人,我有责任把真相告诉人们,以正视听。
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我觉得至少有几桩事情需要澄清。
一、贺子珍到达庐山之后,接触面极窄,顺序为我、朱旦华、“28”号房服务员、司机、卫士小封和毛主席,除此之外,没有见任何人。尚奎和省委其他负责同志都没有去看她,为的是缩小知情面。而有的文章却任意给贺子珍“增加”护士、女伴,还“设计”了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交谈对象,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
二、贺子珍会见毛主席的那个晚上,“180”里面只留下了小封一人值班,连卫士长李银桥都出去了。我陪大姐进屋时,没有见到任何别的人。大姐到室内与主席谈话,我一直在值班室等候,也不见任何人来访。可是有的文章却说,贺子珍听到彭德怀用“雷鸣般的吼声”和毛主席“争吵”。彭德怀出来的时候,还“很紧”、“很久”地与贺子珍握手。这是根本没有的事。
三、有的文章还写道,毛主席那天晚上请贺子珍吃了饭,喝了酒,然后又趁着“皎洁”的“明月”,陪贺子珍观赏庐山夜景。所有这些,包括每一句对话,每一个细节都是毫无根据的,连一点影儿都没有的事。
四、这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一直在北戴河避暑,是主席亲口说的,而且有据可查。而有些文章却说,当时江青正在杭州,接到庐山一个秘密电话,便立即赶来,大闹一番。其实这年江青根本没有上庐山。有的文章还说,王光美“邀了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曾志、郝治平、水静等夫人,打算到美庐(即‘180号’房)来向‘江大姐’问候”,结果吃了闭门羹;于是第二天又再次去拜会。
这是很荒谬的。1961年庐山会议时,江青才上了庐山。王光美与江青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了,她会组织这种“夫人造访团”吗?而蔡、邓、康、曾这些德高望重的大姐,会一而再地结伴去“问候”那个“江大姐”吗?就是像我和佳楣、胡明、余叔这批较为年轻的夫人,也不愿和江青往来,觉得她太傲慢了,而夫人们之间的交往,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
因此,一些作者的那种写法,不仅无视事实,且有损于几位大姐和夫人们的声誉。
五、贺子珍患有精神分裂症,平时,头脑很清楚,记忆力也蛮好。一旦发病了,便畏惧、怀疑,总觉得有人在害她。这一点是无需回避的,否则,好多事就说不清楚;同时,这也不会损害大姐的形象。有的作者是出自好意而隐讳,这还情有可原;而有的则是基于某种政治褒贬的需要,那就不足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