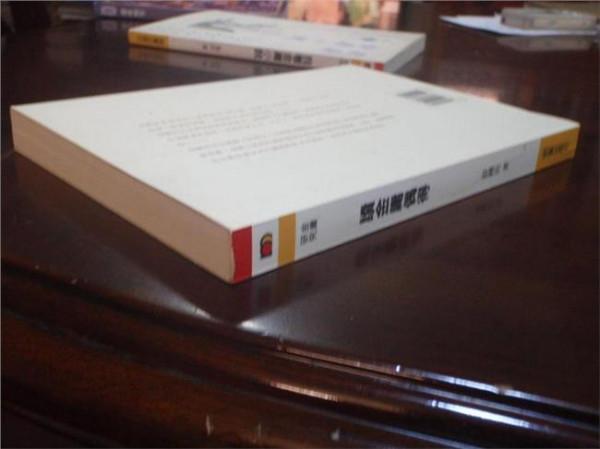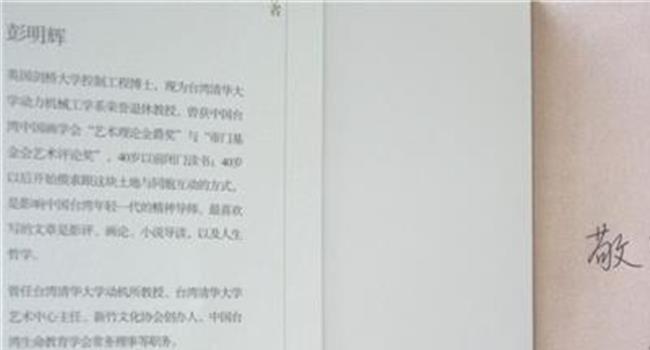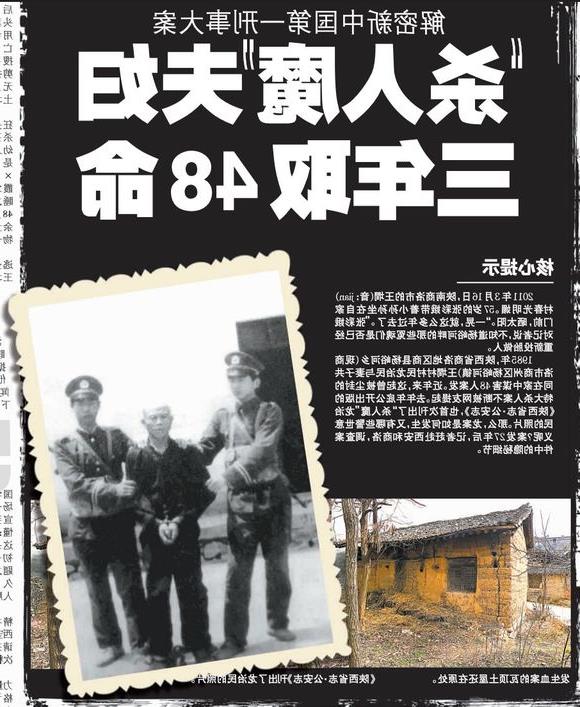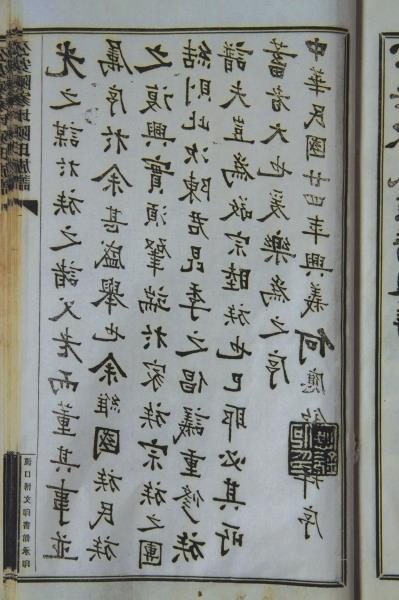舒国治《遥远的公路》 遥远的公路——舒国治
一九八三至一九九○这七年间,我恰巧待在美国,其中有三、四年开车乱跑了很多地方。愈多跑地方,愈忘了何处是目的地,在外的时间愈久,愈不知道要不要回家。每天晚上睡在自己车上,不忧虑今天是星期一还是星期六,不知道别人早上要上班下午要下班。
后来我想了一想,我在美国公路上无休无尽的奔来奔去,大概因为那种惰性及游魂血液吧。
透过挡风玻璃,人的眼睛看着一径单调的笔直公路无休无尽。偶尔瞧一眼上方的后视镜,也偶尔侧看一眼左方的超车。
耳朵里是各方汽车奔滑于大地的声浪,多半时候,嗡嗡稳定;若轰隆巨响,则近处有成队卡车通过。 每隔一阵,会出现路牌,「DEER CROSSING」(有鹿穿过),「ROAD NARROWS」(路径变窄),这一类,只受人眨看一眼。
在怀俄明州,远处路牌隐约有些蔽翳,先由宽银幕似的挡风玻璃接收进来,进入愈来愈近的眼帘,才发现牌上满是子弹孔,随即飞过车顶,几秒钟后再由后视镜这小型银幕里渐渐变小,直至消逝。
在犹他州原野看到的彩虹大到令人激动,完美的半圆,虹柱直插入地里。
大自然对驱车者偶一的酬赏。四十号州际公路近德州Amarillo路旁,十辆各年份的凯迪拉克车排成一列头朝下,也斜插在地里,当然,也是为了博驱车者匆匆一觑。 当午后大雨下得你整个人在车上这随时推移却又全然不知移动了多少的小小空间完全被笼锁的灰暗摸索而行几小时后,人的思绪被冲涤得空然单净。
几十分钟后,雨停了,发现自己竟身处蒙塔拿庞然大山之中,那份壮阔雄奇,与各处山棱后透来的黄澄澄光芒,令你心摇神夺,令你觉得应该找点什么来喟叹它。
这种景光,我突然有冲动想要对着远山抽一根烟。那年,我已戒了好一阵子烟了。 八百哩后,或是十二天后,往往到了另一片截然不同的境地。
距离,或是时间,都能把你带到那里。景也变成风化地台了,植物也粗涩了,甚至公路上被碾死的动物也不同了。 空荒与奇景,来了又走了。
只是无休无尽的过眼而已。过多的空荒挟带着偶一的奇景,是为公路长途的恒有韵律,亦譬似人生万事的一径史实。当停止下来,回头看去,空空莽莽,惟有留下里程表上累积的几千哩几万哩。
西行,每天总有一段时光,眼睛必须直对夕阳,教人难耐。然日薄崦嵫的公路及山野,又最令人有一股不可言说之「西部的呼唤」。
此刻的光晕及气温教人瘫软,怂恿人想要回家,虽然我没有家。我想找一个城镇去进入。这个城镇最好自山岗上已能俯见它的灯火。 长期的公路烟尘撞击后,在华灯初上的城镇,这时全世界最舒服的角落竟是一个老制的橡木booth(卡座)。
如果桌上装餐纸的铁盒是Art Deco线条、镀银、又抓起来沈甸甸的,咖啡杯是粉色或奶黄色的厚口瓷器,那么这块小型天堂是多么的令人不想匆匆离去。
即使吃的也必只是那些重复的汉堡、咖啡、hash brown(碎炒马铃薯)、omelette(烘蛋)、chicken soup(鸡丝与面条炖汤)等。
夏夜很美,餐馆外停的车一部部开走,大伙终归是要往回家的路上而去。而我正在思索今夜宿于何处。 我打算睡在这小镇的自己车上。
睡车,或为省下十六或十八元的住店钱,或为了不甘愿将刚刚兴动的一天路途感触就这么受到motel白色床单的贸然蒙蔽,或为了小镇小村的随处靠泊及漫漫良夜的随兴徜徉的那份悠闲自在,都可能。
睡车,最好是挑选居民停好车后钥匙并不拔出的那种小镇,像佛芒州的Woodstock。
而不是挑选蒙塔拿州的Butte那种downtown像是充满能单手卷纸烟的昔日汉子的城市。南方有些禁酒小镇如亚拉巴马州的Scottsboro看来也很适合睡车,只是人睡到一半,突然音乐声吶喊声大作,并且强光四射,原来是周六夜青少年正在「游车河」(cruising)。
夜晚,有时提供一种极其简约、空寂的开车氛围,车灯投射所及,是为公路,其余两旁皆成为想象,你永远不确知它是什么。
这种氛围持续一阵子后,人的心思有一种清澈,如同整个大地皆开放给你,开放给无边际的遐思。有些毫不相干的人生往事或是毫无来由的幻想在这空隙送了出来。美国之夜,辽辽的远古旷野。
当清晨五点进入吐桑(Tucson, Arizona)或圣塔非(Santa Fe, New Mexico)这样的高原古城,空荡荡的,如同你是亘古第一个来到这城的人,这是非常奇妙的感觉。 千山万岭驱车,当要风尘仆仆抵达一地,这一地,最好不是大城,像纽约。
纽约太像终点。你进入纽约,像是之后不该再去哪里;倘若还要登程,那么在MacDougal街或Bleecker街的咖啡店我会坐不住,只想买一杯Dunkin Donuts的纸杯咖啡带走。
小镇小村,方是美国的本色。
小镇小村也正好是汽车缓缓穿巡、悄然轻声走过、粗看一眼的最佳尺寸。通往法院广场(courthouse square)的镇上主街,不管它原本就叫Main Street,或叫Washington Street,或叫Central Avenue,常就是US公路贯穿的那条干道。
为了多看一眼或多沾一丝这镇的风致,常特意在此加点汽油,既要加油,索性找一个老派的油站,一边自老型的油泵中注油,一边和老板寒暄两句,顺便问出哪家小馆可以一试之类的情报。
一两分钟的闲话往往得到珍贵惊喜。他说这里没啥特别,但向前十多哩,有本州岛最好的猪排三明治;「掷一小石之远」("just a stone's throw",他的用字),有最好的南瓜派……街尾那家老药房有最好的奶昔,我小时每次吃完,整个星期都在企盼周末快快到来……你不妨下榻前面五哩处那家motel,当年约翰.
韦恩在此拍片就住过……。 那个猪排三明治的确好吃,南瓜派我没试,老药房的老柜台如今不见任何一个小孩,倒有稀落的三两老人坐着,像是已坐了三十年没动,我叫了奶昔也叫了咖啡。
咖啡还可以,奶昔我没喝完。记忆中的童年总是溢美些的。 我继续驱车前行,当晚「下榻」在一百多哩外另一中型城镇里的自己车上。
这些三明治或是有故事的motel,我仍尝过许多,但加油站那一两分钟搭谈所蕴含的美国民风民土往往有更发人情怀的力道。
譬如说,美国人有他自有的历史意趣,说什么「约翰.韦恩当年……」说什么「小时候我……」即使不甚久远,他也叹说得遥天远地。
或许美国真是太大了,任何物事、任何情境都像是隔得太远。
当无穷无尽的公路驰行后,偶尔心血来潮扭开收音机,想随意收取一些声音。几个似曾相识的音符流洒出来,听着听着,剎那间,我整个人慑迷住了,这曲子是Sleep-walk,一九五九年Santo & Johnny的吉他演奏曲。
我几乎是渴盼它被播放出来一样的聆听它,如痴如醉。我曾多么熟悉它,然有二十年不曾听到了,这短短的两三分钟我享受我和它多年后之重逢。
这些音符集合而成的意义,变成我所经验过的历史的片断,令我竟不能去忽略似的。 而这些片断历史,却是要在孤静封闭的荒远行旅中悄悄溢出,让你毫无戒备的全身全心的接收,方使你整个人为之击垮。
于是,这是公路。我似在追寻全然未知的遥远,却又不可测的触摸原有的左近熟悉。
有时一段笔直长路,全无阻隔,大平原(The Great Plains,如爱荷华,内布拉斯加,南达科打)上的风呼呼的吹,使我的车行显得逆滞。
为了节省一些车力,遂钻进一排货柜车的后面,让前车的巨型身体替我遮挡风速。当前行的五、六辆货柜车皆要超越另一部慢速车──如一辆老夫妇驾驶的露营车(RV)──时,你会看到每一辆货柜皆会先打上好一阵左方向灯,接着很方正的、很迟钝的、很不慌不忙的进入内车道,超过了那辆慢车,再打上一阵右方向灯,再进入外车道。
就这样,一辆完成,另一辆也完全如此,接着第三辆、第四辆、第五辆,然后是我,我于是也不自禁的很方正的、很不慌不忙的,打灯、换道、超前、再打灯、然后换回原道。
完成换道后,我听到前行的货柜车响了两下喇叭,又看到驾驶的左手伸出在左后视镜前比了一比,像是说:「Good job!」我感到有一丝受宠若惊;他们竟然把我列入车队中的一员。
再美好的相聚,也有赋离的一刻。这样的途程持续两三个小时,终于他们要撤离了。这时我前面的货柜车又很早打起右灯,并且在转出时,按了两声喇叭,如同道别;我立然加上一点速度,与他们平行一段,也按了两声喇叭,做为道别,以及,道谢。
我在路上已然太久,抵达一个地点,接着又离开它,下一处究竟是哪里。
这是一个我自幼时自少年一直认同的老式正派价值施放的辽阔大场景,是Ward Bond、Robert Ryan、Sterling Hayden、Harry Dean Stanton等即使是硬里子性格演员也极显伟岸人生的闯荡原野,是Sherwood Anderson、Nelson Algren、Raymond Carver文字中虽简略两三笔却绘括出既细腻又刻板单调的美国生活原貌之受我无限向往的荒寥如黑白片摄影之远方老家。
老旧的卡车,颓倒的栅栏,歪斜孤立的谷仓,直之又直不见尾尽的highway(公路)与蜿蜒起伏的byway(小路),我竟然毫不以之为异地,竟然觉得熟稔之至。
而今,我一大片一大片的驱车经过。 河流中,人们垂钓鳟鱼,而孩子在河湾中游泳。
一幢又一幢的柔软安适的木造房子,被建在树林之后,人们无声无息的的住在里面,直到老年。树林与木屋,最最美国的象征。许多城镇皆自封为「Tree City,USA」。
如Ann Arbor,如Nebraska City。太多的地名叫Spring field,叫Woodstock,叫Mount Vernon,叫Bowling Green。太多的街名叫Poplar,叫Cherry,叫pine,叫Sycamore。
而我继续驱车经过。美国小孩都像是在tree house(树屋)中游戏长大,坐着黄色的学童巴士上学。檐下门廊(front porch)是家人闲坐聊天并茫然看向街路的恬静场所,这习惯必定自拓荒以来便即一径。
每家的信箱,可以离房子几十步,箱上的小旗,有的降下,有的升起,显示邮差来过或还没。无数无数的这类家园,你随时从空气中嗅到草坪刚刚割过的青涩草香气,飘进你持续前行的汽车里。
啊,美国。电影《意兴车手》(Easy Rider)中的杰克.尼柯逊感叹的说:「这曾经是真他妈的一个美好国家。
」(This used to be a helluva good country.) 如今这个国家看来有点臃肿,彷佛他们休耕了太长时间。
爱荷华画家Grant Wood(1891-1942)所绘American Gothic中手握草叉的乡下老先生老太太,不在农庄了,反而出现在市镇的大型商场(shopping mall),慢慢荡着步子,两眼茫然直视,耳中是easy listening音乐(美国发明出来献给全世界的麻醉剂),永远响着。
坐下来吃东西时,举叉入口,咬着嚼着,既安静又没有表情。光阴像是静止着的。这个自由的国家,人们自由的服膺某种便利、及讲求交换的价值。
家中的药品总是放在浴室镜柜后,厨房刀叉总是放在一定的抽屉里,每家一样。冰箱里总放着Arm & Hammer Baking Soda( u手臂与鎯头」牌的烘烤用苏打粉──用来吸附臭味),每家一样。
而我,驱车经过。 累了。这里有一片小林子,停车进去走一走。树和树之间的地面上有些小花细草,伸放着它们自由自在少受人扰的细细身躯。
不知道在哪本嬉皮式的杂书上看过一句话:「如果你一脚踩得下六朵雏菊,你知道夏天已经到了。」 停在密西西比河边,这地方叫Natchez under the Hill,没啥事,捡了一块小石,打它几个「飞漂」,然后再呆站一两分钟,又回返车子,开走。
常常几千哩奔驰下来,只是发现自己停歇在一处荒弃的所在。
一波起伏的丘冈层层过了,不久又是一波。再不久,又是一波,令我愈来愈感心魂痴荡,我不禁随时等待。
难道像冲浪着一直等待那最浑圆不尽的浪管;难道像饱熏大麻者等待Jimi Hendrix下一段吉他音符如鬼魅般再次流出? 我到底在干嘛?我真要这样穷幽极荒吗? 在路上太久之后,很多的过往经验变得极远。
它像是一种历劫归来,这个劫其实只有五星期,然再看到自己家门,觉得像是三十年不曾回来一般。
在路上太久之后,很多的过往经验变得极远。好些食物,后来再吃到,感觉像几十年没尝过般的惊喜。
抵西雅图后在朋友家吃了一颗牛奶糖,几令我忆起儿时一样的炫然欲泪。 在路上太久之后,很多的过往经验变得极远。
我在车上剪指甲,这里是佛芒州的Norwich,突然想,上次剪指甲是何地?是Charlottsville?是Durham?抑是Oxford? 有些印象竟然很相似。
今天中午进入一个小餐馆,竟觉得像以前来过;一样的长条吧台,一样的成排靠窗卡座,收帐台背后的照片摆设竟然也一样,甚至通抵这餐馆的街道也一样。但跟哪一家餐馆相像?却说不上来。
我只知道,这个镇我从来没来过。 八百哩后,或是十二天后,往往到了另一片截然不同的境地。 三十个八百哩之后,或是三十次十二天之后,景色、植物或是碾死的动物最后全都不见了,剩下的只是一股──一股朦胧。
好像说,汽车的嗡嗡不息引擎转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