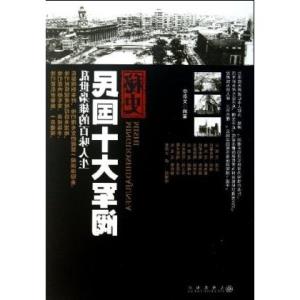施剑翘巧遇孙传芳女儿 孝女施剑翘佛堂射杀军阀孙传芳案
读了《施剑翘复仇案》这本书后,才得知军阀孙传芳被施剑翘经过长达十年的精心策划射杀在佛堂上。同时从书中也得知,另一个军阀,外号狗肉将军的张宗昌也被为了报私仇所刺杀,两个杀人法的下场一样,经过审判蹲了几年班房后都得到了政府的特赦,获得自由身;抗日战争时期,施剑翘的个人复仇史正和为国报仇的号召,成为爱国妇女的代表,发动合川献机运动,所谓用污水把自己洗的干干净净。
民国史之复杂和混乱,传统与现代的纠结从这本书就可以窥见一隅。 案情并不复杂,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南马路清修院居士林主持诵经仪式的下野军阀孙传芳被普通女子施剑翘枪杀,这就是民国轰动全国的所谓“血溅佛堂”的刺孙事件,在审判阶段以及后世,这个事件被以小说、戏剧、传记文学和广播影视作品的形式广泛流传。
施剑翘杀人事件本身并不复杂。
她刺杀孙传芳是为了报其父施从滨十年前被孙俘虏并残忍杀害的血海深仇。 七十年后,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林郁沁以历史学家的眼光重新审视施剑翘案,基于此案发生之后的各方争执带来的复杂性,这个案子的后面的复杂性,就表现在传统儒家的以情为核心的伦理本位和移植于以契约精神和法制传统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冲突;为了维护公共秩序的侠客义举和无能官员之间的冲突;更值得一提的是,林郁沁还以此为基础,着重探讨了近代以来公众同情对中国政治文化所起的影响作用。
中国在汉独尊儒术引经注律来,礼的核心“情”成为了决断重大案子与处于困境中的案子的最终依据,“百善孝为先”承认了“孝”的基础地位和“亲亲相隐”赋予了复仇的道德义务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施剑翘事件发生后,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等各种“表演形式”,反复向公众陈情、诉苦,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替父报仇的孝女和道德完人的正义形象。
儒家认可的这两大美德落实到施剑翘案上,导致大众受其感染,响应极为热烈,其情绪经过追求轰动效应的媒体的推波助澜,使有利于施剑翘的消息通过各种方式不胫而走,施剑翘受到舆论的广泛赞美与肯定,整个舆论一致认为替冤死的父亲报仇实为值得歌颂的义举,其是一种正义的行为,不仅不应该得到惩罚,还应得到赞美。
再加上据说孙传芳在当时又与日本有所勾结,是所谓的“恶人”,在这种近似于一边倒的意见之下,受害者家属希望完全依法判案的呼吁显得极为微弱。
司法部门在无法完全忽视大众的意见的前提下,判处施剑翘七年有期徒刑,最后被一纸中国特色的“特赦令”给予了其自由身,国家默认施剑翘复仇的正当性,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整个县或省以党部的名义上书中央请求必须要宽大处理,大众旷日持久的宣传和请愿运动,使得大众和舆论的压力过于强大,对司法部门和国民党施以压力,是施剑翘获得特赦于轻判的主要原因,可以说这是以情黜法的典型。
按照对现代化的理解,司法审判不仅讲的制度上的独立性,而且极力将情感因素排斥在外,民国已经经过了晚清法制改革、民初引进西方法制、五四对儒学传统的批判,从理论上早已将情的因素驱逐于法律之外,对于建设以司法公正为特征的现代国家为目标的国民政府,司法审判更应该得到制度上的保障。
施剑翘之所以会获得这么一个善果,基于许多原因,一个是以党代国导致了对司法独立体制的侵蚀,这是其能获得轻判和特赦的主要原因;一个就是近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为传播信息提供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手段,给公众提供了一个新的表达意见的机会,使大众意见以所谓的民意更好地表达出来,政府代表民意却是民主时代政治的基本逻辑,国民政府的党国威权体质为了取信于民,不得不随所谓的民意,导致了对司法独立的侵蚀。
林郁沁写这本书,还隐喻了她独特的视角,认为此种公众同情的情绪,虽然无形,实际上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威,小到影响司法,大到影响国家政策,在近代政治文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林郁沁也敏锐的警觉到,这个无形的公众同情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事件上有不同的表现,也许会代表正义,起到弥补国家法律不足的作用;或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从某一方面冲击了党治,以其独特的方式构成政治参与。
但是从消极负面上也可以看到,公众的同情也有可能是非理性的。
尤其被大众媒体操纵以后,可能使此种意见成为一种极端性的诉求。这种诉求积累到一起,可能取得无可匹敌的话语权,编织成一个铺天盖地的网络,逐渐形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民愿或民意。谁掌握了这种代表民意的话语权,就可能以情为武器,达到置对手于死地的目的。
典型如北伐时期因“民怨极大”而进行的私自枪杀,土改中的诉苦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各式判决大会等。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民国时期公众同情的兴起与影响”,从副标题就可以看出来这本书的主题,那就是公众“舆论”对这个事件的影响力和评判。
在中国战国年代,虽然“孟子”就提出了“民意”为国之根本的看法,但其实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中,民意根本无足轻重,原因就在于国家的话语权掌握在获得了学位的有文化和知识的儒士手中,所谓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野,虽儒家希望尽可能广泛地与百姓分享知识,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但是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受教育人的非常少,导致了许多平民百姓也没机会和能力分享读写能力以及学问,结果导致了儒家的教育最后还是保留在上层社会的内部了,这样一套可以为大众和儒家共享的思想需要的话语并没产生,使得大部分中国人无法真正参与公共事务。
民国之所以会出现公众同情的兴起,并且影响了国家的政治、社会和法制,原因就在于,这个阶段白话文报纸的兴起,他们可以通过报纸杂志的宣传,结社、请愿和游行等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官方进行游说,试图让自己的意见影响政治。
西方教育在民国的举办开展以及大量的可以和普通百姓沟通共享的词语从日本的翻译介绍,为中国普通百姓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语言这个媒介。
在当代中国,其实有许多这样的典型案例,比如迫于强大舆论的许霆盗窃案,还有药家鑫案等都是非常典型的公众舆论对审判的影响。导致这些普通的案件之所以会引发全民性的舆论争执,在我个人看来,大众认可的美德依然没有成为立法的基础,法律和制度代表的正义理念和人道原则脱离了公众对其的共同分享,立法者只是单方面的从制度和社会层面去看待理解公众,没考虑到规范能力,使得立法司法与大众的情感距离太远,让他们感觉不到法内情的体现,也感觉不到法对社会正义的主持。
在中国传统帝制时代,“情”可以是理想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基础,又可化为扰乱社会和睦的自私冲动,当这个暧昧的复杂的定义模糊的又影响着中国哲学和文学以及文化的“情”字在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中转化为公众同情时,其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双刃剑的角色,时至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