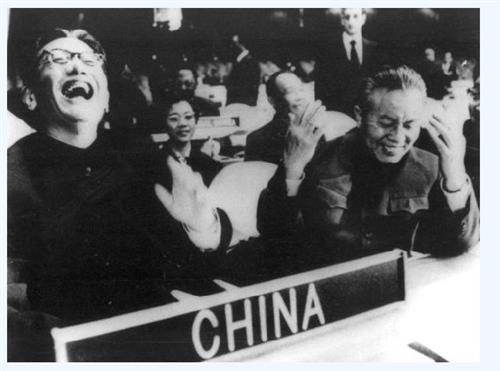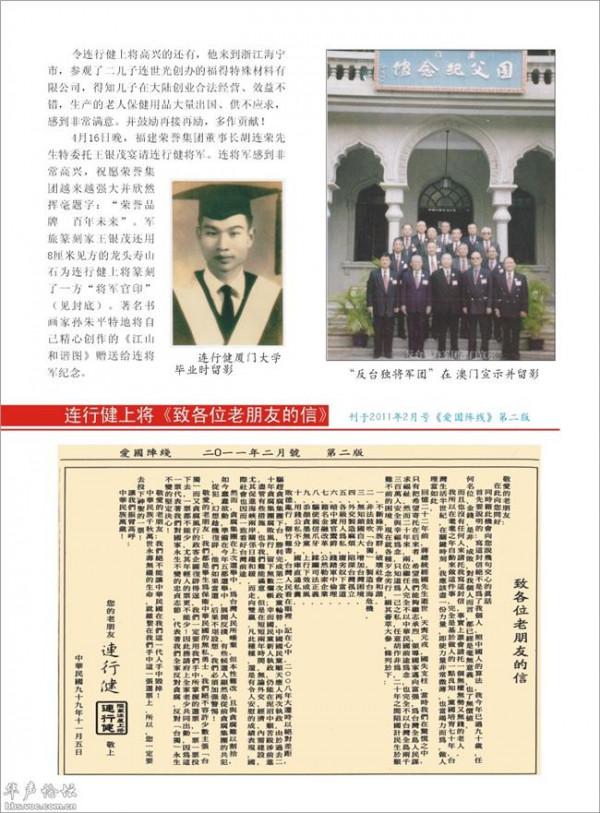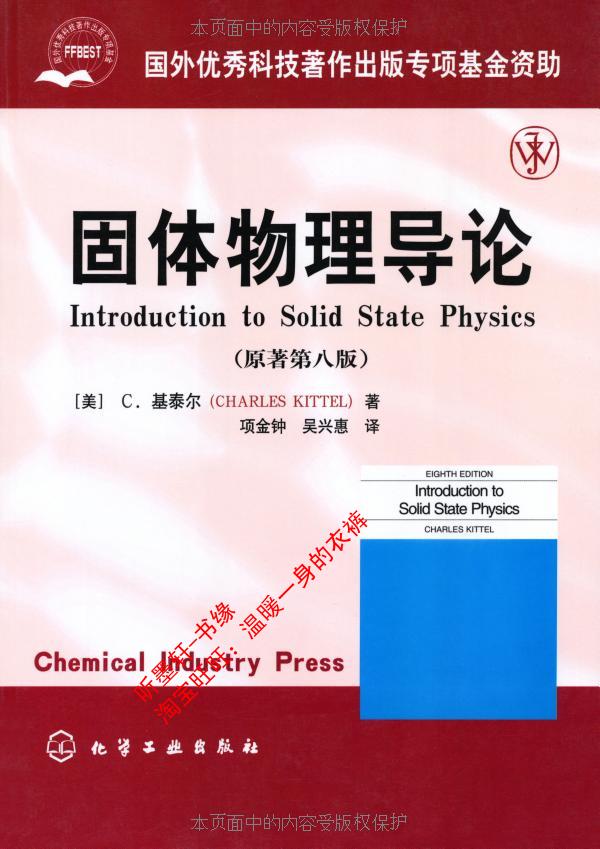大学的根本黄达人 黄达人先生为你解读大学的根本
目前,很多高校响应“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号召,积极制定综合改革方案,其实综合改革方案与学校规划建设方案不同。“规划建设方案”主要是解决“围绕发展目标要做什么?”的问题,而“综合改革方案”是突出“为达到目标要改些什么?”的问题。
我对做规划有两个基本认识:第一,规划宜粗不宜细,规划不是计划;第二,学科怎么弄,要听教授的;但学科如何布局,行政决策的味道应该更重一些。因为教授的特点是学科本位,否则就一定称不上好教授。
在春季工作会上,学校提出了“大团队、大项目、大平台”的思路,我觉得中大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确实需要考虑这个问题,这也的确是我们的弱项。为此,学校提出为实现“三大”创造条件的倍增计划。我理解的倍增计划,就是在确定的优先发展的学科上首先实现倍增。
这是做规划,但是如果做综合改革方案也只涉及宏观,那么,教育教学改革就永远只是空话。比如说,很多高校在提完全学分制或彻底学分制。用时任大连理工大学李志义副校长的说法,完全学分制的本质是学生自主学习,包括自主选专业、自主选课程、自主选老师、自主选进度,前提是供大于求,即在专业、课程、老师和学习阶段等数量上都比较充裕的情况下,实施完全学分制才有意义。
中国大学的现状是“宏观改革轰轰烈烈、微观改革冷冷清清”。即便是教学改革做得比较深入的南京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陈骏校长坦言,在南大,教学改革,没有十年二十干不下来,更不要指望三四年就能立竿见影。李志义副校长也告诉我,目前改了300多门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只占总数的10%~15%。
因此,教学改革是教育综合改革的深水区,既要触动灵魂又要触动利益,教学改革依然是一场攻坚战。 为什么教学改革如此艰难?我认为,可能有以下三个原因。
1. 源自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管理思维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对于大学的管理方式很多时候是工程化、项目化、碎片化、数量化的。像学科建设、科学研究都有量化的硬指标、硬任务,而人才培养的指标偏软。
2. 是由于大学管理者的自我定位
我们总是说大学与政府不一样,但在实际操作中,我们其实也在做政绩工程,追求数据上的表现。对于教学、人才培养这些需要很长时间才有显示度的工作没有倾注足够多的精力。 作为大学的管理者,究竟要不要关注指标?我认为,对于指标要两看。
一些指标确实反映了学校的发展思路,例如,张杰校长告诉我,上海交大把科研经费尤其是自然科学基金当作一种非常重要的价值导向在追求。他认为,之所以强调自然科学基金,是因为它体现的其实是大学的创新活力,而这是上海交大培养创新性人才所必须的。
但是,有些指标也有盲目性。比如说,国际化这个指标,一些人认为通过留学生数量来体现,拼命招收外国留学生。但是西工大汪劲松校长说,所谓国际化,很简单,就是三个字,“跟谁玩”。
一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国际上和那些学校在交流,就体现了这个学校的国际化水平。后来,我加了三个字,“玩什么”,同样是交流,向别人学习和与别人合作是两种不同的程度。又如,研究型这个指标,一些人认为就是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比例,拼命增加研究生数量。
时任武汉大学测绘学院院长李建成就认为,研究型是要以科研带动人才培养,要把科研成果及时地渗透到教学当中。我认为,对于研究型大学而言,即使是本科生,也要注重通过科研来培养学生。
在任校长时,我不主张给学校、学院定指标,我更愿意把指标看做结果而不是目标。例如,根据ESI指标,我们学校目前已有16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我记得当时教育部副部长陈希同志在会上提出要特别关注ESI指标。
此前我自己对这个指标并未特别关注,听陈部长讲话时,冷汗都下来了,下决心要好好研究一下,还对同行的其他校领导讲,我们学校要争取在“985”三期结束的时候能有两个学科进入前1%。
结果回来一查,中大已经有9个学科进入前1%。我特别欣慰,我们没有刻意追求这个指标,但是客观上指标表现也不错,这让我觉得有种“蓦然回首”的感觉。 同时,我并不认为讲指标就有错。去年,在华中科大做本科教学质量审核评估时,罗校长是分管教学工作的常务副校长,他与我就大学的治理模式进行了讨论。
我认为,大学的治理模式也有多样性。可能在北大、复旦、南大等传统的综合型大学的治理模式会比较注重氛围的营造;而在清华、浙大、华中科大等传统的理工科大学可能会比较讲究指标。
我认为,不同的治理模式,没有对错,只要看是否适合学校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发展需要。用李延保老书记的话说,大的方向确定下来,不过是一个选择。对于我而言,现在更不愿意轻易说别人对或者错,有人说我是成熟了,其实我知道,是老了。
我现在也特别理解罗校长所面临的紧迫感。他是恨不得一天当做两天过,五年掰成十年用,相信大家都已有感受。我也曾跟罗校长开玩笑,在他头上有两件大事,一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常态化建设行列,二是拿到“2011协同创新中心”。
两件事其实就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常态化建设行列这一件大事。 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在教育部公布的2015年工作要点里,也提出“坚持中国特色、一流标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组织实施”。实际上,罗校长所说的进入第一方阵,就是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常态化建设行列。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常态化的意思是以后对于这些大学的拨款不再按照项目来拨,不再单纯以指标来考核大学。但是决定谁可以进入第一方阵,又必须要看指标。所以,大家应该能够明白,我们现在追求指标,目的是为了不要被那些工程化、项目化、碎片化、数量化的指标所左右。
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如果进入不了世界一流大学,就要去争取世界一流学科,但是中山大学学科的特点是学科间的水平比较平均,很难说哪个学科占有绝对优势,某种意义上来说,争取世界一流学科,可能更为困难。
再来说“2011”计划。我认为,“2011”计划是进入第一方阵最最起码的标准。许宁生校长曾对我说,这是悬在他头上达摩克利斯之剑。对于我而言,我曾分别担任了第一批“2011”计划科学前沿组的会评和现场考察组长以及第二批行业产业组的会评和现场考察组长,因为做组长的一个前提是本校没有本组的参评项目。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到第三批的时候,不要再担任组长了!
实际上,从前两次如此艰难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我们的学科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是不够。因此,我认为,下一步,需要进行总结、调整。前几天,我应邀参加了我校三个协调创新中心的讨论,我想,我的梦想今年应该可以实现了。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也跟罗校长开玩笑地说,我退了,许宁生跑了,两座大山现在全部压在他的身上。他的压力山大可想而知。因此,我很能理解罗校长在春季工作会时通过指标来充分表达与第一方阵差距的这种方式,其实他是要让大家明白我们的努力方向。
至于如何进入第一方阵,我认为,并不是要把谁拉下来,而应该反过来想,第一方阵的阵容是可以扩大的。在这个方面,上个世纪80到90年代的浙大和南大给我们做了榜样,当时这两个学校没有列入国家重点建设的行列,但是浙大的路甬祥校长和南大的曲钦岳校长毫不气馁,带领两个学校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他们现在不是稳定地站在第一方阵吗?同样的道理,现在讲第一方阵,也不是说固定只有几所高校,我们和前几所高校的差距逐渐缩小,那我们就可以进入第一方阵!
2006年,在第六届教代会上,我们提出建设“居于国内一流大学前列、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的目标。2012年,学校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建设“文理医工各具特色融合发展,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
进入第一方阵,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我们全校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对此,罗校长提出,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要实施分步走的战略路径,进入第一方阵并无明确的时间表,我很赞同,但时间真的是非常紧迫了,我们应该一起努力,缩短与第一方阵的距离。
罗校长作为一位新人来到中大,在他的就任演说中,我注意到了他对中大历史的尊重。我认为,校长到新的学校,最重要的是继承和发扬。
在与罗校长聊天时,他几次提起陈寅恪先生。大家不要觉得理工科的老师对陈寅恪先生不熟悉,我可以举出好几个理工科教授崇拜陈寅恪先生的例子。有次聊天,罗校长提到原打算在就任演说中向陈寅恪先生表达敬意,后来被告知在那个场合讲可能不是很合适,最好在其他场合说。
陈春声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告诉我,他曾在2009年陈寅恪先生逝世40周年之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读书人要脱俗》,里面提到陈寅恪先生,“将学术精神的要旨,归结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将这一点与‘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读书人要脱俗。”我认为,这就说得很清楚,对于陈寅恪先生的这两句话,大家可能更加看重抵御外来干扰,尤其是做学问不要受政治的干扰,但更重要的其实是学者对自身的要求。
罗校长刚来不久时曾跟我聊天,他以后从校长岗位上退下来后,是留在广州还是回到武汉。我告诉他,虽然我的身份证还是杭州的,但是我主要住在广州。
我还说,作为校长,首先是中大人,然后才是中大的校长。中大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罗校长表示赞同。其实,我还有一个私心,因为我知道他正在领衔一个国家重大项目和大科学装置,我希望能够落户在中大,壮大我们的科研力量。
作为中大人和作为外人来讲话是很不一样的。有些话让外人来讲,我们觉得是批评,比较难以接受;但是作为中大人来讲,大家关起门来,怎么讲都没关系。即便如此,在春季工作会后,罗校长给我打电话说,他在会上作为中大人的感觉太好了,后来想想可能有些话说得过头了。
我想,这件事可能我都有责任,因为我再三跟他说,你应该以中大人的身份来讲话。同时,我也希望在座诸位也把校长当作中大人,这样,他说的很多话就是顺耳的。
3. 教学改革其实是教师的自我革命
教师都是学科本位的,一些教师,尤其大牌教授会认为自己的课是本专业的核心课,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课不重要。 对此,时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院长认为,现在专业课程设置上两个突出的问题是核心课程过多以及核心课程讲不深。而后者更难。对此,饶毅说,对于现代生物学,核心课程只有四门,学完这四门核心课程,现代生物学的框架就能基本掌握,包括他自己的课都不是必修。对于这样的老师,我是很敬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