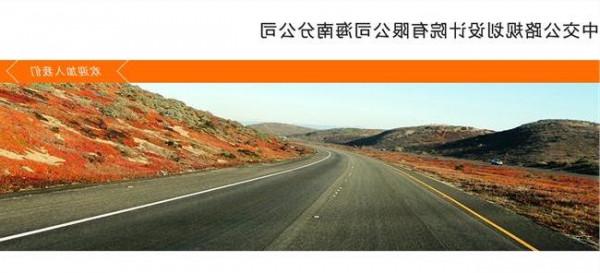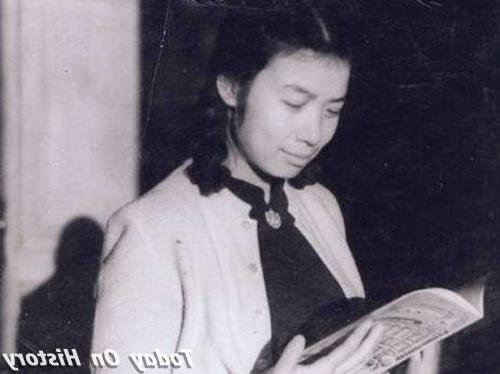孙维世毛泽东 47年毛泽东为何怒斥新华社:你们是中央社吗怎么造谣
核心提示:有一天我正在廖承志的窑洞,毛主席给他打来电话,我都听得到话筒中传出来的湖南腔:“你们是中央社吗?你们是《中央日报》吗?你们怎么造谣了?新华社不造谣,中央社才造谣。”
毛泽东 资料图
本文摘自:《百年潮》2015年1期,作者:李敦白,原题为:《回忆与周总理有关的几件往事》
我在宣化店第一次见到周总理,那时都叫他周副主席。我对他的外表的印象,最突出的就是帅,英气逼人,目光敏锐,看上去精力充沛,一望即知不是常人。他个子不算很高,中等个吧,眉毛特别重,络腮胡子,刮不胜刮,脸上常常露出青灰色的胡茬。
周副主席和代表国民党的王天鸣将军以及代表美方的白鲁德将军带着大批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宣化店视察调查,当天晚上开欢迎会,我就在那个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他。我和我的翻译骆叔平坐在最后一排——实际上我的中文水平并不需要翻译。
三方都发了言,李先念揭露国民党部队对宣化店的包围攻击,王天鸣说,新四军是我们的兄弟部队,我们不可能跟你们闹摩擦,更不可能围攻你们,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讲得很诚恳。周恩来马上接口,表示非常欢迎王将军的态度,而且说,王将军的话以后能不能兑现,请在座的每一位作见证。他非常敏锐,立即抓住了机会。
散会以后,走回招待所的路上,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碰到李先念提着灯笼送周恩来回宿舍。李先念介绍我们认识。周恩来跟我握了握手,没有一句客套,直接就说:“我们讲话的时候我就一直注意你,我讲话之后你拼命鼓掌,国民党代表和美国代表讲话后你坐在那儿不动,这样不行,他们会注意你,你回上海以后会有麻烦。
”所以,我跟周总理第一次见面,就挨了一顿批评,但是受他的批评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他丝毫没有居高临下、教训人的姿态,完全是从保护你、关心你的角度出发,让人心悦诚服。
周恩来与人沟通的能力真是无与伦比。我心想,奇怪,第一,我坐在最后,会场又很暗,他怎么会看到我,而且注意到我的动作?第二,他身处这么重要的场合,应该高度紧张,怎么会留心别的事情?我记得跟他提了一句我想去延安,他说,等我回到南京再说吧。
延安时期,我跟周恩来有一次特别重要的接触。大概是1947年初,有一天小廖(廖承志)来找我,说周副主席叫你马上去,你骑我的马吧。小廖有个小红马,特别棒,可它欺侮我,拼命跑,怎么也勒不住,我只好强逼它跑向一个很陡的山坡,它不得不停下来。
我下了马,再不敢骑,牵着它走。结果,到杨家岭周副主席窑洞时,斯特朗已经开始跟他交谈。我的角色是翻译,既然他们已经开始谈,周就让我坐在旁边做他的“活词典”,他表达不出来的时候给他供词。
他的英文不算很好,欠流畅,但这个人特别聪明,选词很准,能够运用并不丰富的词汇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只有几次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向我要词,或者求证。那个时候,我对周已经有所了解,所以对此倒也没有觉得很特别。
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同时,他还在处理另外两件事情。他的窑洞是一个大房间,左边是小超大姐坐着给国际妇联写信,他们的养女孙维世则走来走去思考着一个什么演出,一会儿邓问他写信的措辞,一会儿孙走来问他某个场景如何处理,周有条不紊,一丝不乱,好像他的脑子可以同时处理许多件事情。我很感慨这真是一个组织天才。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新华社有一个记者叫胡懋德。他发了一篇文章,说美军一年之内在上海犯了三千八百项兽行。起因是此前有一篇报道,说某月驻上海美军犯了多少项暴行,他把这个数字乘上十二,又将“暴行”上升为“兽行”。
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是一家自由主义色彩浓厚的英文周报,对中共态度友好,连它都公开叫板,说请新华社把三千八百项兽行的清单列出来,我们全文发表。有一天我正在廖承志的窑洞,毛主席给他打来电话,我都听得到话筒中传出来的湖南腔:“你们是中央社吗?你们是《中央日报》吗?你们怎么造谣了?新华社不造谣,中央社才造谣。
”第二天,周恩来就到了清凉山,集合全体党员讲话,讲了一整天,但没让我参加。
新华社党员的比例很高,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左右,只有少数人不是党员。会后给我传达了周恩来讲话的内容。周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他反复强调,新华社要讲真话,千万不能造谣,不能主观臆想,不能为了打动读者而捏造新闻。
周还跟他们讲,他在南京、上海的时候,做民主党派的工作非常辛苦,跟他们讲形势讲前途,好不容易讲通了,过几天又忘了,得重新来过。之所以能讲通,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报道的准确可信。
所以,捏造或任意扭曲新闻,所起的是坏作用而不是好作用,影响很坏。新华社曾长期保持讲真话的传统。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大概是1960年或者1961年,“大跃进”刚过去的时候,有一个记者写了一篇专稿,写得很零散,主题不鲜明,我就在前面加了一个导语,大意是说:在新中国,与过去的灾荒年头不同,生活虽然艰苦,但不会饿死人了。
审稿的副局长把这段导语划掉了,我问为什么,他说:“你说的不够真实,下面许多地方饥荒很严重。”我当时确实不知道饿死大量人口的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