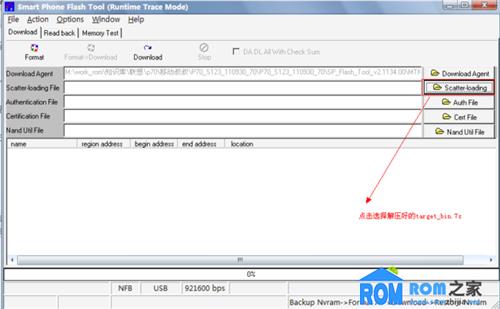台湾陈卫平 陈卫平:台湾对大陆近二十多年儒学研究的评述
台湾学界在1980年代提出“文化中国”,意谓大陆和台湾在文化传统上存在着一致性。因此,台湾学界对于大陆近二十多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比较关注。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台湾以继承和发扬儒学为己任,而大陆发展到文革期间把儒学作为彻底打倒的对象,因此台湾对于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关注自然就集中在儒学方面。
1949年以后,港台形成并活跃着现代新儒家,而现代新儒家注重阐发孔孟和宋明理学,现代新儒家在1980年代以后又成为大陆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于是,台湾学术界[1]最瞩目于大陆儒学研究中有关孔孟、理学、新儒学的研究。同时,在一般层面的儒学研究上,由于港台新儒家注重阐发儒学的宗教意蕴和现代意义,因而对大陆有关儒教说、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传统的争论也有所评述。
大陆近二十多年对于儒学研究,是从对孔子的重新评价开始的。熊自健所著的《中共学界孔子研究新貌》甚为全面地评述了大陆1978年至1988年的孔子研究,包括研究孔子的方法论以及孔子的道德哲学、宗教思想、美学、认识论、政治思想、教育学等方面。这里择其与哲学相关部分的评述。
熊自健注意到大陆对孔子的重新评价,首先是与研究方法的出新相联系的。他以李泽厚、匡亚明、张岱年的方法为代表,指出李泽厚从文化心理结构来研析“仁”,指出仁学结构的四因素及其相互关联;匡亚明强调不能机械套用“存在决定意识”来分析孔子的人本哲学思想体系,提出对孔子思想遗产实行三分法,即分为封建性意识、有生命力的智慧、精华与糟粕相混杂三方面;张岱年注重对哲学范畴、命题的理论分析,由此来认识孔子的哲学体系及其特点、传承;认为这些方法“超出了简单阶级分析的模式,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探索孔子思想内在的统一性具有方法论的自觉,要求避免各执一端片面地理解孔子”;然而,牟宗三指出的宋明儒从道德实践的工夫来体认孔子,要比上述的方法“更具有活泼动人的生命”。
关于孔子道德哲学的研究,熊自健绍述了朱伯昆、魏英敏、冯友兰、匡亚明、罗佐才、李启谦、杨景凡、严北溟、杨伯峻、李泽厚、萧箑父、任继愈、徐长安等人的有关论著,在孔子论道德的意义与道德行为的来源、孔子道德哲学的核心、孔子道德哲学的体系这些问题上的各种观点,认为“中国大陆学界近年来对孔子道德哲学的解析有浓厚的学术气息,脱离肤浅的政治谩骂”,“最令人侧目的是,大多数的学者主张对孔子的道德哲学吸收其精华,进行创造转化,为社会主义的道德生活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哲学服务”;但是,“牟宗三先生所阐明孔子成德之教的精义,是大陆学界解析孔子道德哲学时尚未达到的境界”。
关于孔子认识论的研究,熊自健分析了张岱年、任继愈、钟肇鹏、茅亭、杨凤麟、冯契、刘邦富、王举忠以及北大哲学系与萧箑父等主编的两本《中国哲学史》等论著,认为这些论著涉及到了孔子关于知识的来源与性质、认知的方法与过程、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等问题,重新探索孔子的认识论,在“努力地辨析孔子认识论在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与作用上,颇见功力”,但往往纠缠于唯心、唯物的问题上,对于最能表现孔子认识论特点的知识与道德实践的关系问题,较少有人提出讨论,而牟宗三在《现象与物自身》“所开出儒学认识论的新方向,正好反照出中国大陆学界探索孔子认识论的各种限制”。
对孔子美学的研究,熊自健以刘纲纪、张怀谨、叶朗、钟肇鹏四人的研究成果为代表,认为刘纲纪以结构分析的方式来探讨孔子的美学,孔子从仁学出发,以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去观察美和艺术的现象,强调审美和艺术是陶冶人的思想情感的重要手段,分析了艺术的社会作用,又提出了美的本质是与道德上的善相统一,把“中庸”作为美学批评的尺度;张怀谨从孔子的诗乐理论来探讨孔子的美学,由此把孔子的美学思想概括为由诗乐而达到理,又由礼而归乎仁,指出孔子审诗正乐的美学理想与天下归仁的理想是结合在一起的;叶朗以孔子的审美观念为中心,从其提出的美学范畴和命题来论述孔子的美学思想,强调探讨审美和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孔子美学的出发点和中心,并说明了孔子“兴观群怨”、“大”“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所具有的审美意义;钟肇鹏把孔子有关美和文艺的言论汇集在一起,分类论述,以文质彬彬为孔子美学思想的纲领,由此诠释孔子的美善统一、诗教与乐教、语言修辞等思想。
他认为从上述四人的研究成果可看到:“研究方法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限制最少”,“不落在‘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架构中来解析孔子的美学,而从孔子美学本身的性质与内涵进行研析”;比较一致地注意到了孔子美学与其仁学的关联,“因此他们探讨孔子美学是具有整体性的脉络”;辨析了孔子美学的价值层次,不是“把孔子有关美和文艺的论点放在同一平面上来处理”,而是注意到它们在孔子美学思想中有不同的层次;一致认为美善统一的理想是孔子美学的最大特征,并指出伴随这一特征而来的一些局限性;有待努力的是加深对孔子仁学的体察,由此才能进一步诠释出孔子美学的精彩之处,在这方面马一浮的《论语大义》和台湾大学教授张亨的《论语论诗》是值得作为参考的。
[2]
大陆的美学研究,包括对中国传统美学的研究,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是重要的理论依据。陈怀恩在肯定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堪称为近代处理中国美学的皇皇巨制”的同时,对其用《巴黎手稿》来诠释孔子的仁学和审美态度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他认为该书把仁学诠释为以社会性的感情为本,而马克思讲的社会感情是一种历史的抽象,孔子的道德情感则是实存的,两者“在出发点上就有差异”;马克思和孔子虽都认为审美活动是自由境界,但就孔子来说,“一般人的艺术享受和艺术创作都可以暂时地达到自由、审美的境界”,就马克思来说,纯美的自由境界要等待人类的“人性的感官”、“社会感官”完全创造出来才能达成,而这又与完全废除私有制相联系,因此,“就实践过程来看,两者却是泾渭分明的”;该书以“艺术作用即社会性感情的交换功能”来诠释孔子的兴、观、群、怨是否有公式化的问题;他还指出该书既认为孔子以善为美的内容,又说孔子承认形式美有独立意义,这是互相矛盾的。
[3]
在大陆有关研究孟子的论著中,李明辉对杨泽波的《孟子性善论研究》给予了比较高的评价。在他看来此书“是中国大陆第一部突破马列教条、从自己的观点来讨论孟子性善论的专著”;并说1994年他在为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办“孟子学国际研讨会”的时候,“曾广泛浏览中国大陆有关孟子学的著作,发现千篇一律都将孟子的性善论说成唯心论,完全无法进入其思想脉络之中。
因此,尽管杨泽波此书仍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但已令人耳目一新”。[4]但对其耳目一新之处和值得商榷之处都未有进一步的论述。
杨祖汉则在充分肯定杨泽波的著作是“近年来孟子学的相当有水准及富个人见解的著作”的同时,对此书中有关牟宗三的孟子研究的一些评议提出了商榷意见。首先,关于孟子与康德。牟宗三认为康德和孟子都是道德自律形态的,杨泽波则认为不然,因为康德重理性轻情感,并把道德情感纳入他律之中,而孟子尊重包含丰富情感性的良心本心,很难戴上道德自律的桂冠。
杨祖汉维护牟宗三得观点,论证孟子的学说“是自律的伦理学,不特如此,康德的意志底自律说,必须承认孟子的理论,才能证成”。
其次,对道德形上学的理解。牟宗三沿着孔孟“践仁以知天”、“尽心知性知天”之义,阐发“道德形上学”,杨泽波认为,这样的道德形上学是为了使本心善性有稳固的基础,从而走向把心体性体不仅作为道德根源而且作为宇宙真实根源的泛道德主义。
在杨祖汉看来,这是对牟宗三的误解,因为牟宗三从孔孟出发,区分了道德的形上学与形上学的道德学,后者是为心性找形上学根据,而这正是牟宗三所反对的。
再次,圆善问题。所谓圆善,即德福一致,牟宗三认为儒、道、释对于圆善如何能实现的问题,较之康德有更圆满的解答,杨泽波认为儒家幸福观也许比康德圆满,但其并没有解决康德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在实际上保证有德之人一定能享受到现实的幸福。
杨祖汉指出,这是把幸福理解为满足感性欲望而导致的,现实的幸福是人的存在情况使他感到称心如意,是一种状态的理念,因而儒家的圣人一切随心而转的境界就是现实的幸福。第四,牟宗三以孟子为标准,分宋明儒学为三系,以朱熹为“别子”, 杨泽波批评这一标准有偏颇,因为孟子和荀子各继承了孔子的内求或外求之一翼,所以不可以孟子为孔子嫡系真传。
杨祖汉申论牟宗三对孔、孟、荀的分别,以为孔子虽然讲外学,但重点在反己自省的德性之学,故孟子所偏者小而荀子所失者大,承继孔子方向的自然是孟子,以此来看朱熹用讲知识的方法来讲道德,与孔孟不相应,认其为“别子”也是合理的。
总之,杨祖汉认为在杨泽波的孟子研究中,对牟宗三的孟子研究的理解不太恰当,并认为这往往是大陆学者的通病。[5]
对于大陆宋明理学的研究,傅伟勋和曾春海都注意到了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傅伟勋的评论较为具体,提出该著作有两个特色:强调了长期不被重视的元代理学;注意到理学发展与当时社会发展的关系。但对该著作的序言提出科学的理学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混淆了科学形态、哲学形态、意识形态这三种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6]作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当代儒学主题研究计划”成果之一的论文集《儒家思想在现代东亚:中国大陆与台湾篇》,收有香港学者郑宗义《大陆学者的宋明理学研究》一文,对大陆的宋明理学研究有甚为详细的分析。
他认为大陆的宋明理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49年至八十年代初,研究几乎完全套用唯心唯物的二分法、阶级出身等教条主义,对理学大抵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第二阶段自八十年代处至八十年代末,此时已不满教条的生搬硬套,而提倡通过重要范畴的分疏来掌握理学,对理学有正、负两方面的评价,但仍未脱教条阴影;第三阶段自八十年代末至2000年,研究开始完全摆脱教条的色彩,强调文献的解读与爬梳,且多有参考借取海外学界的观点说法,以为进一步思考析论之所资,但对理学的了解还不免重心性而轻天道,而有一偏之虞。
他对第一阶段的评估,这里只叙述与本文有关的部分。他认为侯外庐等主编的《宋明理学史》在研究方法以至内容结论上均有大不同于贯穿唯心唯物二分法的《中国思想通史》,反映了大陆学者的理学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已转入另一阶段,书中很多篇章实际上是通过分析厘清宋明儒的各个范畴、命题及问题来立论的,特别是对材料所下的考证工夫,例如仔细指出宋明儒那些观念受到佛、老的影响,则深具参考价值。
对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宋明理学研究,他的看法是“冯先生虽自诩从比较哲学的观点揭示宋明理学的中心课题乃关乎什么是人与怎样做人的‘人学’”,但视野常常转到共相与殊相的问题上,与《中国哲学史》的旧说大同小异,“未能会心于宋明儒天道性命相贯通的睿识”。
他对第二阶段的评估,以张立文的著作为代表,认为张立文肯定理学是体现当时时代精神的思潮,但由于强调回到它那个时代中去考察它,因而很难重释出理学的现代意义;张立文以范畴分析方法透视宋明理学,“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绝对值得肯定”,但其对理学范畴的分析,依然是唯心、唯物那一套,而且以世界本原问题作为研究理学的视野,无法了解理学贯通天道性命的特质;在这一阶段,张岱年的《宋明理学评价问题》和《宋明理学的心性概念的分析》,“竟一反其唯物论立场,运用道德自觉性与西方哲学理性主义的观念来阐释宋明儒的心性之学,虽只简略点及而未见仔细的铺陈,惟已隐约透露出大陆学者的理学研究在九十年代又将迈进另一新阶段的消息。
而这消息后来则具体表现在张先生的弟子陈来先生的著作中”。他对第三阶段的评估,以陈来的《宋明理学》为代表,认为陈来“更能尽量让文献本身说话,并且在义理上几完全弃用唯心、唯物等教条用语”,其借用西方哲学中的实践理性与普遍性道德法则等概念来辨解理学之理的实义,反对将理简单化地看成社会规范或礼教,“可知他对理学中的心性部分确有相当的契会”;不过,其对理学的理解有重心性轻天道的片面。
最后,他的结论是“大陆学者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研究,迄今似仍未能完全契接宋明儒天道性命贯通的微意”,因而需要与牟宗三的理学研究有进一步的对话交流、视域交融。[7]
传统儒学自汉以后成了经学,因而对儒学的研究不能不涉及经学。同时由于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有研究经学的计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