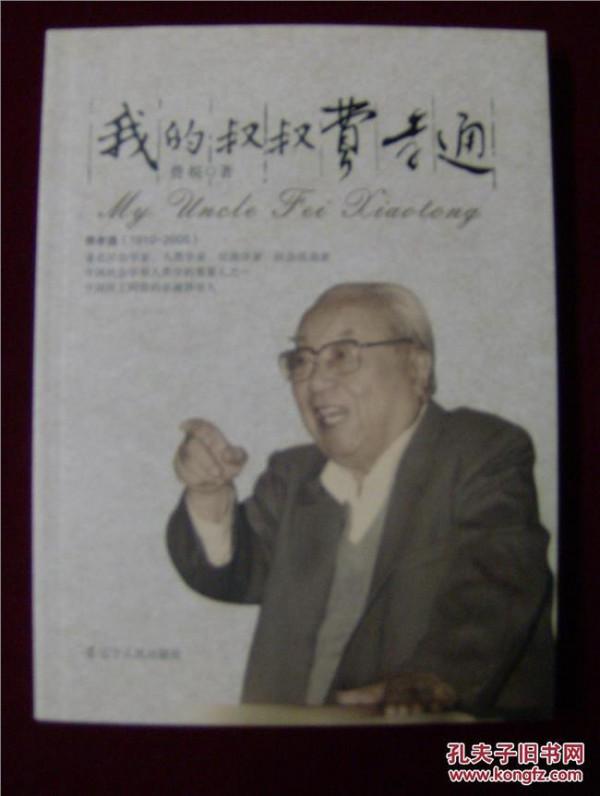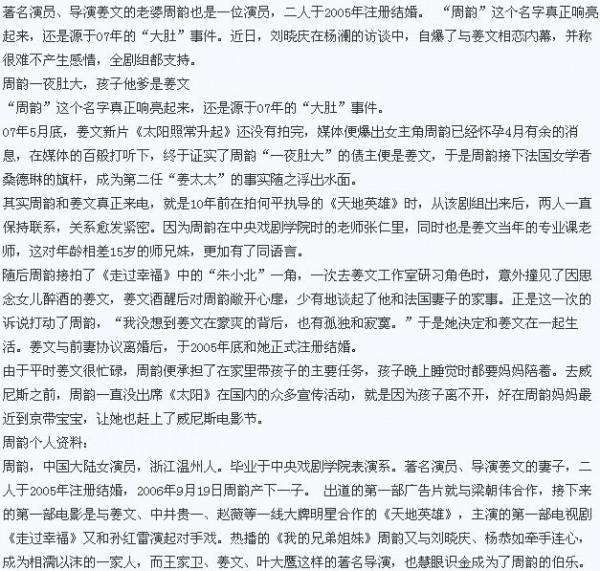费孝通妻子 费孝通的妻子 《我的叔叔费孝通》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拨乱反正,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领导中国人民全力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春回大地,万象更新,这一刻,人们真像又回到开国初年那种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日子,但是时光一去不回头,当叔叔抓住机缘的时候,已经是年近耄耋的老人了。
1977年2月,叔叔出席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参加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可以说是他重新获得工作机会,开始忙碌起来的标志。他拿起搁下了20年的笔,开始写作,“赞孝通”这个久违的名字又出现在报刊上了;接着他又拾起断了20年的实地调查的线头,迈开脚步“行行重行行”,奔走在全国各地的乡间田野,村镇街头,一篇篇实事求是的调查报告,又呈现在人们面前。
除工作外,叔叔家里也恢复正常,不再冷清。
在吉林省公主岭工作了十多年的女儿费宗惠、女婿张荣华一家四口,获准调回北京,全家人团聚了。这时叔叔家已经从西四排搬进了“和平楼”,住房虽然比原来大了一些,但是老老小小六口人挤在一起还是显得局促,为了给“第三代”腾出空间,叔叔写东西的时候就被挤到卧室床边的小桌上。
有一位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来找他,见他伏在床边的小桌上写稿,床上堆满了杂乱的书籍纸张,想起了几十年前他们在中学时宿舍的情景,禁不住笑着说:“你怎么还在闹住宅问题?”是啊,自从女儿一家回来以后。
人多了,空间就少了,两个外孙上学要做作业,只能把地方让给他们。 1983年,叔叔当选全同政协副主席,他家从“和平楼”搬到“高知楼”(顾名思义,这是提供给高级知识分子住的宿舍楼),住房条件得到改善,总算有了一间属于他自己的书房。
我在整理《费孝通文集》书稿时粗略地算过,如果从1977年2月,叔叔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时写的《民族研究向前看》算起,到1982年底写《我看人看我》止,收录进《文集》的文章有六七十万言,也就是说,这些文字都是他迁入高知楼前,在繁忙的公务活动之余,“伏在床边的小桌上”写出来的!
当上政协副主席应该算是“国家领导人”了,按规定可以分配到条件更好的住房,有关单位几次要给叔叔调整住房,但是他都以“老马恋槽”为由,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他说,在民族学院住惯了,环境熟悉,邻里和睦,闲时在院子里散步,大家见面打个招呼,聊上几句,十分惬意。
再说老伴身体不好,校医院的医生护士都认得,打针、吃药很方便,人熟是个宝嘛。1988年,他担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由于职务上的变化,“高知楼”的住房显然已经影响到他的一些公务活动了,有关单位再次请他搬家,但是老人家仍然依恋着周围的一切,不肯离开。
又拖了五年,直到1993年,在管理部门多次动员下,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已经居住了40年的民族学院宿舍,搬到新街口四号院的新居。 宗惠和荣华回来后,帮着婶妈把家里安排得妥妥帖帖,恢复了正常的“秩序”,不用我再去“安装炉子”和“打扫卫生”,所以“文革”后我反倒去得少了。
不过我知道叔叔很忙,他要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也知道他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是特别法庭的审判员;他的名字不时在报纸上出现,还看到了他批判江青的文章。
打倒“四人帮”,中国有了希望,叔叔迫不及待地想要干点什么事情。1977年,他致信当时负责筹建社会科学院的胡乔木、于光远,说自己这匹“三四十年代初生之犊,看来已甘为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矣;牛也罢,马也罢,驰驱未息。
殊可告慰”。希望自己还能像“巴滇山道上背盐的驮马”那样,供人民驱策。 1978年冬,担任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的叔叔,赴日本出席联合国京都东亚学者学术讨论会。
这是他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也是第一次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公开露面。在学术界销声匿迹了20年的费孝通突然出现在公众面前,让不少同行吃惊。
这以后,他又访问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印度等国。他利用每次出国的机会,尽量多了解这二三十年来国外社会学人类学发展的情况,设法与老朋友接头,并结识新朋友。1979年四五月间,他随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从他写的《赴美访学观感点滴》里,可以了解到他出国访问的一些情况: 赴美访学一月,历经十城。
飞机旅行似蜻蜓点水,短期中接触面颇广……思想交流少于礼仪交欢。即在专业座谈会上,话题方启,思路方通,散场之刻已到,如谓访学则难人堂奥,因此,这次访问实际上只起了个重建联系的作用。
我个人的条件更使上述情况较为突出。一是社会学和人类学在美国是两门学科,一般是各自设系,井水河水各有其道。
我却是个两栖类,两门学者都以同道相视,不宜轩轾,因而需兼顾双方,任务加倍,未免顾此失彼。二是少壮好写作,狂言拙作流传海外已有40多年,同行后起者大多读过这些书,加上20年来有关我个人的谣传颇多,此次出访,多少有一点新闻人物的味道,要求一见之人为数较众,难免应接不暇。
三是我30多年来和国外学术界实已隔绝,最近几年虽然接触一些外文书刊,也没有时间精心阅读,接到访美任务后,佛脚都抱不及,仓促启行,心中无数。
新名词、新概念时时令人抓瞎。四是旧时相识多人鬼录;幸存者众多退休。现在这两门学科的主力几乎全是我同辈的学生,后辈之歌,曲调舛异,领会费神。五是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在讲文化、讲社会的学科里要找一套能互相达意的语词原已匪易,而我又得借用本来没有学好,又是荒疏已久的英语作为交流工具,当然难上加难。
在与外国学者进行沟通的同时,他还和香港、台湾的同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叔叔的出访结束了我国社会学人类学界与国外学界隔绝了差不多30年的历史,为后来请境外学者“进来”讲学和国内学生“走出去”求学创造了条件。
1979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胡乔术,要叔叔出面恢复中国社会学的工作。
在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早在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的时候,被当成资产阶级学科从全国高校中砍掉了。当时叔叔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请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在中国“断子绝孙,多少留个种”。如今要想复活一门已经死去近30年的学科,谈何容易。
一门学科可以挥之即去,毁于一旦,要重建时却不能呼之即来。重建就得造砖造瓦从头做起。 任何事情都要人来做,重建社会学也一样,首先要有“人”。然而30年前干这行的人,死的死,老的老,要不已经改行。
更严重的是,当时知识分子心中疑虑重重。要知道,自新中国成赢以来,知识分子一直是被“改造”的对象,他们的心始终没有踏实过。“文革”时,更沦落为“臭老九”,被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一时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甚嚣尘上。 1978年,胡乔木曾给30多位过去社会学界的老先生发出邀请,请他们参加一个商量恢复社会学学科的座谈会,开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