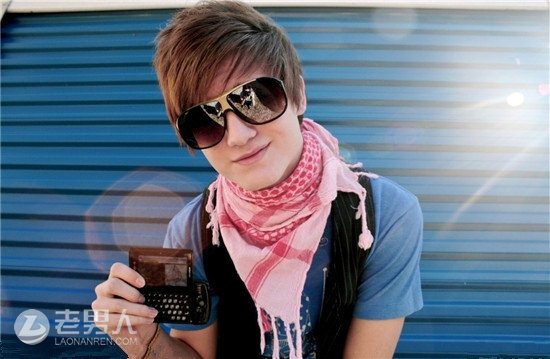这个看脸的时代,艺术家如何应对?
英格玛·伯格曼《假面》,电影剧照,1966年
用艺术打破“媒体脸”的暴政
人脸,一直以来都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在摄影出现之前,人们主要通过面具和肖像绘画的形式将脸复制下来,前者最初和宗教祭祀有关;后来它的这层意义逐渐被取缔,主要和纪念死者、再现人物以及确认其身份、地位有关。
拿破仑的死亡面具
在人类一直以来的意识里,在很大程度上,脸其实就代表了人。人们一方面有再现自己面容的愿望,另一方面还是免不了希望画里的那张脸更美、更庄严、更符合自己的期待。
阿尔布雷特·丢勒《自画像》,1500年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摄影术的发展逐渐取代写实主义的肖像绘画。可以说,这种便捷捕捉人脸的技术既满足了人们对一张客观、真实的脸的追求,又让更多普通人的脸被记录下来。
经典好莱坞时期的著名影星海蒂·拉玛和费雯·丽
其实,脸的图像从来都没有真正客观和民主过。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印刷技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电影明星的脸被大量印制在杂志封面和海报上。他(她)们的脸除了展示功能之外,更加引导了观众对其的崇拜,这个传统到今天仍然甚嚣尘上。
美国当代艺术家辛迪·舍曼的摄影作品
不知不觉中,观众也被操纵着去学习拥有这样一张脸。于是,有些艺术家尝试去揭露这种媒体对脸的暴政,以期待打破观众已经养成的观看习惯。
苏联导演爱森斯坦《总路线》电影剧照
当好莱坞电影尽情展示俊男靓女的时候,其它很多致力于电影艺术的艺术家则尝试在电影中展示尽可能多元的面孔。苏联导演谢尔盖·爱森斯坦(Сe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н Эйзeнштeйн)将众多普通民众的脸部特写,通过蒙太奇剪接在一起。
布努埃尔《一条安达鲁狗》电影剧照
西班牙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Luis Buñuel)在他的作品《一条安达鲁狗》中,特写暴力的脸部镜头令人印象深刻。在这些导演那里,脸的容貌、表情不再单一,也取消了观众对习以为常的明星脸的凝视。
阿努尔夫·莱纳复绘作品
现在,人脸早已变成一种可以被轻易操控的图像,在技术加持下,人们可以任意美颜、修图。同样,在当代艺术中,脸在艺术家那里,也常依赖于图像技术媒介的过滤。只不过这和审美没有关系,而是为了反映脸在媒体社会所遭遇的危机。
阿努尔夫·莱纳对路德维希·乌兰特死亡面具的复绘,1978年
奥地利画家阿努尔夫·莱纳(Arnulf Rainer)用激烈、粗暴的笔触在画面上进行涂抹。不管是自己的照片还是死者的照片,经过他的再加工之后早已面目全非,他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论证脸的面具特征,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查克·克洛斯作品
查克·克洛斯作品(局部)
美国艺术家查克·克洛斯(Chuck Close)和莱纳不同,他将人脸照片转化成巨幅的绘画,但是这个人脸却是由细部抽象的图形编码而成的。人脸在克洛斯这里变成了数字面具,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反抗媒体社会的技术虚构。
安迪·沃霍尔《玛丽莲·梦露》,1962年
说到对“媒体脸”的应用和解构,最著名的艺术家非安迪·沃霍尔莫属,他用最廉价的丝网印刷方式将明星和领袖的头像转化成艺术品。脱离了任何语境的名人头像正如现代印刷一样,既廉价又虚无。
白南准《再见,玛丽莲·梦露》,1962年
在1962年和1999年,韩国艺术家白南准分别以玛丽莲·梦露为题材创作了两件作品:《再见,玛丽莲·梦露》和《追忆20世纪》。观众很容易在这两件作品中,辨认出他们集体记忆里那一张极其熟悉的“媒体脸”,但是在玛丽莲·梦露的笑容背后,真实存在的却是她的死亡事实。
白南准《自肖像/头与手》,1982年
在1961年和1982年,白南准创作了两版装置艺术作品《自肖像/头与手》。第一次,白南准通过双手在雕塑的脸部交替开合;第二次,自己的雕塑头像、电视里的自己、现实中的自己,三者同时在场。艺术家知道,这一切仍旧会在照片上被看到,如此隐喻媒体这张大网。
白南准《电视佛》,1974年
艺术家与面具的抗争
今天,人们面对精湛的肖像艺术时仍会赞叹不已,从中世纪的圣像画到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再到伦勃朗、莫奈、梵·高的自画像......肖像画在近代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文艺复兴之后,人的肖像越来越多。看起来,人的主体地位似乎是得到了确立。
左:委拉斯凯兹《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1650年;右:弗朗西斯·培根《教皇英诺森十世的肖像研究》,1953年
可是当欧洲文化孕育的肖像绘画取代了面具,它又何尝不是作为另一种形式的面具存在。将人脸转化成肖像画,说到底它还是人工制品。画家捕捉到的人脸并不是一张活生生的脸,而是一张无生命的面具。
日本艺术家杉本博司的摄影作品
伦勃朗自画像
其实关于这一点,很多肖像画家早就意识到了,所以伦勃朗才会不厌其烦地描绘自己各个年龄段、各种表情的自画像。他不希望自己的生命被定格在某一刻,成系列的自画像对他来说是对生命迹象的极力捕捉。
莫奈《自画像》,1886年
在19世纪后半叶以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开始拒绝毫无生气、只是作为社会身份再现的肖像画,他们开始尝试在肖像画里加入更多个人主观的诉求和情感,因此极具浪漫主义特征。
罗丹《塌鼻男人》,1864年
现代主义雕塑大师罗丹(Auguste Rodin),在他创作于1864年的早期作品《塌鼻男人》时,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抗拒人们所期待它所扮演的角色。他努力在雕塑的脸上镌刻上生命的痕迹,这是他塑造脸的方式,其中蕴含着一种对自然和自由的渴望。
曼·雷《泪珠》,1932年
曼·雷《黑与白》,1926年
1926年,艺术家曼·雷(Man Ray)创作了他最出名的作品《黑与白》。画面中,他的模特脸贴桌面,手托非洲的土著面具。可是这里的人脸竟也像面具一般,曼·雷通过这两者的并置,模糊了人脸和面具之间的界限。
安托南·阿尔托的死亡面具
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抽象”一度成为造型艺术的座右铭。这个时候,传统的肖像绘画显然已不合时宜。但是法国戏剧理论家、艺术家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却逆潮流而动,他认为传统的肖像画家为使人脸显得生动而满足于“单纯的表面”,而他所追寻的是一张真实的脸。
安托南·阿尔托的绘画作品
1948年,阿尔托在去世前不久完成了一张素描杰作。画面上,一张张脸彼此迎合,宛若在上演一场假面戏剧,阿尔托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呈现脸和面具之间的辩白、生命和死亡之间的角逐。
弗朗西斯·培根《肖像习作》,1955年
弗朗西斯·培根《乔治戴尔肖像习作》,1963年
弗朗西斯·培根笔下的人物往往面目狰狞、扭曲,和以前我们熟悉的肖像画全然不同。在他创作于1955年的《肖像习作》里,艺术家以强烈的个人风格制造出了一种生命的幻象,仿佛通过生命的在场表达对面具的反抗。
辛迪·舍曼摄影作品
在当代某些艺术家那里,他们通过摄影手法仿造肖像,不经意地揭露了肖像画的面具特征。美国艺术家辛迪·舍曼(Cindy Sherman)拍摄的一组以自己为原型的“历史肖像”,日本艺术家杉本博司拍摄的蜡像照片......都用照片营造了一种古典肖像画的假象,恰好证明了肖像画的面具特征。
杉本博司摄影作品
脸从来都不只是一张皮相而已,它是一个最具辨识性的身份符号。名人的脸和普通人的脸不一样,它的传播代表着某种权力、文化和信念的覆盖范围;死人的脸和活人的脸不一样,对死者照片的保存其实是对人象征性的留存;在好莱坞电影里,黑人脸的出现平衡着白人世界的价值观念……
努斯拉·拉提弗·库莱施《你是来寻找历史的吗?》,2009年
巴基斯坦艺术家努斯拉·拉提弗·库莱施(Nusra Latif Qureshi)在2009年为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作品《你是来寻找历史的吗?》中,将印度王朝统治者的头像和自己的头像叠印在一起,质问着西方观众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后殖民目光。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瑞士人的遗物》,1991年
法国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Christian Boltanski)在他的一系列装置作品中,为匿名死难者创建档案,通过一张张肖像照片为他们的生命留痕,还他们生命的尊严。
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敖德萨纪念碑》,1986年
从人造面具、肖像画到摄影和影像,艺术家始终与世俗和流行保持着距离,并以局外人的身份审视着这场关于脸的狂欢。以前,他们抗拒人脸变成毫无生气的死亡面具;如今,他们越发警惕“媒体脸”的侵袭。
基斯·科廷厄姆《虚拟肖像》,数码摄影,1993年
伊丽娜·安德斯纳“虚拟脸/Nexus7”系列,1998年
如今,脸显然已经越来越沦落为一个飘忽不定的幽灵。在未来,我们是否也能容忍它变成某些艺术家所预言的虚拟存在呢?
监制/齐超
编辑、文/尚峥妍
发布/刘璐
本文由《时尚芭莎》艺术部原创,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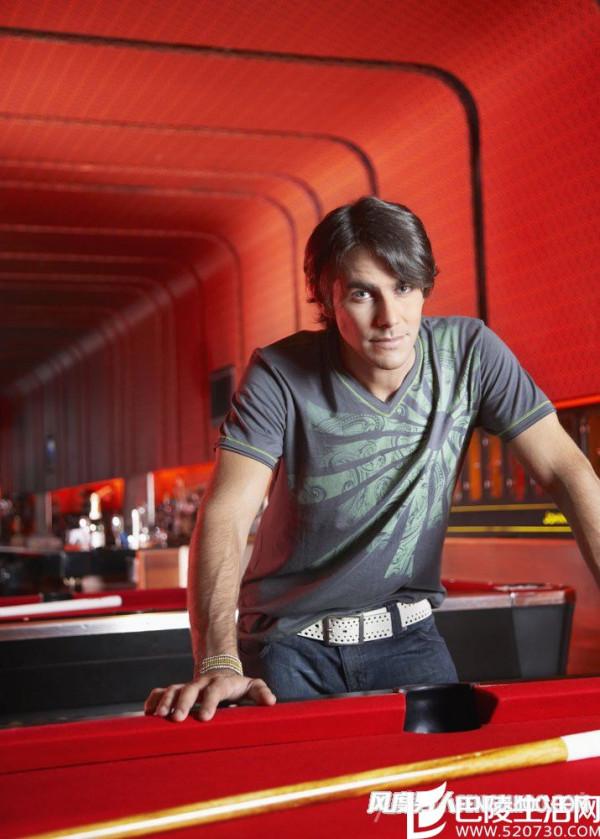


![中国人为何喜欢锥子脸 锥子脸受宠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都喜欢锥子脸?[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e/f6/ef6d004e8e63537b2ed228faa71d4450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