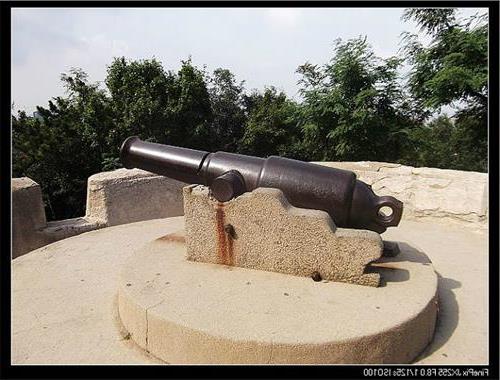清末山东巡抚丁宝桢杀大太监安得海
1869年9日,西太后宠信的大太监安得海南下采办龙衣,途经山东,为山东巡抚丁宝桢派员捕获于泰安,旋在济南伏诛,成为同治年间震动朝野的重大事件。
安得海(1844—1869),又作安德海,直隶南皮(一说青县)人。自幼乖巧,口齿伶俐,而为人狡狯。据载,他“艺术精巧,知书能文”,“能讲读《论》、《孟》诸经”(《清稗类钞》,南海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160页)。
当时,其家乡一带在宫中当太监者颇多,其中不乏发迹后成为暴发户者,这对安得海刺激很大。1855年,安得海12岁那年,因家庭贫困,遂“自宫入内为宦”(《清代野史》,巴蜀书社1987年10月版,第1辑,第139页),人称“小安子”。
因在家中排行第二,入宫得势后,人们又称他为“安二爷”。初受咸丰皇帝喜欢,渐升为御前太监。为扩大其政治权力,安得海拼命巴结权力欲极强的懿贵妃(即后来的慈禧太后),千方百计讨得懿贵妃的欢心。
1861年,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死,临终遗诏中封载垣、肃顺等为“顾命八大臣”,辅佐皇太子载淳。及载淳即位,皇后钮祜禄氏与懿贵妃并尊为东、西太后。不久,为了同载垣、肃顺等人争夺朝中大权,西太后发动了“辛酉政变”,将载垣、肃顺等八大臣或杀或贬,从而得以垂帘听政。
在这场政变中,安得海为西太后立下了汗马功劳。开始,西太后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制服八大臣,便欲和留守京师与洋人交涉的恭亲王奕訢相联合,但因热河远离京师,无法取得联系。
正无计可施时,安得海献苦肉计,让人打得遍体鳞伤,名义上是逐回京城,实则为了暗通消息。经安得海与其他太监的联络,终于使奕訢与西太后串通一气。通过安得海,西太后还联络了一批武员,其中就有手握护卫京城兵权的胜保。
胜保凭借手中的兵权,坚决主张两宫皇太后听政,反对肃顺等人专权,并公开扬言将带兵以清君侧。正是由于奕訢、胜保等人的鼎力支持,西太后才成功地发动了政变,得以垂帘听政。
(仝晰纲:《中国历代宦官》,济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287页)而安得海则因此更得西太后的欢心与器重。由于西太后对安得海“语无不纳”,安得海遂得逐渐干预朝政,“纳贿招权,肆无忌惮”《贪官污吏传》,北京占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他还“笼络朝士,使奔走其门,势焰骎骎”(《清朝野吏大观》,第1辑,卷1,第77页)。一次,恭亲王奕訢请见西太后,西太后正在和安得海谈天说地,竟然推辞不见。奕訢受到羞辱,十分恼火,退下后曾对其亲信说:“非杀安,不足以对祖宗、振朝纲也”(《近代稗海》第11辑,第30页)。
此后,在西太后与奕訢的权力之争中,安得海始终站在西太后一边,奕訢终被罢议政王。安得海遂愈得西太后宠信,势焰更,“朝士日奔走其门,声势煊赫”(《清鉴纲目》,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569页)。
同治皇帝登基时年仅6岁。安得海见小皇帝无权,更加谄媚西太后,甚且还在西太后面前讲同治帝的坏话,挑拨离间其母子关系。同治帝“尝因事斥安得海,旋为那拉氏所责罚”(《清代野史》,第1辑,第139页)。随着同治帝年龄渐大,他不仅对母后的专横日益不满,更对监视自己的安得海也“恨之益甚”。
因而,他常在宫中用泥土塑造一些小泥人,然后用小刀一一砍去其头颅,以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愤。其随从太监不解其意,曾问及缘故,同治帝则说是“杀小安子”,“于是,内监中知安得海之首领将不保矣”(《清鉴纲目》,第569页;《清代野史》第1辑,第139页)。
鉴于慈安太后也不满于安得海的跋扈,年龄渐大的同治帝遂与慈安太后策划,欲除掉安得海。
在同治帝看来,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为人正直,遇事敢为,将除去安得海之事交给他办比较妥当;而东太后也认为丁宝桢系“有肝胆之人”,可以信赖。1869年3月,丁宝桢进京叩见同治帝,蒙召见两次。其间,同治帝曾与丁宝桢密谋除掉安得海之策。丁宝桢对除去安得海之事慷慨应诺,并奏称:“闻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请执而诛之,以其罪奏闻。”
1869年5月间,曾充任曾国藩幕僚的薛福成自江南赴保定,途经山东时,鉴于其弟薛福保在丁宝桢幕府,遂顺便至济南拜见丁宝桢。丁宝桢与他谈论天下大事,“逾二旬不倦”。临别,丁宝桢告诉他说:现天下太平,“惟太监安得海稍稍用事,往岁恭亲王去议政权,颇为所中。
近日士大夫渐有凑其门者,当奈何?”停了一会,又说:“吾闻安得海将往广东,必过山东境,过则执而杀之,以其罪奏闻,何如?”薛福成与其弟一齐回答:果真如此,实在是不世之业。
其难度如同剿平一巨寇,功尤高,但事先布置要严密,行动要当机立断,否则不惟贾祸,亦恐转益其焰而贻天下患。丁宝桢表示赞同,并加快了筹备活动(《薛福成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这年,两宫皇太后正准备为同治皇帝筹办婚事。于是,西太后便答应派安得海去南方为同治帝置办大婚所用的龙衣。按照清廷祖制,宦官不得随便出京,擅出都门者就地处斩。同治帝得知此事,便密诏丁宝桢做好诛杀安得海的准备。
(《清代野史》第1辑,第139—140页)1869年8月10日,安得海“声称奉旨出京,赴苏州采办龙袍”,令在内廷当差的太监、苏拉(清代内廷机构中担任勤务之人)等13人跟从同行。8月13日,安得海由北京起程东行,随行的尚有其胞叔安邦太并随身服侍之安马氏、族弟安三、胞妹洛二、胞侄女拉仔以及在家服役之女仆2人。
其管家还为安得海雇了30余人随同服役赶车。他们由通州雇船沿京杭大运河南行,又雇一向充当镖师的韩宝清等5人为保镖,一路上声势煊赫,招摇过市。
安得海所雇船为两只太平船及数只小船。太平船船头上插着“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大旗,两旗上又插有一日形、一三足乌小旗,船内尚安放龙袍,沿途又雇妇女唱曲取乐。路经天津时,安得海还曾赴天齐庙游玩,因与庙僧滨文言谈投机,遂亦带领同行(《丁文诚公奏稿》,贵州省新闻出版局2000年版,第223页。
丁宝桢在接到同治帝密谕后,当即密嘱德州知州赵新:“传闻安得海将过山东,如见有不法事,可一面擒捕,一面禀闻”(《贪官污吏传》,第75页)。至8月17日,安得海一行乘船进入了德州境。德州是直隶、山东两省交界的重镇,又是南北水陆交通要冲。
鉴于次日是自己生日,安得海遂决定在德州停留一天,过完生日后再继续南行。这时,德州知州赵新也获得了安得海一行入境的消息。赵新聪颖过人,断案甚速,常常一次堂讯,即能结案,故有“赵一堂”之誉。
他访闻有北来太平船两只、小船数只已驶入州境,且“仪卫炫(煊)赫,自称钦差”,却“无传牌勘合”(清代奉命出京兵员由兵部签发身份证件,沿途地方官员要按礼迎送),“又未奉文行知”,遂顿觉可疑,随即委派妥员前往密访。
不久,该员回衙报称:“系安姓太监坐船,旗上大书‘奉旨钦差’、‘采办龙袍’字样,两旗上又有一小旗,上画一日形、一三足乌,船之两旁俱有龙凤旗帜,并闻船上设有龙衣一套,其所带之人,举动桀骜;且女乐成队,品竹调丝,以致观者如堵”(《丁文诚公奏稿》,第216页)。
18日,安得海率其随从乘船抵达桥口,令船靠岸,同时命管家黄石魁下船,登岸去采买肥鹅及大葱等食物。当时,安得海命人在中舱并排安放了两把太师椅,一把摆着龙袍一套,翡翠朝珠一挂;另一把则坐着安得海。船上的男女都一一上前给他磕头祝寿,并雇有妓女设宴作乐。
最后吃了“烧鸭寿面”。沿途遇有人盘问,韩宝清等保镖即上前肆行恐吓,致使民间颇为惊骇。当日,德州知州赵新亦亲率随从弛往查询,不料安得海祝寿完毕,即已扬帆出德州境南去了(同上书,第216、223页)。
赵新阅历广,经事多,官场经验十分丰富,对安得海过境一事要不要向上司丁宝桢汇报,颇费了一番思索。如不上报,怕得罪丁宝桢;如明白禀报,又怕一旦不能去掉安得海,自己反而遭殃。他召集幕僚密议,最后决定采用夹单密禀法。
这样,丁宝桢如不上折参奏安得海,则其密禀夹单即非例行公事可言,既不存卷,也让安得海无从得知;如果丁宝桢上折参奏安得海,则无论祸福则均由丁宝桢一人担当,而与地方官毫无关涉(薛福成:《庸盦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2—83页)。计划既定,赵新一面“飞移下站及邻封跟踪查访”;一面即用夹单将安得海过境事密禀于巡抚衙门,请丁宝桢核查办理(《丁文诚公奏稿》,第216页)。
丁宝桢接到赵新密禀夹单,遂据以上奏清廷,并指出:“我大清王朝列圣列祖相承已历二百余年,从不准宦官与外人交结,亦未有差派太监赴各省之事;况龙衣系御用之衣,自有织造谨制,倘必应采办,但须一纸明谕,该织造等立即敬谨遵行,何用太监远涉糜费?且我皇太后、皇上崇尚节俭,普天钦仰,断不须太监出外采办;即或实有其事,亦必有明降谕旨并部文传知到臣。
即该太监往返,照例应有传牌勘合,亦决不能听其任意游行,漫无稽考。尤可异者,龙凤旗帜系御用禁物,若果系太监在内廷供使,自知礼法,何敢违制妄用?至其出差携带女乐,尤属不成体制。
”而安得海到底系假冒钦差,还是捏词外出,丁宝桢尚一时真伪莫辨。但丁宝桢觉得安得海此番出宫南下,“显然招摇煽惑,骇人听闻,所关非浅”,现在虽然尚未见骚扰撞骗之事,惟自己守土一方,不能不派员截拿审办,以昭慎重。
于是,他一面密饬署理东昌府知府程绳武、署理济宁直隶州知州王锡麟及沿运河其他州县一体跟踪截拿,然后解赴省城亲审,一面又于9月5日将安得海出京招摇及上述办理情形一并奏报清廷(同上书,第216—217页)。
安得海一行乘坐太平船由德州南下后,一路驶至临清南湾地方,因见南行水路不畅(河水变浅,不能行船),遂弃船上岸,换上马车,改走陆路。其所带女乐,因车辆无法多载,随即付给工钱打发回去。但安得海仍带有妇女5人,其随从人员尚有30余人,外表多似镖师模样。
他们由临清经东昌府南下,先后沿东阿、东平、汶上、宁阳一带行走,“势甚迅疾”。所经州县官员先后将安得海一行踪迹上报,使丁宝桢对安得海的行踪了如指掌。当时,丁宝桢鉴于安得海随从人员众多,且多似保镖模样,恐怕他们“不服查拿”,遂又密饬各路巡缉武员酌带小队驰行,绕到安得海一行之前,与地方官相机捕拿(同上书,第217—218页)。
署理东昌府知府程绳武办事一向谨慎,惟恐安得海万一有西太后懿旨而招惹麻烦,自己担当不起,故接到丁宝桢追捕安得海的密札后,改换便装,头戴斗笠,脚穿草鞋,在炎炎烈日下,率精壮快马紧随安得海一行之后,跟踪了3天,一直追到汶上县,但却迟迟不敢动手。
于是,丁宝桢又加派总兵王正起发兵追捕(《薛福成选集》,第128页)。
9月7日,安得海一行本已南行至宁阳县,临时又改道东北,前往泰安游览。鉴于天色将晚,安得海准备在南关义兴客栈(驿站)住下休息,以便次日去泰山游玩。泰安当地文武官员为将其稳住,遂不动声色,前往客栈参见了安得海。
傍晚,泰安营参将姚绍修带所部官兵将义兴客栈团团围住;署理泰安县知县何毓福则会同守备刘英魁带领差役、兵勇冲进客栈,将安得海拿获,同时将其随从人员连同车辆等一并扣留。接着,总兵王正起也率队赶到。于是,由王正起、何毓福等将安得海及其跟随之人连夜解往济南(同上书,第128页)。
次日,丁宝桢亲自密审安得海。当丁宝桢责问其因何外出时,安得海傲慢地回称:“奉旨差遣,采办龙衣。”丁宝桢追问:“既系奉差,何以并无谕旨及传牌勘合?又何以携带妇女,妄用禁物?”同时叱责安得海“必属假冒,何能狡饰”(《丁文诚公奏稿》,第218页)。
安得海开始还勉强争辩,口称:“我奉皇太后命,织龙衣广东。汝等自速戾耳!”(《薛福成选集》,第128页)。继而经丁宝桢以其“毫无凭据及不应一路招摇震惊地方”严厉盘问,安得海始“形色惶恐,俯首无词,自称该死”。
丁宝桢又命搜查其随身所带物件,于贴身包袋搜出两个纸包,内有不同纸片两种,均系干预地方公事,经询问,确系安得海受人请托。至此,安得海假冒钦差、招摇煽惑已确切无疑。
接着,丁宝桢又提审安得海跟随之人,据供称:安得海声称奉旨采办龙衣,带领他们起程,实不知真伪,由天津坐船携带妇女多人同行。至临清地方,复又换乘马车,行至泰安,即被拿获。丁宝桢随即饬令属下将安得海随带衣箱打开检查,见箱内装龙衣一领,翡翠朝珠一挂,余均系常用物件。
检查完毕,丁宝桢又令将衣箱依旧封固(《丁文诚公奏稿》,第218页)。鉴于朝廷谕旨未到,具体何意也未可知,丁宝桢欲先斩后奏,为国除害,即使事后因此遭朝廷严厉谴责也不遗憾。但署理泰安县知县何毓福却长跪力谏,请丁宝桢再略待时日,候旨遵行(《薛福成选集》,第128页)。丁宝桢遂将安得海及其跟随3人饬令历城县知县孙善述严加看管,以候旨遵办。
9月8日,西太后见到丁宝桢奏折,“颇惶骇”,但事已至此,只得忍痛与慈安太后召集军机大臣及内务府大臣商议此事。慈禧问恭亲王奕訢及军机大臣文祥:“法当如何?”奕訢、文祥等皆言:“按祖制:太监不得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
请令就地诛之”(同上书,第129页)。慈安太后、奕訢等遂拟写了一道上谕,内称:“丁宝桢奏太监在外招摇煽惑一折……览奏深堪诧异。该太监擅自远出,并有种种不法情事,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宫禁而儆效尤?著马新贻、张之万、丁日昌、丁宝桢,迅速派委干员,于所属地方,将六品蓝翎安姓太监,严密查拿,令随从人等,指证确实,无庸审讯,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饰。
如该太监闻风折回直境,即著曾国藩饬属一体严拿正法。
倘有疏纵,惟该督抚等是问。其随从人等,有迹近匪类者,并著严拿,分别惩办,无庸再行请旨”(《清穆宗实录》卷264,第9—10页)。但因西太后阻挠,“谕留中两日未下,醇亲王奕譞亦力争,始下查拿之命”(《清鉴纲目》,第569页)。
11日,军机处字寄钦奉密谕到达济南。丁宝桢接旨后,即于次日委派兼署臬司潘霨、抚标中军参将绪承,督同济南府知府龚易图、历城县知县孙善述将安得海押赴西门外刑场(今城顶街一带)正法。
至于在泰安县所截留安得海随从人员及妇女、车辆等,丁宝桢又札饬何毓福等人一并解押来省,一俟人犯提解至省,即行审讯,以便与现已解省之陈玉祥等分别办理。而其衣饰等物,丁宝桢即饬令发交藩库存储。至于龙衣一件、翡翠朝珠一挂,是否安得海私造,抑或系其窃取,丁宝桢尚不辨真伪,遂决定另行委派员弁亲携连同所搜出之纸片两种,一并咨送军机处查核,以昭慎重。
一切办理完毕,丁宝桢即于当日一并奏报清廷(《丁文诚公奏稿》,第218—219页)。
不久,丁宝桢所派员弁将在泰安县所扣押的安得海随从男女人等,连同旗帜、车马、金银、珠玉、衣物等项押解回省,遂与陈玉祥等3犯共68人一并饬发济南府知府龚易图、历城县知县孙善述等确审。
至9月16日,清廷又寄发上谕,称:“安得海既经正法,其随从之陈玉祥、李平安二名,亦系太监,均著即行绞决。此外尚有太监几人,著丁宝桢于讯明后一并绞决,以儆效尤。其余随从人等迹近匪类者,即懔遵前旨,分别惩办……安得海衣物等项,毋庸存储藩库,即由该抚派员解交内务府查收”(《清穆宗实录》卷264,第26页)。
经丁宝桢亲自审讯,将陈玉祥等6名随同出都太监绞决,安得海的管家黄石魁、田儿及5名保镖共7人以“迹近匪类”一并正法;随从苏拉及安得海亲属等8人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丁文诚公奏稿》,第223—224页)。
所起获之物品,丁宝桢令人一并登记造册,计有骏马30余匹,最良者日行600里;黄金1150两;元宝17个;极大珠5颗;真珠鼻烟壶1枚;翡翠朝珠1挂;碧霞朝珠1挂;碧霞犀数10块,最重者至7两。其余珠宝亦甚多(《庸盦笔记》,第83页)。
早在9月9日清廷第一道密谕下发之后,消息很快传出,在朝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并对丁宝桢交口称赞。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翻阅邸钞,见安得海伏法,精神为之一振,将邸钞给幕僚们传阅,并呼丁宝桢字说:“稚璜成名矣!”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曾国藩闻讯后也说:“吾目疾已数月,闻是事,积翳为之一开。稚璜,豪杰士也”(《薛福成选集》,第129页)。
安得海被处决后,丁宝桢曾命暴尸三日,以示严惩。事后,由历城县知县孙善述为其购地埋葬(《庸盦笔记》,第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