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一帆为城市而设计 行人地位尴尬而卑微 中国大城市像为汽车而设计
对于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来说,过马路——这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却往往需要付出非凡的勇气和毅力。
打个比方,某天你想从自家居住的小区到马路对面的超市买些日用品,很可能必须采取以下步骤:先步行10分钟到小区大门;然后右拐向东走200米,翻过一道长达180米的人行天桥(过这种天桥需先爬上50米,横跨80米宽的马路,再走下50米);最后再向西折返200米,才能抵达原本与小区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
当然,当你提着采购来的大包小包回家时,还得再重复一遍上述路线。这一来一去,光在路上就要费掉你宝贵的几十分钟。
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大城市越来越像为汽车而设计的。在这样的城市里,行人的地位尴尬而卑微,不但要忍受汽车造成的噪声和尾气污染,更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路权”不断地被汽车挤占。隐藏在这背后的,还有汽车霸权对人身安全的潜在威胁——曾经有人观察过,广州海珠区的一个十字路口,为车亮起的绿灯有90秒,同一地方的行人却仅有不足10秒的“冲刺时间”。
吊诡的是,这些“为汽车而设计”的城市并未赢得驾车者的拥戴,尽管路越修越宽、“环”越建越多,可日益拥堵的交通同样令私家车主和出租车司机们头痛不已。
这场发生在行人、汽车与道路之间的“战争”,不过是人与城市进行“战争”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城市化进程也呈加速度发展。据官方统计,中国的城市数量已由建国初期的130多个增加到目前的660多个,城市化率则由10%左右提高到40%以上,几十年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历程。但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城市病”也开始在中国凸现,并且大有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的趋势。
属于城市化后发国家的中国,原本有机会借鉴各国的历史经验以避免“城市病”的发生。遗憾的是,我们非但未能如此,很多时候反而变本加厉。综观中国的“城市病”症状,既有其他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遭遇的通病,如住房交通拥挤、城市无序扩张等;也有我们较为独特的病例,如对历史文化遗存的大规模破坏、新城建设的“千城一面”等。
谁是这些“城市病”的制造者?谁把寄托着我们诸多美好想像的城市变得如此不堪?
旅美北京籍作家娜斯在一篇题为《痛恨宽马路》的随笔中,介绍了纽约街区划分的合理和道路设计的人性化之后评价说:“在城市改建规划上,到目前为止,北京似是最失败的。”这是否意味着国内城市规划师的水平比国外同行差呢?娜斯女士没有给出答案,但相信许多中国人——至少我们的规划师们不会同意这样的判断。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国际建筑学界有句名言:“城市建筑是长官、开发商、建筑师和市民合谋的产物。”这句话或许可以推而广之,适用于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等各个环节。毫无疑问,这种“合谋”其实是一种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制衡;在这场“合谋”当中,市民作为城市生活的主角,拥有不可或缺且举足轻重的地位。
而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建设中,恰恰是市民这个最重要的角色长期处于被忽略甚至抛除在外的位置。很多情况下,城市仅仅成为长官展示其政绩的舞台,长官的意志决定城市的走向。于是,我们时常从城市官员那里听到要在几年内将本市拓展到多大规模(多少面积、多少人口、多少经济总量)之类的“誓言”;于是,我们看到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陆,各地的城市景观都是清一色的大广场、宽马路、玻璃幕墙……
由官员主导的城市发展模式尽管效率较高,可以让市民更快地感受到城市巨变带来的好处,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强制拆迁对居民财产权构成的侵害;一些超出城市经济实力和实际需要的大兴土木给市民添加的负担,等等。在这一模式里,规划师和建筑师常常沦为迎合官员喜好的傀儡,开发商们则很容易通过“寻租”获取谋利的空间。
这种状况一方面与现行官员考核体系的不合理和民主制度的不健全有关,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特殊历史文化的反映。众所周知,城市的诞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就城市的起源、功能和特点而言,中国与西方的城市明显不同——在西方,城市最早是以市民会聚地的面目出现的,是市民阶层摆脱种种经济、政治乃至人身束缚而寻求自由的场所;而在中国,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早期的城市并非经济发展的产物,而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工具。
严格地说,古代中国只有“城”,没有“市”。
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城市显然已与过去有本质的区别,却仍不可避免地受到某些传统习惯的影响。举例来说,中国是目前少有的将城市划分行政等级的国家,地级市管县级市、县级市管小城镇,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设计的初衷也许是希望借助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市镇和农村的发展,但在实际运作中却出现了大城市压小城市、上位城市“吃”下位城市的问题。
特别是一些地级市由于城区的经济体量较小,靠自身财力不足以维持运转,只好动用行政力量从下级城市“抽血”,严重制约了后者的发展。
人们常说,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却不免忽略了因果关系的另一面——城市化应当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真正的城市化从来都是以市场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绝不能倚靠行政强权来推动。因此,尊重市民的主体地位,把城市发展的决定权交给市民,以此促使各种经济社会要素自由地优化组合与生长,才是中国城市的活力之源。
我们注意到,中央提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来,中国的城市发展战略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转型,从“GDP优先”、“重物轻人”向“以人为本”的正途回归。很多城市放弃了“国际化大都市”之类华而不实的口号,将目标转向建设“宜居城市”、“可持续城市”。
涉及到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等具体事务时,市民听证会这种民主形式被越来越多地采用(尽管在代表遴选、听证程序等细节上还有待完善);而在更深的体制层面,社区居民自治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探索已开始破题,并在一些城市付诸实践。
不过,在为民意日益彰显感到欣喜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再次对“市民”的概念予以厘清。对于任何城市来说,市民都应当涵盖居住在这座城市的所有居民。现行户籍制度把大量外来经商务工者排除在城市之外的做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无法接受:一个守法的公民参与创造了城市的GDP,却不能平等地享受这个城市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甚至难以得到起码的安全保证。
宽容和自由是城市精神的基石,也是市民社会的根本保障。只有在这个前提之下,一个健康理性的城市化时代才会渐行渐近,并最终导向国家的现代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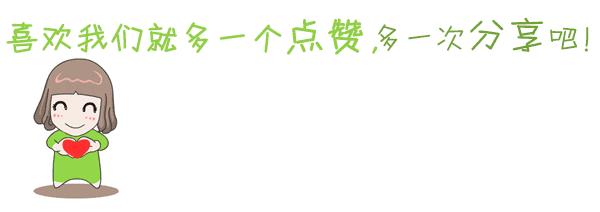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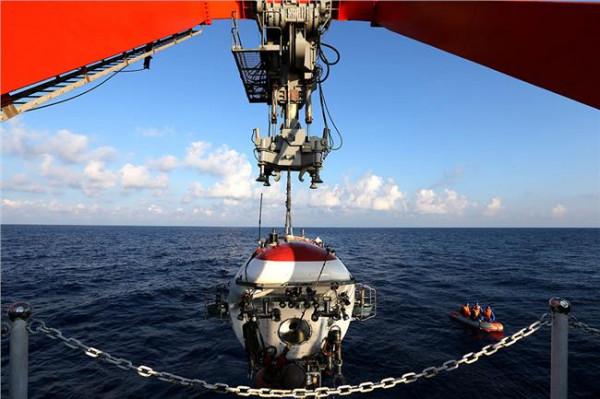

![>杨一帆上海交通大学 中共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e/fb/efb789da0885add6f6b3da6c43d7a055_thumb.jpg)
![>西南交通大学杨一帆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与上海交通大学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图]](https://pic.bilezu.com/upload/9/89/989288f96f8f47ac9fb920393b11e2a2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