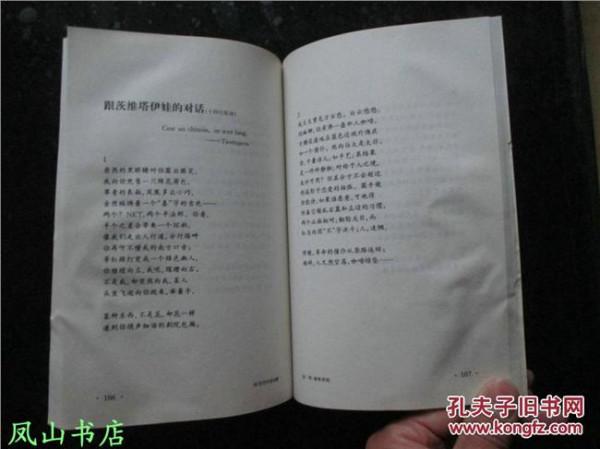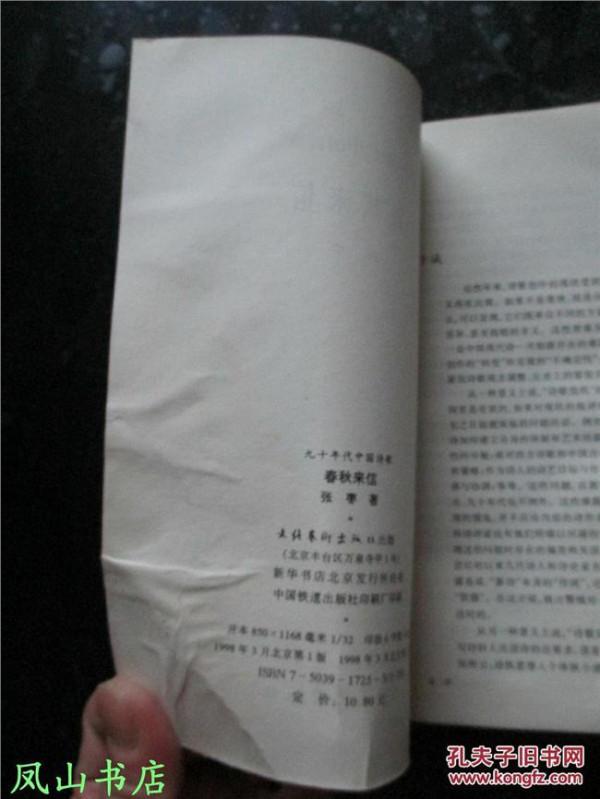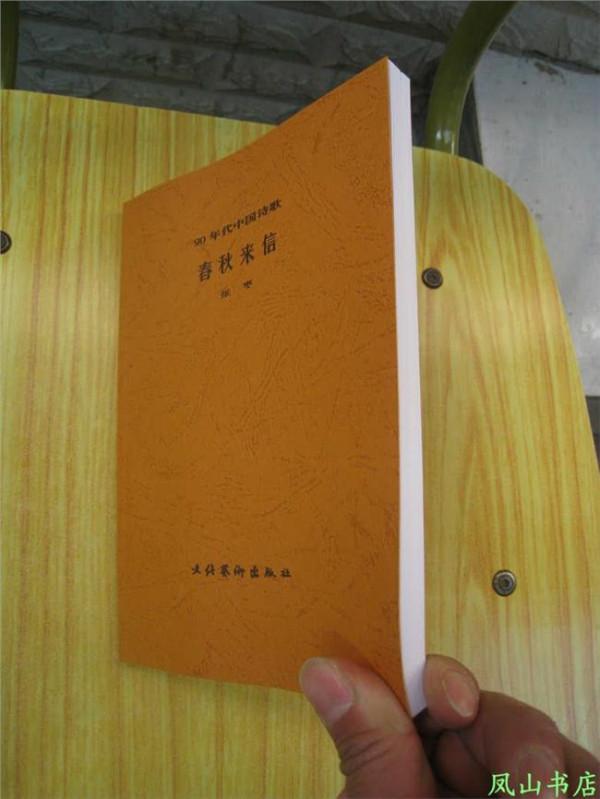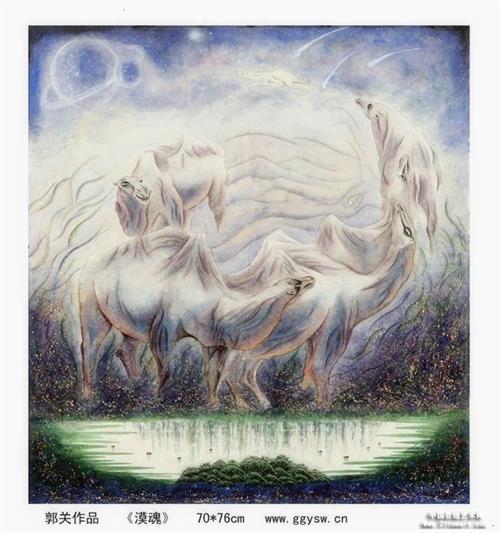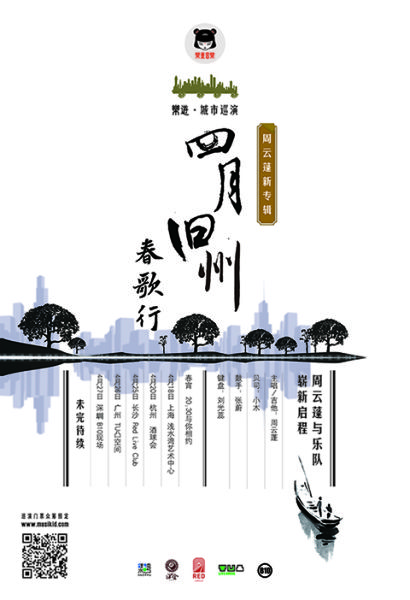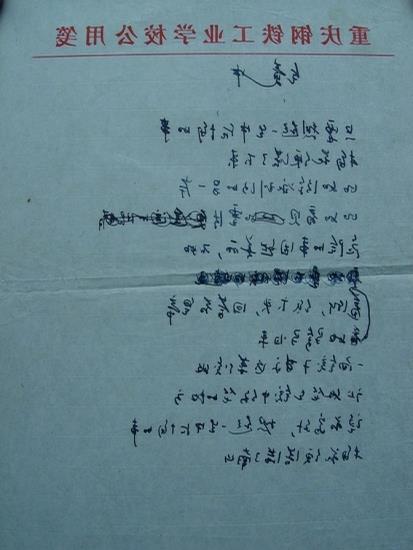张枣诗歌 诗歌细读:从“重言”到发现 ——以细读张枣《镜中》为例
和同时代很多诗人一样,张枣对欧美现代主义诗歌情有独钟,这首诗中的非个人化特征,就明显有来自艾略特诗歌观念的影响。基于这种喜爱,他径直将诗歌的现代性等同于“现代主义性”,在他看来,后者的标志即是“将语言当作唯一终极现实”或“对语言本体的沉浸”:“对写作本身的觉悟,会导向将抒情动作本身当作主题,而这就会最直接展现诗的诗意性。
这就使得诗歌变成了一种‘元诗歌’(metapoetry),或者说‘诗歌的形而上学’,即:诗是关于诗本身的,诗的过程可以读作是显露写作者姿态,他的写作焦虑和他的方法论反思与辩解的过程。
” 如果以张枣的这种“元诗主义”观念返观《镜中》,可以看到,诗中情境并非诗人亲历,而纯粹是语言的虚构,并且在这一虚构行为中暴露出语言自身,如抒情声音发出者与“她”和“皇帝”之间构成的关系,就很像是现代画家埃舍尔在他的画中所构造的那些不可能的建筑,而使观者注意到绘画行为本身。
在这一意义上,《镜中》无疑具有张枣所追求的“元诗”的性质。
诗不必是诗人一己情感的表达与现实境遇的倾诉,不必是对时代、社会的映射,而是向语言内部的倾注与投身,这样一种“元诗”意识和写作姿态,是新时期以来当代诗歌追求文学自主性的极致表现,今天很多诗人和批评家已对之做出反省和修正,但在这首诗写作的年代,还是一种全新的诗歌观念,既为当代诗歌开拓了新的审美空间,也凝结出一些极为出色的诗歌文本。《镜中》正是其中之一。
辨识出《镜中》的这一层“元诗”因素,就可以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发掘。这首诗中所显露的“写作者姿态”一方面固然是“对语言本体的沉浸”,另一方面,透过时间的距离,又可使我们看到其中观念与姿态的历史性的内容。在新诗历史上,自觉思考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的关系,创造性地汲取后者的美学资源,卞之琳有过成功的实践,他在晚年将他的实践概括为“化古”。
张枣的思考和实践也可归于这一脉络,而又有新的特点。“化古”表达的是一种现代性的主体姿态,但在卞之琳时代,由于去“古”未远,中国古典诗歌的表意程式和美学范型仍然有其实体性的乃至压迫性的分量。
而到了新时期以后,在思考和言说新诗与古典诗歌及其“传统”的关系时,当代诗人所普遍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未来主义”的姿态,在对艾略特的传统观的接受中,中国当代诗人实际上并没有接受其向古典主义回归的立场,相反,在他们看来,新诗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在于加入某种不断微调其秩序的威严“传统”,而在于向未来的投身,并且只有在这种投身中才可能有效地激活“传统”。
这样一种认识,无疑在现代性的话语延长线之内,但也有当代文化史的具体渊源,这里无法展开细述。由于这种认识,使当代诗面对古典诗歌及其“传统”显出一种较之早期新诗更为强有力的姿态。张枣在“传统”或“古典精神”的认识上,或许与当代其他诗人存在不可不辨的差异,然而,在《镜中》这首诗里,却似乎症候性地显影出了这一姿态。
在诗中,诗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在“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一句中得到了精彩的呈现。它隐喻着1980年代以来,当代诗与作为一种美学/文化的既有范型和压力装置的中国古典诗歌之间建立起来的一种新型的关系。换言之,在当代诗追求自身的现代性时,总会和“传统”形成一种镜像式关系,这个“传统”并非某种绝对的实体性的对象,也从未获得过稳定和确切的内涵,而是被当代诗自身所建构、所发明出来的事物,因而它并未显出一种在其他场合谈到它时常常具有的沉重、压抑的意味,反而显出一种轻盈的质地。
由于这种话语建构性质,它和当代诗之间构成的真实关系也并非是对象性、认知性的关系(“镜前”),相反,“传统”成为当代诗为自身发明的一个功能性的位置(“镜中”),通过它(无论其涵义是肯定的,即如张枣所言需要“进入和接近”的,还是否定的,即需要反抗或挣脱的),当代诗得以反复确认自身的主体性。
这并不是要否认,在中国古典诗歌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真实的、活的(同时也是一直在变动的)书写传统,也不是要否认新诗与古典诗歌之间存在真实的联系,就像前面已分析到的,《镜中》对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和抒情声音的化用,这种联系,往往是具体的,在创造性的技艺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而在另一层面上,在现代知识语境中,“传统”这一概念总是一种颠倒的认识论装置的产物,是一系列现代性的知识/话语从自身出发作出的阐释, 因此它也常常带有一种总体性的、不言自明的面貌,就像前文所引张枣关于“传统”那段话所体现的那样,因为它的内涵始终有待新的知识/话语的命名和填充。
也就是说,尽管张枣在话语表层表达了对“传统”的谦卑,但他实际上分享着当代诗人共有的对于“传统”的“写作者姿态”,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入地去理解这首诗中那个似乎突如其来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皇帝”一词所可能具有的隐喻意味,或某种文化无意识。
如果从“元诗”的角度,将之置于当代诗与“传统”的关系上,这个“皇帝”显然并非“传统”或“古典精神”的象征,而指征着新诗所具有的创造力,而这个“面颊温暖”而“低下头”的少女,则更像是古典世界的婀娜化身。
就像这首诗在读者中的影响所表明的那样,它的魅力与其说是源于它所建构的与中国古典诗歌之间的联系,毋宁说是在建立这一联系时,面对后者所显示出来的强烈的信心。而这种强烈的信心,正是八十年代文学、诗歌所体现的文化意识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
由此,我们才能明了,为何这首诗触及了追忆的主题,却并不令人产生这一古典诗歌的经典主题通常予人的哀感,反而却洋溢着一种明媚的韵味,带给我们的情绪,即使不能说是喜悦,至少可以说是悠然的。循着上述文化无意识的向度回头再来看“梅花已落满了南山”,这最后一句所具有的旷远、升华之感,其来由,恰可以说是从那个被虚构的“窗/镜”中,虽然在诗歌文本的表面,是“他”/“她”/“皇帝”正绵绵追忆着过去,而隐匿在文本之内的,却是八十年代新诗的自我意识,是它正在那一特定的历史时刻眺望和想象着自己的远方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