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伊斯兰 殷之光:“伊斯兰国”:戴着“恐怖主义”面具的新霸权
新近出现的“伊斯兰国”及其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是今天“政治伊斯兰”的“圣战”运动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现象。单从外部观察,那么它无论从宣传话语,到其行事方式,均能很好地为“政治伊斯兰”所勾勒的伊斯兰形象提供佐证。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伊斯兰国”的暴力及其反西方的本质主义立场,实际上很好地佐证了亨廷顿所描述的文明冲突;而“伊斯兰国”的政治调动模式及其诉求,则很好地契合了富勒对“政治伊斯兰”性质做出的身份政治认同的判断。 但是,如果简单的将“伊斯兰国”的出现,理解为文明冲突的必然结果,沿袭所谓伊斯兰传统对抗全球化现代性的二元论史观,那么便无法真正理解“伊斯兰国”对今天世界秩序能够造成的根本危害。
这种将“伊斯兰”及其暴力彻底他者化的逻辑,实际上回避了几个更为基础的问题。首先,无论是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政治伊斯兰”,还是伊斯兰宗教本身,为什么直至21世纪的今天,会以“哈里发国”的形式重新出现,并快速蔓延?其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政治调动方式的“政治伊斯兰”,为什么会在今天,甚至在欧洲内部的移民群体中,获得大量支持?最后,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是否存在一种话语方式,能够真正回应“政治伊斯兰”提出的反霸权抗议,并提供一种超越二元化批判的理解方式。
一般说来,如果我们沿用上文讨论的那种他者化的视角,那么“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Al-Qaeda)一样,会被看作是广义的“政治伊斯兰/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最具恐怖破坏色彩的武装袭击行动,则会被统一称作为“圣战”(Jihad)。
参与到这类活动中的个体,则在英语中被称为“Jihadist”(圣战者)。这一在英语中生造出的概念,有时也会被与阿拉伯语概念“(mujahid)混用。后者的复数形式(Mujahideen)在英语世界更为常见。
其最早为现代英语世界读者所熟悉,来源于前文提及的1979年阿富汗战争。一批自称为”Mujahideen“的游击队战士,自发组织抵抗苏联入侵,并随后得到来自美国的大力援助。
但是,很快美国便发现,这批信仰伊斯兰的”自由斗士“们在苏联撤军之后,很快便把枪口转向了美国自己。随着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与苏联正式解体,中东地区那种冷战时期形成的地缘政治平衡很快便因美国驻军沙特被全面改变。
成为地区新霸权的美国发现,冷战时期原本被掩盖在美苏二极争霸局面下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几乎是不加过渡地变成了一种游击队式的力量,四处挑战着美国在冷战之后试图建立的单极霸权秩序。 随着文明冲突论的出现,这种针对”霸权“的反抗,被理解为本质主义的宗教文明对抗。而随之,伊斯兰教法内部含义丰富的”圣战“,则越来越被简化对等于针对”异教徒“(kāfir)的武装袭击行动。
然而,在这种文明冲突论影响下,那种在伊斯兰内部出现的教法失衡却被彻底忽略。将伊斯兰他者化的叙述方式强调一种以伊斯兰教派为核心的分析方法,而忽略了教派内部之间教法层面上的互文互通特性。今天”反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为代表的一批圣战者。
他们普遍被认为是彻底的逊尼派萨拉菲主义者。 然而,我们仔细考察,便会发现一些在这种简单的本质主义教派范畴下无法理解的现象。以”圣战“运动中最为令人感到恐慌,也是最具社会恫吓力的”殉道“行为为例。
这种行为强调,为圣战目的而献身的”烈士“,不但会得到优厚的后世福报,还会被同组织内的人共同怀念与崇敬。这种”烈士崇拜教“(cult of martyrs)的传统构成了”基地组织“中一种重要的认同方式。
然而,有学者指出,这种类似”圣人崇拜“的传统一直以来是伊斯兰苏菲派等信奉神秘主义教团的核心特色。而这类神秘主义教团,则是萨拉菲主义者教义中明确反对的内容。
这种对殉道传统的政治性调用。实际上已经完全突破了那种一般意义上的教派分野。然而,在”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的政治宣传中,这种伊斯兰内部教法教义的交叉被策略性的模糊化。取而代之的,是用极简的语言,以及二元的逻辑,强调其教法解释的统一性。而站在”反恐战争“角度,将这种复杂性简化,不但无益于”反恐“行动,甚至可能有助于确证那种受特定教派强调的虚假的统一性。
在今天的”伊斯兰国“政治宣传中,其教法霸权恰是建立在这种对世界的二元化理解与对伊斯兰教法本质主义的诠释基础上。在”伊斯兰国“的建国神话里,2003年的那场战争是其发源。然而,有证据表明,在此之前,”伊斯兰国“重要领导人Abu Musab al-Zarqawi等反美势力早已在伊拉克境内活动。
但是,其突破性发展则应当得益于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后进行的大规模”去复兴党化“ (De-Ba‘athification)政策。
该政策旨在大量清缴政府内部与社会各个行业中的复兴党党员。这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开始于2003年5月16日。随后,伊拉克临时联合政府又接连颁发命令,进一步在社会各个层面推行深化”去复兴党化“的政策。
受到这类政策影响的职业包括政府各部门公务员(包括法官)、大中小学教师及教育官员、医务工作者、银行金融业人士以及军人等。 这一大批丧失了养老金的失业精英大量流入”伊斯兰国“前身”伊拉克基地组织“(Al Qaeda in Iraq)。”伊斯兰国“能在短期内迅速坐大,与这一清洗政策不无联系。
“伊斯兰国”不定期出版一份制作精美的电子刊物(具体刊名隐去)。其内容主要包括几方面。首先是对“伊斯兰国”性质及任务的阐述。其次是对其治理行动、战争胜利的宣传。再次包括对教法的“权威”阐述以及对反对意见的批判。
最后则有对“异教徒”世界的妖魔化描述。例如,在其中一期上,该杂志讨论了所谓“现代的奴隶制”问题。文中提到,今天所谓的奴隶制就是用工作时间,工资来束缚人的制度。这种制度由“异教头目”所创制。单纯的从语言上来看,我们甚至很容易把它与金融危机之后欧美世界兴起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简单化的批判相联系。
在其宣传刊物第一期,便有文章谈到,这个世界已经分成“两个阵营”(Two Camps)。这种冷战式的话语方式与今天小布什提出的“反恐战争”观念几乎完全重合。
在ISIS看来,世界是“我们”对抗“敌人”的格局。敌人包括“美国和俄国带领的十字军和他们的同盟”,其背后是“犹太人”。在这场全面战争中,ISIS还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活动提供了教法解释。
ISIS提出,这场对抗战争的目的在于破坏“十字军”世界的稳定,让“他们”陷入无休止的内斗之中(第4辑内容)。因此,每一个“战士”都有义务独立承担起这种责任,打击对象除了一般意义的战斗人员之外,对“十字军’平民‘”(Crusader “civilians”)也无需留情。
我们可以发现,ISIS发展起来的二元逻辑,甚至在国际法层面,也彻底否定了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发展来的当代国际战争法原则,及其对于战斗人员和平民的区分。
从形式上来看,“伊斯兰国”这份刊物非常“摩登”,排版精良,语言简洁。但是,从内容中分析,就能看出我们之前谈的“封建反帝”的霸权不平等特色了。它第一期的封面讲的是所谓“哈利发的回归”。在黑色大标题下,是一副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地图。
而阿拉伯的视觉中心,则落在了ISIS活动的核心地带:Al-Sham地区。这块地区包括了今天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确实在他们的政治宣传当中,遵照《古兰经》,叙利亚将会是他们发动最终大决战的地方。
这种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世界想象,实际上构造出了一个明确的等级差序世界观。虽然他们也会借助伊斯兰的大同想象--“乌玛”,但是从他们的具体政治宣传当中我们会发现,他们设想的乌玛不是世界人民大团结的乌玛,他们的乌玛是以阿拉伯为中心的世界帝国霸权。
在ISIS的治理实践与政治宣传中,伊斯兰教法内部的多样性以及教法学派间的争论被直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被ISIS“官方”认可的教条。ISIS认为,自己提供的教法解释是独一的,也是受国家支持的。
通过向其控制境内的教法解释学者颁发证书的形式,ISIS自上而下地将一个原本在伊斯兰社会内部自生的资源,用权力管制了起来。同时,ISIS还专门刊文,从教法角度,论证这种遵从“政治领导”(Political Imamah)的必要性。ISIS还系统针对伊斯兰内部反对其行为的教法批评进行回应,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排他的霸权式教法阐释。
我们还能发现,与先前的“基地组织”不同,伊斯兰国有一套治理理念,以及分五步走的建国路线图。从游击战对抗(Hijrah)开始,经过集合各方力量多点出击(Jama’ah),再到对异见统治者(包括穆尔西、阿萨德等不受ISIS认同的穆斯林领导人)治理区域的破坏活动(Destabilize Taghut),吸纳统合各地反抗力量(Tamkin),直至最后建成哈里发国(Khilafah)。
在伊斯兰国的宣传中,它也明确地表达了其治理理念。
在其“官方”刊物中,我们可以发现,ISIS设计了一整套完整的货币。作为“想象的共同体”载体之一,货币有能力传达一种最有效的认同基础。在其设计稿上,我们看到ISIS意图发行的货币均为金属硬币。
这传达了其将纸质货币视为虚假金融符号的态度。货币共分三种面额,分别以金、银、铜铸造,面值等值于铸币所用金属的价值。正面均为阿拉伯文标识的面额数字,反面为标志农业生产、宗教领导、武装斗争等方面的内容。除了对治理的构想之外,在其各期内容中,ISIS还会向读者展现其教育、养老、医疗、城市重建、市场管理、交通管理等各个方面的成就。
在“伊斯兰国”的政治宣传中,我们发现,其展现的是一个从物质条件,到治理手段,再到个人层面都充满着“现代”因素的“国家”。不得不承认,这个由一群手持单反相机、苹果手机,玩着《刺客信条》、《战地》等电子游戏,听着欧美说唱音乐流行歌曲的年轻人组成的“国家”,从根本上打破了我们那种建立在传统二元论基础上对这个世界以及现代历史的认识方式。
发生于阿拉伯世界的问题同样也具有其普遍意义。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以及意识形态阶级政治在世界范畴内的衰亡,一直以来压抑在中东世界的各种冲突开始集中释放。
传统的伊斯兰思想资源被“伊斯兰国”代表的特定威权所占领,民粹主义也披着伊斯兰的外衣大行其道。这种民粹主义依托了20世纪以来长久生长于阿拉伯世界心中的反帝反殖民思潮,以回归伊斯兰原教旨传统为口号,迅速席卷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空间。
对于霸权的反抗,目的在于对发展平等的追求。而今天以“平叛”为目标的国际性反恐行动,实际上并未能真正有效应对这种带着“恐怖主义”面具的新霸权。今天在中东地区出现的美国主导下的反恐及其反对的对象,本质上均诞生于那种在“国家利益”绑架下被化简的二元论世界观。
当政治退化为政党表演与国家利益财产权意义上的争端之后,暴力则成为了其实践的手段。必须认识到,20世纪早期伊斯兰现代化运动的多样性,是其本身教法发展的内生结果,作为其目的是回应当时影响愈加深远的现代化进程,而其希望处理的问题,也极具地区特殊性色彩。
这种现代化运动,在同时期的中国,则表现为以王静斋、达浦生等人为代表的伊斯兰现代化运动倡导者们,提出“遵经革俗”、“爱国爱教”等观念。
今天的“伊斯兰主义”成为了诸如“伊斯兰国”等组织建国神话的组成部分。这种本质主义教法观念不但破坏了阿拉伯地区的教法多样性,甚至还彻底割裂了伊斯兰与其它思想资源的联系,并进一步构成了伊斯兰对抗(西方)现代化的虚假想象。这也是霸权的一种呈现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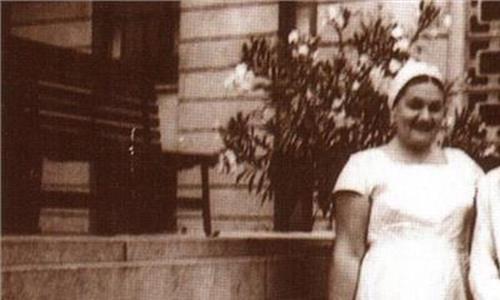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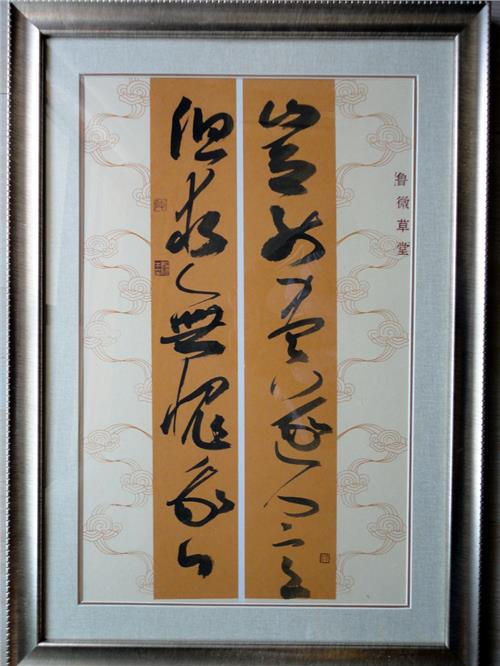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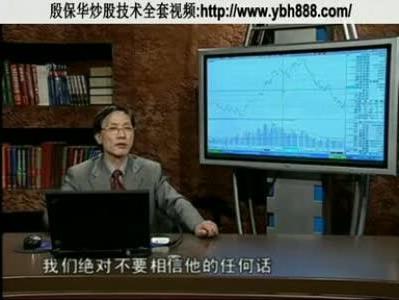
![>[30P]少年张三丰殷素素|少年张三丰殷素素|2001年《少年张三丰》](https://pic.bilezu.com/upload/2/93/293b80a3e44b76b50182620cc76a260e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