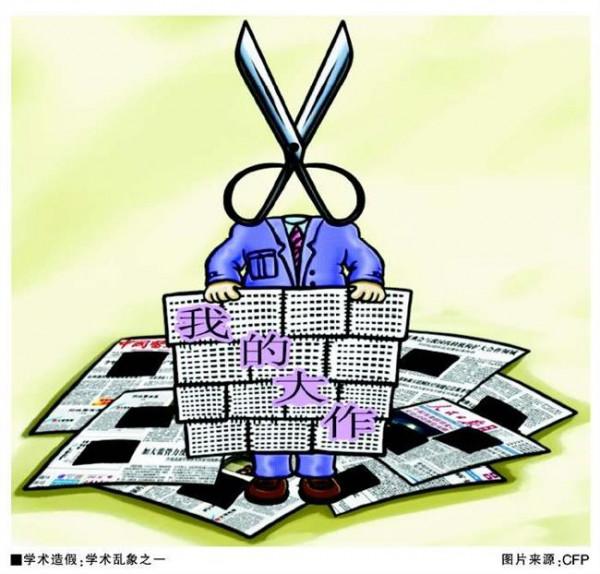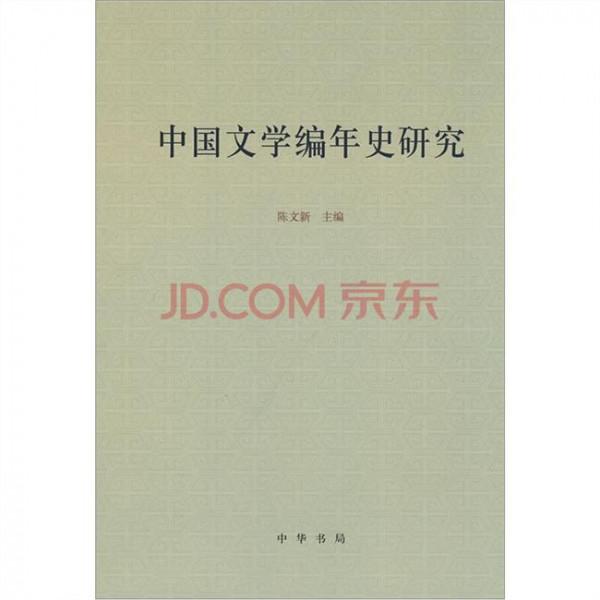汪晖新左派 徐友渔:评中国九十年代的新左派——说崔之元 甘阳 汪晖
二十世纪最后十年中国思想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发生在知识界的大争论。先是出现了新左派思潮并引起广泛批评,然后是自由主义思潮正式露面并引发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对峙。这场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兴趣,二000年开年不久,已有好几本相关资料汇编陆续出版。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感到不少人对这场争论的起因、过程、实质,以及双方分歧究竟何在,并没有清楚、确切的了解。比如有人认为,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新左派强调社会公正;自由主义者争取言论自由不过是提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而新左派提倡经济民主则是代表了工农大众的利益。
我认为,这种混乱不确的认识只表明了某种话语策略的成功。我愿在此阐明自己的看法,偏颇和成见在所难免,祈望各方指正。
(一) 新左派思潮的出现背景
新左派思潮以甚么机缘产生?为何它与自由主义的论争成了九十年代的重要景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思想学术论争格局及社会生活两方面的变化作一说明与比较。
首先是争论场地转移。在八十年代,党内高层思想路线分歧与理论界、社会上的观点对立是贯通一气、互相呼应的。而在九十年代,由于有邓小平"不争论"的指示,党内或官方意识形态对立很少张扬(当然也偶有发生,例如老左派的一系列"万言书"与《交锋》等作品的论争),知识界内部的争论显得突出。
其次是争论内容的更替。八十年代主要表现为革新与保守的对立,党内理论界表现为教条的马列主义与政治新思维之争,党外文化界表现为中西文化大讨论。而在九十年代,交锋的基本阵线是现代与后现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在九十年代,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和争论,更关注制度安排,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过程之类的现实问题。一批人文学者从哲学、历史、文学、思想史转入社会学或社会批判。有人说,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一个从哲学-美学到社会学的转向。
在八十年代,革新派知识分子中的主导倾向是对五四新文化和启蒙运动的继承与宏扬,与五四时一样,反专制、反封建是主要议题,批判自身传统,了解和借鉴西方学理蔚然成风。而在九十年代,风向发生逆转。八九年的六四风波之后,在批"全盘西化"(甚至具体到对电视系片《河殇》进行大批判)的指导方针之下,对西方学理的学习和借鉴变成了清理与批判,反专制、反封建的主题变成了反西方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在八十年代后期传入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急剧滋生,以前人们接触的是值得仰慕的西方主流文化,而现在开始流行暴露西方弊病,消解西方价值的非主流观念。
反专制、反封建从中心话题变成了禁忌,有人被迫暂时沉默。而从另一些知识分子的心理层面上看,这已经不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学问,而是直面现实的勇气和耐性的问题。痛感的尖锐性与求变的迫切性经不住时间与日常生活的消磨,迟早会松驰下来。
文化人求生和求新的本能驱使人转换话语。中国的现实并无根本变化,需要改变的是立场和视角。许多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当成另一个中国--与八十年代 不同的中国,与一九八九年不同的中国--来对待。这样,美国的问题会成为中国 的问题,西方知识分子的思维套路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模式,尤其是,当代西方左派对西方和全球问题的诊断会成为对中国问题的诊断。
在政治问题不得不暂时悬置起来的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凸显了。权力肆无忌惮地将自己汇换为金钱,本土资本的运作寸步难行,除非投靠和寄生于权力,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金钱(资本)作为第二种恶,对许多人而言显得比第一种恶更难于忍受。知识分子开始认真考虑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
中国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出在哪里,不同的知识分子给出了不同的诊断。
对于被称为(或自称为)自由主义派的人而言,他们始终没有忘记政治问题。他们呼吁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法治,以此来制衡权力,规范市场经济。他们的问题意识可以概括为:新情况,老问题。
而与之对立的新左派基本上认为中国的问题已经转换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危害。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而这么做的启发和激励因素可以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一九九九年爆发的民族主义狂热,使敌视西方阵营的新左派思潮在气势和舆论上占压倒优势。
(二) 所谓"制度创新"与国情
新左派的致命缺陷是脱离实际,为了得到自己预先设定的结论,为了施展自己刚刚学到的西方最新学理分析,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歪曲、割裂,强行纳入自己的理论框架。甘阳和崔之元在九十年代初指责中国知识界主流迷信西方经验,是"制度拜物教",认为他们根据西方最新学理和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发掘出的制度创新因素如果发扬光大,就可以对西方的现代性作出超越。
但把他们的高论和中国的现实相比较,只能使人产生哭笑不得之感。
比如,甘阳认为,中国乡镇企业具有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模式意味着,"华夏民族从农业社会转入工业社会,或许可能创造不以彻底摧毁乡土社会为代价的历史经验。果如此,这不仅对华夏民族''生活世界''之历史延续具有无可估量的意义,而且将是对人类文明史的莫大贡献。
""中国乡镇企业所提出的问题,毋宁应该看作:中国现代性对西方现代性的挑战,并正在形成对西方现代性的一种 alternative。"(见《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载《二十一世纪》1993年4月号第5页)甘阳以"对乡土中国的大量经验研究"为自我标榜,但中国的现实如何呢?
真正从事过田野调查,把结论建立在实证考察之上的农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乡镇企业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原则,关键是不允许农民改变身份。中国社会半个世纪最基本的事实,最重要的分野就是城乡二元化,全部人口分成了"有城市户口者"和"农民"两个等级,他们在居住、求职、受教育、医疗、福利各方面享受完全不同的待遇。
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的结果。"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决非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更非广大农民的心愿。
和城市化相比,乡镇企业的形式使城乡收入差距无法缩小,便劳动力的转移处于不稳定、低效率状态。千百万农民不顾艰难险阻涌入城市,形成震动各方的民工潮,充分说明把农民束缚在乡土上是多么不合理和不得己。(参见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载《东方》1994年第1期)
指出乡镇企业发展的困难和实质并不是想否定其成就,与以前那种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比,乡镇企业无疑带给农民一定程度的机会和富裕。我们也知道,立即、彻底取消城市/农村身份差别,是不现实的。但从农民自身的利益和中国农村发展的前途看,取消身份制毕竟是无可回避的必要条件。
前不久中央政府在使农村人口取得城市户口方面松动了很小的一步,立即被各方人士欢呼为中国改革户籍制度有重大意义的举措,可见人们对于甚么是文明和进步,心中是有数的。
不顾事实,把数亿中国农民的无奈当成取代西方文明的生发点,在美国校园中畅想自己如何洞见了落实文化中国的历史机遇,真不知叫人说甚么好。更有甚者,把与自己对立的一派知识分子说成是津津乐道于"不平等的自由",是贵族派,标榜自己的"平民"立场,天下还有比这更滑稽的事情吗?(见甘阳《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载《读书》1991年1月号第85页)。
崔之元也喜欢谈乡镇企业,他是要说明,大跃进固然不好,失败了,但其中也包含了相当的"合理因素",乡镇企业就是大跃进的合理因素(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载《二十一世纪》1994年8月号第7页)。但他对下列事实不作解释:为甚么大跃进、人民公社使乡镇企业办不下去,而只有在彻底否定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做法之后,乡镇企业才有突飞猛进?
崔之元急不择路地为人民公社评功摆好,把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的村民民主自治也归功于人民公社:"1958年后建立的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体制,虽然不如今天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灵活,但也为今天的村民民主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首先,土地的集体所有,为乡村的民主自治切切实实创造了有利的前提……其次,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双层经营'',并非简单地分田单干,乡村公共建设、产前产后服务等''集体层''更趋重要,各家各户在为乡村公共财政交纳税费时,必然同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从而为乡村民主自治提供了物质利益动机(见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第15页)。
崔之元的以上议论只能使对中国现实有所了解的人目瞪口呆。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村民和村一级的集体连种甚么庄稼、怎么种的权力都没有,村民们失去了自留地、果树、甚至炉锅碗瓢盆,他们吃饭去公共食堂,行动军事化,常常在半夜打着灯笼搞大会战,上级的命令不论多么荒唐(比如种薯要挖地三尺,插秧株距3寸,砍光树木去大炼钢铁)都得执行,不然会被捆绑、斗争、监禁,这是中国农民最没有自主权的日子。
在这段时间,任何违背农作常识和基本生存的命令他们都无法违抗,其结果是饿死三千万以上的人。这居然是"为村民自治奠定了重要基础"!
崔之元想说明的是,公有或集体所有,是民主自治的前提。他的例证是"印度地方选举常被大地主操纵",多么奇怪的逻辑!其前提是:民主自治的唯一阻碍是金钱势力,其推理是:凡没有金钱作祟的地方,就一定有民主自治。那么,怎么理解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呢?
崔之元似乎完全不懂得下列道理:只有当人们的生产资料和财产有保障,他们才可能有自由、民主、自治。
中国目前的乡村民主,说到底是国家"给"的,当然也适应了分田到户的形势。崔之元企图为中国当前的乡村民主提供一种物质利益驱动机制的解释:村民为公共财政纳税,必然(?)要求政治参与监督。这完全是一种在西方历史上起作用的机制,比如人们常说的美国公民的"纳税人意识",又如英国近代中产阶级抗争皇权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
这些当然很好,但可惜中国的现实并非如此。名目繁多的税款、集资、摊派,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的强征强收,这一切并没有使村民树立"交了钱,我就是主人"的意识。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严禁滥收费乱摊派,而这种命令收效甚微,充分证明崔之元的解释模式之荒唐可笑。
二 评中国的现代性与批判
(一.) 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与汪晖的分歧,同样涉及到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汪晖与崔之元和甘阳在立场、观点方面相当一致,但论说的侧重点不同。他没有专门论说中国旧体制中有多少优秀事物,可以与西方最新冒出苗头的优秀事物媲美,或可以形成超越西方文明的因子。他着力证明,中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社会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是一个市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能变了,知识分子的功能、与政府的关系变了,知识分子的批判对象也应当变。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社会作用是批判,在汪晖看来,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在九十年代却表现出批判性的丧失,因为他们并不全力以赴地批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他在发表于《天涯》1997年第5期上的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当此文收入另一文集《田野来风》时,其名称是"市场时代的降临与思想的溃败",把主题表达得更直露了。

















![[14/8/2010]难忘的旋律:新中国50年代电影歌曲精品连播(原声原唱)](https://pic.bilezu.com/upload/3/35/335245d7bb9f68da8f364d294de109fa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