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百度云 怎样从文学角度评价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高行健?
窝正好就《灵山》写过点东西,可能有点文不对题,不过还是直接复制过来好了,有空用电脑排版: 無須諱言,即使身上注定帶有大量的政治烙印,任何一個關注華語文學的人都不應該錯過高行健這樣一位充滿爭議的作家。令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靈山》同高行健這個人一樣,充滿了爭議與矛盾:《靈山》這樣一部作品,由於其獨特的寫作方式以及敘述手法,讀者很難在初次閱讀中看出這部作品究竟在寫什麼,只能從字裡行間體會到高行健筆下的中國——或者說“靈山世界”中瀰漫著的憂鬱以及若有若無的絕望。
然而,《靈山》這部小說確乎是一部悲劇,而且與王國維先生所說的,悲劇的第三重境界或有相似之處。因此,筆者在這裡選擇《靈山》這部作品進行分析,並期待這一篇東西能夠將這部作品中的悲劇人物以及背景群像揭開一角。
首先,筆者想簡單介紹下《靈山》中出現了的人物形象。 嚴格意義上來說,《靈山》這部作品並不存在狹義上的主人公。高行健寫作的這樣一部厚達六百一十六頁,分割為八十一個章節的的小說裡,並沒有出現一個“有名字”的主要人物。
《靈山》這部作品最為顯著的特點——同時也是這部作品最令人迷惑的幾個特質之一——便是交叉的人稱敘述。高行健在《靈山》絕大多數章節中,用一半時間講述故事是“我”,另一半時間是“你”:“我”说的是一個中年作者(或許便是高行健自己)在自己診斷為癌症後,得知自己被誤診,開始在中國南方的進行一場廣泛,深入而又散漫的旅行——“我”說的,便是這次旅行的記錄;而“你”則在進行一場尋找“靈山”的旅程,從始至終高行健都沒有讓“你”告訴讀者什麼是靈山,我們的視線只能隨著“你”向著遠在遠方的不知其所在的靈山前行。
書中的其他人物同樣沒有名字甚至代號,他們各有特點,內在卻似乎是一致的。
其中比較重要的一個人物,是和“你”邂逅的“她”——這也是《靈山》中少有的,可以描繪出人生軌跡的角色:一個年輕的學習醫學的女性,因為不喜歡自己所修習的專業,恐懼日後可能過的醫生生活,加之被初戀男友始亂終棄,決定逃離原有的生活,前往“你”所徘徊的中國西南的邊陲小鎮。
而高行健在這部小說裡描寫的更次要的角色則有太多太多,有大山深處的守林人,有在森林中科考的植物學家,有雕刻塑像的木匠,有在小縣城碌碌無為的小官僚……这些扁平人物构成了《靈山》世界的人物群像。
如果按照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所下的定義,《靈山》並不能很合拍地算作是“悲劇”——它並不是“對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模仿”,也並沒有由順境轉入逆境或者由逆境返回至順境的過程:整部作品的基調是冷峻的,或者說,死水微瀾的。
正如高行健自己所鼓吹的那樣:這是一部“冷的文學”。它只符合一點,即這部作品引起了讀者的憐憫與恐懼,並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Katharsis,羅念生先生將此詞譯為“陶冶”,而朱光潛先生則從亞氏《政治學》中對照,譯為“淨化”。
筆者此用羅念生先生的說法更為妥當)。如果讀者把視角轉到前文所介紹的幾個角色,我們能夠很清晰明了地看到,所有《靈山》中的角色都是“非典型”的中國式悲劇人物。
先從“我”談起。 高行健筆下的“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高行健本人的投射(Projection)。高行健由於他的立場,在國內受到了政治與文化層面的打壓,過得並不算如意,書中的“我”也是一個在政治上犯了事兒的作家,預支了幾百元錢的稿費遊走在南中國的大地上——從川藏邊境到上海,順著長江而下。
書中關於“我”的部分是冷靜的,“我”似乎始終只是一個旁觀者與聆聽者,或許稍微比一般的中年人多了些冒險精神。
“我”所聆聽,目睹以及書寫的世界是乾淨的,乾淨得甚至難尋血色,也好像是一副水墨畫,展現給讀者的只是“我”的世界的一個輪廓,更多更深層次的東西只存在於畫軸上大片的留白中。
“我”的遊走始於確認自己被誤診後離開北京,雖然有些許薄名,卻連新書都未必能夠出版。當然,更確切的說法是被北京流放,被踢出了主流的文化圈子。
“我”的這場遊走本身就是浪漫主義式的悲劇,其精神與拜倫所寫下的長卷《恰爾德•哈羅德遊記》或有共通:一個流亡者被排除在主流話語圈之外,開始旅行,並在旅行中完成對自我的尋找。“我”並沒有給出探尋之後明確的答案,答案或許高行健已經給出了,他們藏在那些遺落了的風俗中,藏在深山中匠人的手裡,藏在一個個不起眼的寨子裡。
然而,縱使“我”找到了自我,回答了“我來自何方”,這些東西仍然在漸漸消失,這是人力無法改變的,悲哀的現實。
造成這樣悲劇性後果的,與身在其中的人類無關,是當時的大環境使然,書裏書外的人,無非是在這個時代大潮中翻滾搏浪的小舟,對改變無能為力——這或許是最大的悲哀吧。 與主角是“我”的冷靜近乎白描的描寫相比,主角是“你”部分的描寫則是熱烈而奔放的,內斂的情感在這一部分不停地湧動,甚至要噴出紙面。
同時,關於“你”的部分,中,故事也要更加收束一些。“你”一開始就是一個流亡者,不知為何在尋找一個叫做“靈山”的處所。
“你”遇到的所有人似乎都知道靈山這個地方,但是似乎所有人都不願意告訴“你”何處才是靈山。“你”就這樣,通過些許路人的指引(或許也是誤導),一路前行。在這個叫做烏依鎮的地方,“你”遇到了“她”,並與“她”陷入了愛河。
“她”似乎也在尋找靈山的路上,而“你”從此不是孤獨一人。在這個部分,高行健似乎為了彌補“我”部分的冷峻與壓抑,幾乎控制不了他的筆觸,在“你”和“她”之間發生的故事中插入了大篇幅的性描寫:“我”的部分是《靈山》的表象,是日神的造物,而“你”的部分則被酒神所引領,我們從這裡接觸到的是《靈山》世界的本質:靈性的,也許有幾分是肉體的。
筆者認為,正是八十年代整個社會屬於一種“失根”的虛無狀態,物質侵吞了原有的質樸。
在這個環境下。某種意義上,“你”是一個對(不可知且不確切的)精神境界——即靈山的追隨者。然而,時代已經變了,刻意的尋找反而難以尋求到自己所想要的東西:“你”越往後就越虛無,越“瘋癲”;以為距離靈山越近,靈山反而更遠。
“你”似乎已經走了很遠,卻又似乎根本沒有離開烏依鎮,連陪伴著“你”的“她”,也變得稀薄起來。靈山在何方?“我”不知道,“你”已經迷失,讀者在雲裡霧裡——直到書末,原來有跡可尋的“你”“我”人稱切換變得更為雜亂之後,作者才用這樣一段對話,稍微透露了靈山面目的一角: 他孑然一身,遊盈了許久,終於迎面遇到一位拄著拐杖穿著長道袍的長者,於是上前請教: “老人家,請問靈山在哪裏?" “你從哪裏來?"老者反問。
他說他從烏依鎮來。 "烏依鎮?"老者琢磨了一會,"河那邊。" 他說他正是從河那邊來的,是不是走錯了路? 老者聳眉道:"路並不錯,錯的是行路的人。
” 與“我”在尋找自我中最後感到的無奈不同,“你”的尋找本身就是虛無主義的,更悲哀的是,“你”在尋找的過程中,已經迷失了。與“我”的悲哀不同,“你”的悲劇是個人化的,即使色彩更加濃重。 但是,高行健筆下的人物所尋找到的,究竟是不是他們真正的自我呢?即使能夠上了靈山,然後能得到什麼呢? 就像尼采在《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開篇所寫的那樣: 當查拉圖斯特拉三十歲的時候,他離開了他的家、離開了他家中的湖泊,然後到了山上。
他享受他的靈性與孤寂,他十年來都不曾為之感到厭倦。 但是最後他的心轉向了……查拉圖斯特拉的『向下走』從此開始了。 查拉圖斯特拉所在的山——一個修煉身心,享受孤獨,充滿靈性的地方,與靈山或許存在共通的地方:神秘,並不可避免地充斥著逃避的意味。
尤其是在高行健這個作者本身的流亡者背景之下,《靈山》的隱逸氣質實在是很濃烈。然而,查拉圖斯特拉最終還是下了山,即使“你”和“我”能找到靈山,又如何能保證在這座山上呆一輩子呢? 這也許是這部作品中,最濃厚的悲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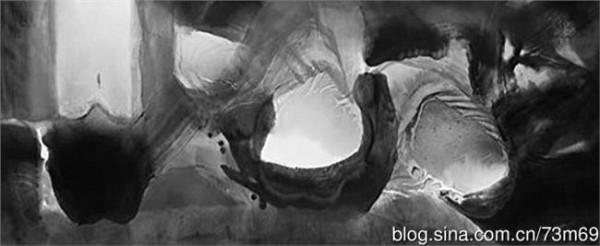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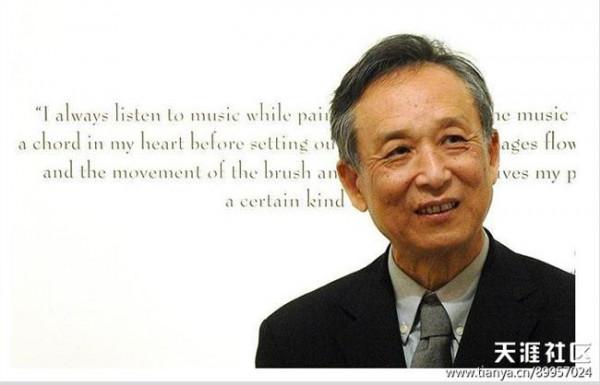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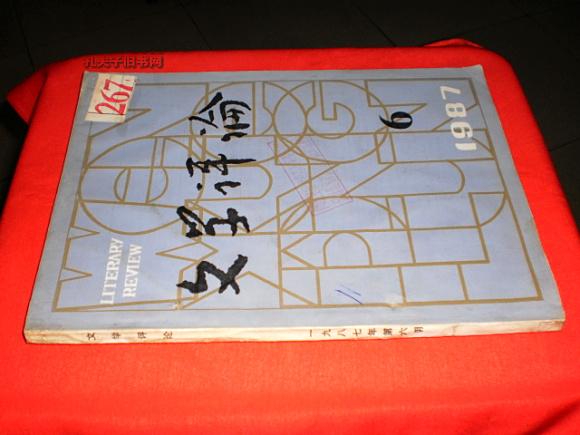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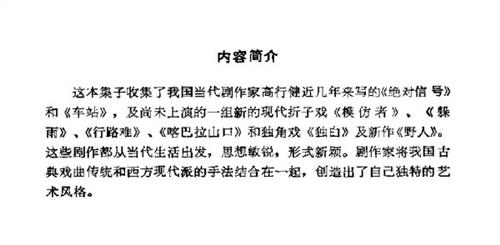



![>宋仲基电影五感图 宋仲基五感图完整版百度云中文字幕[经典推荐]](https://pic.bilezu.com/upload/1/f7/1f791b40e845066b23526ef1106703c4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