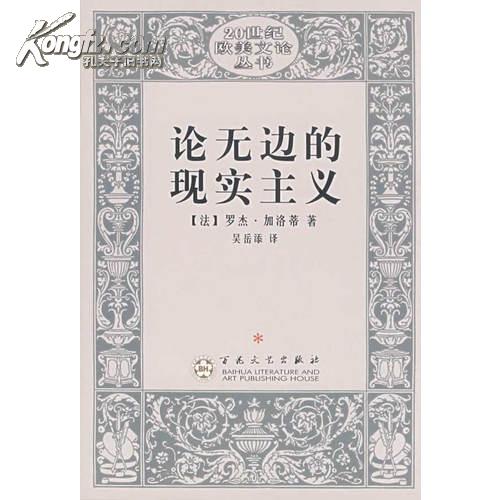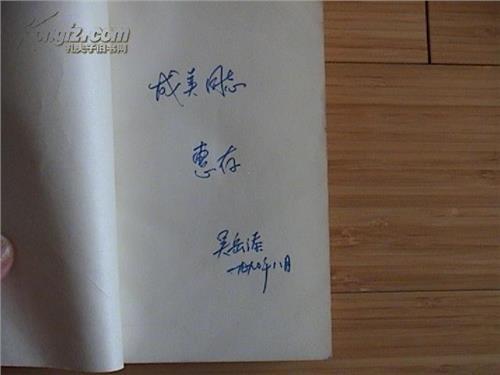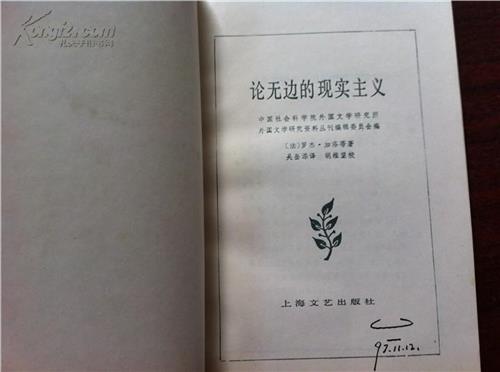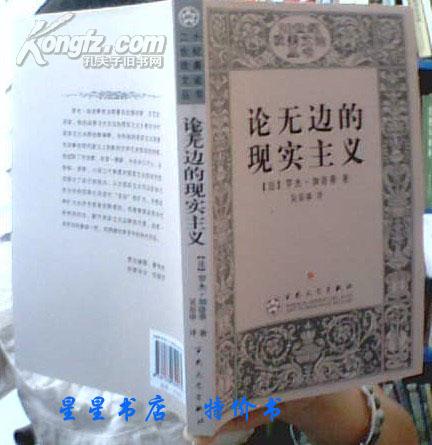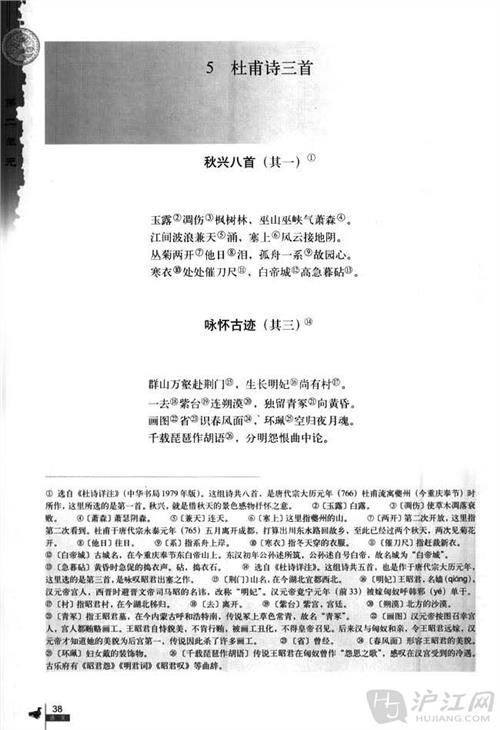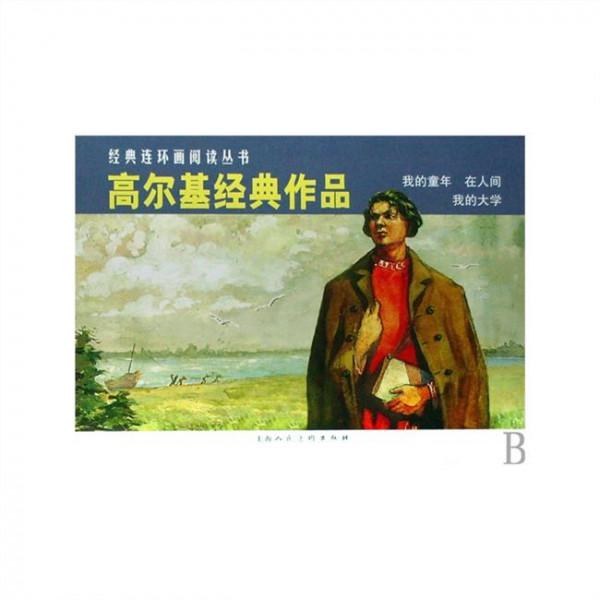栗宪庭现实主义不是 仍然是无边的现实主义
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在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进程里一直没有消停过。现实主义是否是唯一正确的道路,这样的大激辩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而现在,新一辈的学人又通过自己的个案研究、批评工作对现实主义做出更为本质性的反思。如果说,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就是对现实主义质疑、斗争、消解、吸收的三十年,这种说法毫不夸张。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质疑,还是消解,它们并未否定现实主义作为一门现实的艺术而产生的强大社会批判力,而只是把矛头指向了现实主义的种种虚假外壳: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红光亮的现实主义、媚俗的现实主义,等等。
本文的写作也是基于对现实主义与当代性这组命题的反思,而它多半源于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新世纪开初,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重大现象便是关于里希特的讨论愈发热烈,这种讨论在2008年中国美术馆举行格哈德里希特回顾展时更是达到高潮。(1) 我不能肯定“模仿”这个词是否能准确或不含偏见地表明中国当代艺术接受里希特时的心态,但存在的事实是,不占少数的艺术家对里希特的接受,是从一种风格走向另一种风格,其间似乎并不存在连续性。而作为比较,即便是在抽象绘画和具象绘画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里希特仍体现出精神的一致性。
可以想见,同样有着社会主义经历的艺术家,里希特会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中国艺术家们一种身份认同感和宿命感。同时,鹊起于八十年代、为西方主流艺术圈层接纳的里希特确实又为浮躁的中国当代艺术平添了一份成功的范例。但种种机缘背后,里希特现象的流行仍然在于那个徘徊在艺术家思想里、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的幽灵,这个幽灵在六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内有效地实现了艺术家们一种入世的社会情怀,但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他们观看和表达的模式。具体到里希特这个案例,当中国当代艺术学习、模仿、照搬这位当代性极强的艺术家风格时,究竟是现实主义被当代化,还是当代艺术被“现实主义化”?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后者。
单向度的现实主义
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是一个与当代性有冲突的问题。这是本文所立足的第一个基本判断。即便不断然地下结论,现实主义不具备当代性的可能条件,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不从对现实主义的旧有认知中挣脱出来,对当代性的思考仍将停留在一个保守而僵化的层面。
本文并不尝试对“什么是现实主义”作本源性的阐释。作为不稳定概念,现实主义在20世纪已经成为最令人困惑的一个术语。(2)同样,本文也不想通过某些限定,诸如相似、错觉等来设置一个绝对的现实主义标准。很显然,中国的现实主义标准尤为混乱,在为工农兵的文艺、为大众的文艺,尤其是为政治的文艺方针指导下,现实主义画家在不同阵营里被安排、被决定,原本仅为一种单纯的风格样式,却成为艺术家命运的准绳,并随着政治天平的摆动而起伏波折。
然而,无论怎样变动不居,我们仍可以归纳出现实主义在中国确立以后的某些共性:(3) (a)画家群体均受苏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影响;(b)题材和内容均构成作品阐释的核心;(c)作品均不指向绘画本身,缺乏艺术自律。除为数不多的静物画、风景画、肖像画外,大部分作品往往还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4) 作为占据统治地位的主流艺术样式,现实主义确立自己的方式十分戏剧化,五十年代初期《中国美术》关于现实主义的大争论便是一例。八十年代,伴随着清除精神污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来的第八届、九届全国美展,其微妙却严厉的官方措辞恰似一张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它们给人的印象则是,现实主义在中国的确立远非自发生成这么简单,它运用的方式正是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活学活用。
而在另一边,当我们谈起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时,多是侧重于它反叛性的一面,事实上,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主义色彩,栗宪庭在评价其推出的政治波普时,就有过很形象地说明:“对比中国的‘政治波普’,如王广义在使用商业符号时,由于过于依赖叙述性,而干扰了对商业语符的视觉语言的转换。其他中国艺术家作品的语言强度,亦多囿于叙述性。这大概由于写实主义教育给他们带来的影响。”(5) 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即便在舶来西方当代艺术时,现实主义仍旧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使艺术当代性的因素被弱化。而与政治波普同时期的新生代绘画、玩世现实主义,在进行绘画实验以及表达个体经验时,叙事性仍旧构成了这种实验和经验的核心。
1990年代中后期,全方位的前卫性实验在绘画中展开,精神分析学、身体政治学、图像观念的引进前所未有地增加了艺术家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和深刻性。之前,局限于“典型化”、“符号化”等单一手法的现实主义也因为寓言、象征、戏拟、反讽等后现代主义手段的运用而变得丰富多彩。(6) 然而,作为艺术家理解现实的一种手段,题材和内容仍旧占据了其中的核心部分,这种叙事性无疑将影响艺术家对视觉语言本身及“当代性”其他层面的探索和突破。一个典型的例子则是,在艺术家王兴伟以后现代的方式对绘画史资源(尤其是欧洲经典油画资源)进行置换时,他的作品本身却没有提出绘画史的问题。种种现象说明,中国当代艺术在引入各种西方理论丰富自身的同时,始终没有把自己放入一个连续的美术史范畴,这种尴尬的境遇阻碍了对当代性的深入思考。
不能不说,尽管中国当代艺术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正在失去效力的艺术工具并试图抛弃它,现实主义却如影随形地附着在当代艺术的每一次实验里。这种状况也必然存在于那些受里希特影响,广泛运用图像资源的艺术家身上。(7)
里希特的现实主义
格哈德里希特对中国的影响持续且深刻。从年龄上看,其影响涵盖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整整三代人,尤其集中于七十年代以来的青年艺术家群体,随着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深入,这种影响还将扩大;从身份来看,无论是擅长写实的体制内画家,还是偏重观念的当代艺术家,不管是学院派或非学院派,里希特都提供了一条通往当代艺术的捷径;从创作门类看,里希特的影响则为风景画、静物画、肖像画各种类型画种的创作打开新的局面。
把中国艺术家对里希特的运用放在现实主义的范畴里讨论,毫不过分。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以图像的观念来解释这种现象。但问题在于,在没有对图像,以及里希特如何运用图像的概念厘清的前提下,图像论依然会陷入以题材、内容为主导的宏大叙事模式,近年“庸俗社会学”的观点已经对此做出了批评。况且,这种庸俗化的论断背后本身就反映出“现实主义”思维的根深蒂固。
既然现实主义与中国当代艺术呈现一种既矛盾又共生的关系,我们如何面对绘画的现实主义传统?关于这一点,里希特对现实主义坚持的一面不无启发。里希特年轻时期成长于民主德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国家政党所奉行的文艺政策与中国“为工农兵服务”的论调十分相似。在学习期间,里希特接受的学院训练带有浓厚的苏联色彩,其文化课程设置集中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史、美学理论及政治经济学,学院传授的艺术路线则是混杂了欧洲古典主义、民粹派倾向的俄罗斯油画传统和马列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体系化的教学不可能不对他的艺术成长产生深刻影响。
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种影响视为消极的,或把里希特潜逃西德后对抽象绘画的选择全然视为叛逆行为,这都有失客观。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在里希特西逃后被保留下来,它让艺术家在面对西方崭新的当代艺术氛围时,保持了一种不即不离的距离。
1965年,里希特在创作《鲁迪叔叔》时,在技法和构图上开始体现出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回归,而这种新古典主义传统在艺术家此后的许多创作里得到延续,如《爱玛》(1966)、《贝蒂》(1988)、《阅读的女孩》(1994)、《与孩子在一起的S.》(1995)等。这些作品构图严整、稳定,笔法精致细腻,展现了里希特作为一名社会主义画家精湛的再现能力。本杰明布赫洛把其绘画中的现实主义情结视为国家现实主义、斯大林式现实主义同西德美术文化的一种调和,而不是放弃。(8)
对于里希特来说,早年纳粹德国和社会主义东德的经历使他在逃亡西德后抛弃了任何形式的乌托邦意识形态,却没有让他放弃现实主义的技法。具有乌托邦色彩、以具象绘画为载体的现实主义同附属于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经济、追求艺术自律原则的抽象主义被调和在一起,这种调和则体现在里希特“绘画作为摄影的一种方式”这一观念中。和别的观念艺术不同,里希特的观念并没有让绘画最终被解构,通过设置一个脆弱而悖论的关系,绘画反而得到了延续。
更具体地说,里希特对现实主义的运用并非简单停留在技法层面。相反,他针对现实主义的再现性问题提出一个极其悖论的观念。无论是肖像画还是风景画,它们都伪造了一个再现性场景,似乎绘画又回到了对自然的摹仿的古老传统中,不同寻常的是,里希特却通过绘画行为本身否定了这一种看法。
由于是以照片为原型,绘画再现自然的功能因此被抽离,而代之以图像的复制功能;由于绘画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一张照片,保持摄影图像本身的客观性也没有成为创作的目的。里希特目的仅仅是为了让绘画成为照片——他称之为“照相画”,此时,绘画摹仿的功能被摄影取代,从而,摄影完成了对绘画的一次否定。不过,画框本身赋予的含义使得照相画的绘画性因素始终存在,也使得里希特的创作始终被视为一种绘画行为。尽管运用图像,里希特却试图创作一幅没有内容的照片,这使得艺术家最终保持了绘画自身的纯粹性。然而,照片本身承载的内容却使得这种绘画的纯粹性不能纳入格林伯格式形式主义范畴中分析。(9) 通过设置这种吊诡的观念,里希特力图完成一次极富雄心的证明:即便完全抹除再现性功能,即便从形式主义自律的窠臼中走出来,绘画仍旧可以实现。
仍然是无边的现实主义
至今,仍然存在一个疑问,即里希特的绘画离开了阐释还能够生效吗?有不少人会非议,正因为里希特今天有人巨大声誉,所有阐释就如同锦上添花或画蛇添足,不过尔尔。本杰明布赫洛在其文章中明确提到里希特与现实主义的某种血肉关联,而正是此人,里希特曾亲口表明布赫洛政治学的阐释是荒谬的,但这并不影响布赫洛成为里希特一生中最重要的批评家和挚友。
里希特的绘画被放在观念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抽象主义等等框架中反复阐释,这正好说明了当代艺术依赖文本阐释的一面。这也是本文不愿意对里希特与现实主义进行过度阐释,或者摆出一副权威面孔的原因,究其根由,还是因为我畏惧那种陈腐酸败、执迷概念的学究气。里希特不存在一个原型,他存在于的是一种时刻发生的状态,这才符合当代艺术生生不息涌动的魅力。
在这一点上,中国艺术家、批评家们大可不必对里希特动辄冠以“大师”此类的威名。里希特的成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复制,他在柏林墙树立起来的最后时刻成功把握住自己的命运,潜逃西德;在冷战初期美国扶持欧洲艺术文化时,他也是享受补贴的一份子;而他亦没有错过德国六十年代艺术市场勃兴的历史机遇。对于所有成功的人来讲,共性就是在他们身上都能发现一个又一个让人熟悉的历史节点,而在每次历史震荡的当口,他们都幸运地站在了浪尖。里希特也不例外,抛开他的艺术,我们仍旧可以从不同角度来为他的人生作传。有了这个前提,我们才能正确地面对一个“去神化”的里希特,这也是中国当代艺术迫切需要的状态。
但“去神化”的里希特并不意味着一个“市场化”的里希特和一部庸俗成功学中的里希特。里希特作为一名艺术家,最大的成功还是在于他回归到自己真实的内心经验。他对现实主义的吸纳,除了在形式上有效地调和了现实主义与当代艺术之间的紧张关系,更体现在他的现实是立足在德国的历史反思中。我们没法想象,里希特在面对纳粹历史时会选择阳刚之气、充满青春情调的政治宣传图片,他继承的是桑德尔的肖像传统和本雅明的知识分子气质,即便是最为柔和的《海边一家》这样的作品,深究之下,也会了解到那个和蔼的父亲角色的人是杀人无数的党卫军恶魔。而对比不少中国艺术家,当他们在类同的方式中运用图像时,要么沉湎于自己青春的怀旧感伤,要么不出新意地做一些政治波普,这种差距实在不能以道里计。
而另一个重提现实主义与当代艺术的原因,则是出于对一种单一化思维的顾虑。里希特现象在中国的广为流行,作为积极的一面,它反映出艺术家对“图像”的巨大热情,这种热情无疑将有助于修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的“符号化”倾向。但不加反思的模仿,也造成了图像泛滥的趋势,似乎只要是图像的,艺术家就有了合法的当代性。以图像来阐释当代性,只能催生出庸俗化的图像观。而拘泥于题材与内容的审美观,无疑又是“现实主义”思维模式在艺术家心中根深蒂固的体现。可怕的不是题材与内容,可怕的是题材与内容的决定论思维。总而言之,里希特对中国,就如同一个拐杖,在不断摸索寻找自我的中国当代艺术这里,它提供了可靠的支撑,乃至是一份自信,但拐杖永远是拐杖,在前行的路上,需要的还是一副结实的年轻的身体,四肢健全,勇往直前。
(1) 德国德累斯顿国家艺术馆馆长马丁罗特回忆起参观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班的情景时,甚至惊讶,“那里有95%的作品看起来像格哈德里希特的风格。” 参见“总馆长马丁罗特谈北京‘格哈德里希特’和‘灵动的风景’艺术展”,克劳迪娅科特采访,崔涛涛译,中德文化网,2008年6月。
(2) 在这里,有必要对现实主义与写实稍作区分。有一种看法将现实主义分为观念及技法两个方面,并将写实纳入技法层面而对二者给予区分。事实上,现实主义和写实,当它们如实地描摹客观自然时,就已经包含了人类观察自然的态度,而不能仅仅认为写实是一种技法程式。现实主义概念无论多模糊,作为对自然的逼真模仿或客观再现,它依旧很容易与抽象主义或形式主义区分开来。瓦萨里在其《艺苑名人录》关于画家逼肖的写实技术的描写,仍然是今天现实主义的重要范例。现实主义的模糊,在于现实主义强调客观地展现自然世界,但事实上,即便对于同一件事物,不同现实主义者的解释却大不相同。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为自己首先预设了一些宏观的理论假设,如客观、写实、逼真等,但细究之下,这些假设本身就具备极大的不稳定性。
把现实主义的概念流变、不同派别的差异一一列举,这种本质性的探讨显然不在文章能力范围之内。本文的现实主义,限定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确定以来的现实主义状况,但文章不能仅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三十年尽管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思维影响深重,但明显不能划归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里希特的照相画(photo-painting),仅仅是运用写实的技法,而并没有涉及到现实主义的观念,因而不能放在讨论的范畴里。这种看法很值得讨论。
首先,里希特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民主德国生活过十余年,青年美术教育时期完全接受的是苏联式的现实主义教育,它不可能不对里希特后来的当代艺术创作产生影响。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里希特在潜逃西德初期,就学于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曾倾心于西方抽象表现主义,但在1960年代中期,却明显回归到写实的题材和技法上来,这其中不能不说没有现实主义的影响。
而且,如果仅仅以写实技法的运用来说明里希特,也存在悖谬。里希特的照相画在他自己的阐述中,是为了创造出一幅照片,也就是说,这里并不存在描摹客观自然的概念,他的照相画是纯然观念性的。
而这种观念,实则已经对现实主义(或写实)的客观性进行了一次揶揄和反讽。由此,当西方重要学者、批评家,如本杰明布赫洛,在阐述里希特的现实主义时,更多地把它视为对于国家现实主义、斯大林现实主义(也即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西德美术的一种调和。
(3)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地位,同时期在国统区,民族主义诉求下的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现实主义也成为主导。值得注意的是,如徐悲鸿、吴作人等画家早期受法国古典主义影响更多,但建国初期,伴随着美术领域大规模的意识形态改造和苏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引进,苏联体系不可能不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
(4) 现实主义绘画能否达到艺术自律?美国超级现实主义绘画,作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典范提供了肯定性的回答。批评界普遍倾向于从题材分析超级现实主义绘画,恰恰走入了与其初衷相悖的误区。艺术家们的创作几乎涉及所有传统题材,静物、风景、肖像等,历史画却不在此列,其原因正是基于历史画的叙事性、象征性背离了超级现实主义的原则。可以说,超级现实主义关注的是现实主义的错觉性,而非叙事性,这种观念是它为当代艺术打开的一个新维度。参加爱德华卢西-史密斯,《超级现实主义》,封一涵译,(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
(5) 参见栗宪庭,《艺术的民族当代主义》,《重要的不是艺术》,(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45至152页。
(6) 参见朱其,《态度与图像的实验:1990年代的前卫绘画》。作者对1990年代以来的种种绘画现象作出归纳,试图提出一种成熟的前卫绘画探索正在此时形成,而这种前卫性体现为(一)绘画的文化姿态和自我反省深度,(二)绘画在图像模式、视觉观念以及叙事性、绘画性方面的实验。
(7) 可以说,里希特在中国的流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这种现实主义传统。当艺术家试图寻找一种温和的方式来传达自己对集体主义和历史的记忆时,里希特模糊和冷漠的风格恰好为这种情感提供了绝佳的表达方式,而里希特在当代艺术圈的崇高声望,则似乎为这种风格预设了“当代性”的合法效力。不过事实证明,在中国特定的当代艺术语境里,这种摹仿不具备必然的“当代性”基础。
(9) 参见彼得奥斯本,《绘画的否定:里希特的否定》,蒲鸿译,《艺术时代》,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