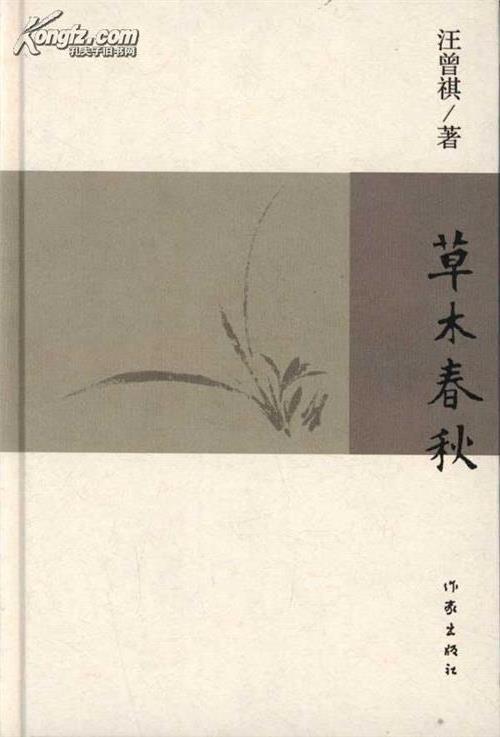沈宏非川菜 沈宏非谈苏州菜:一个上海人的体会
与苏州城里的大部份风物相比,变化最小的,大概就只有苏州话和苏州菜这两项口头文化遗产了。 比如,元旦你要大闸蟹,春节你要刀鱼,清明你寻白鱼,“五.一”你点鲃鱼,“十.一” 你问鳜鱼──无论是在苏州的饭店还是菜场,这些要求都将无一例外地遭到白眼。
念你是游客,也就罢了,如果是苏州本地人,说不定会在电光火石之间即被鉴定为脑残,或直接押送精神病院。 又看在现如比食客的贪婪更发达的养殖业的份上,鱼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你认为猪肉比较保险──没听说杀猪也有季节性的──而在冬天想吃樱桃肉,夏天要吃蜜汁火方,春天点一份荷叶粉蒸肉,在任何一家对自家老品牌尚存有几分荣誉感的饭馆里,遭到当面或者背地的鄙视,都是一样没商量的。
一碗面、只是一碗汤面,甚至不要爆鳝、卤鸭以及焖肉之类的任何浇头,总不会有自取其辱之虞了吧? 也不完全对。既是汤面,则面汤有白汤和红汤之分,分别代表着春夏和秋冬这两大不同的系列。如果你乱点红白,照样会蒙受违法“乱季”之冤屈。
就连鲜肉月饼,苏州人也坚持只在中秋前后发售,不像上海那样,一年四季年中无休。当然,也比上海好吃得多。至于甲鱼,苏州人只吃春节的“菜花甲鱼”,过了春天的甲鱼,即成“蚊子甲鱼”,也不是不能吃,但最好关起门来偷吃,千万别让熟人撞破。
应时则贵,失时则贱。 以上这些,还是按季或按月分的普及版,从前,在讲究的苏州饭馆,凡是离土的蔬菜,只要一隔夜,就只能喂鸡了。 莼鲈之思 “不食,不时”虽是孔子的教诲,但真正领会贯彻并且落实到行动上的却是苏州人。
苏州人车前子这样写道:“苏帮菜是极其讲究时令的,春雨绵绵,吃“碧螺虾仁”;夏木阴阴,吃“响油鳝糊”;秋风阵阵,吃“雪花蟹斗”;冬雪皑皑,吃……我就在自己家窗口喝一壶热乎乎黄酒,不出门了。
” 明清时代,苏州人吃的大部份新鲜食材,已达到“率五日而更一品”的水准(见明代王鏊<<姑苏志>>)。产品更新换季的速度和节奏,比Zara和H&M还要迅速。
再往前,1700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在离家三千里外的洛阳当西晋大司马的苏州吴江人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苑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适忘,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
” 以思念季节性的食材做为唯一辞职理由并且获得批准,古往今来,并不只张翰一人,准确地说,是两人,第二个,也是苏州人。陆文夫生前说:“七年前,我有一位朋友千方百计地从北京调回来,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是为了回苏州来吃苏州的青菜。
这位朋友不是因莼鲈之思而归故里,竟然是为了吃青菜而回来的,虽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也可见苏州人对新鲜食物是嗜之若命的。头刀韭菜、青蚕豆、鲜笋、菜花甲鱼、太湖莼菜、南塘鸡头米、马兰头••••••四时八节都有时菜,如果有哪种菜没吃上,那老太太或老先生便要叹息,好象今年的日子过得有点不舒畅,总是像缺了点什么东西似的。
” 移步换景 所谓“莼鲈之思”,可能是政治策略,但最初做为一种礼仪的“不时,不食”,的确已被苏州人内化为一种共同的生活美学。
如果说食物是人,季节是景,则苏式饮食美学就和苏州园林一样,都是移步换景,一步一景的。 据清代<<桐桥倚棹录>>记载,当年,苏州虎丘七里山塘,酒楼菜馆不下百户。
“每岁清明前始开炉安锅,碧槛红阑,华灯璀灿。”但“过十月朝节,席冷樽寒,围炉乏侣,青望乃收矣。是以昔人有‘佳节待过十月朝,山塘寂静渐无聊’”之句”。
因此,如果指名道姓地要来苏州找某种好吃的,除查好好航班和车次之外,务必得挑对时候。 以鱼为米 苏州人的“不时,不食”,实在是被苏州的天时地利给娇纵出来的。
水乡的体系,春秋时代就已形成,远近环抱姑苏的太湖、阳澄湖、石湖、独墅湖和黄天荡以及各种被称为“荡”的湿地,无不鹜飞鱼跃,蟹肥虾美,四时鱼鲜,八节水产,一一应时而出,终年迭替不绝。水里不只有鱼虾蟹,更有“水八仙”(即水生作物如茭白、莲藕、南芡、茨菇、荸荠、水芹、红菱、莼菜) 一年中轮流上桌,以供四时尝鲜。
而附郭诸山之上,则菇、菘、蕈、笋等美味应时迭出,终年不断。所谓“鱼米之乡”,不是鱼和米,而是以鱼为米。
赵筠<<吴门竹枝词>>云:“山中鲜果海中鳞,落索瓜茄次第陈,佳品尽为吴地有,一年四季买时新。”现在,以上“佳品”虽不尽为吴地所有,但长三角。“地富鱼为米”,苏州滨湖近海,水清土饶,苏帮佳肴最早以水产和鲜蔬著名。
交通自古便利,“水浮陆移,无所不至”。隋开运河后,更是帆樯如林,商贾幷辏,食货丛集,“中家壮子,无不商贩以游者”,终于成为我国东南最大的商业都会。入清号称“天下四聚”之一。
苏州自古“擅三江五湖之利”。三江即入,“底定”的不仅是三万六千顷的太湖,也包括了苏州人在时序上的固执和坚守。 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 只要应时,廊下盐齑即成珍品;吃对时令,乌鸦也能变凤凰,就像叶放所说的那样:“(这些东西)让人相思了整整一年才见面,吃到了嘴里,哪有不激动的道理?” 苏州菜的精致,与传统民风有关。
历史上,苏州民俗一向“多奢少俭”(宋.范成大<<吴郡志>>);“以讲求饮食闻于时,凡中流以上之人家,正餐小食无不力求精美”(清.
徐珂<<清稗类钞>>)。“寻常过从,大小方圆之器,俭者率半百”(明.周履靖<<易牙遗意序>>)。
“奢”既体现在对时序的坚持,也体现在烹饪手段上。那些应时而出的平常之物,一经苏州厨子之手,立马改头换面,出落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正如沈三白在<<浮生六记>>中夸奖芸娘的那样:“善不费之庖,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
小说家陆文夫也认为:“苏州家常菜都比较简朴,可是简朴的幷不马虎;经济实惠,精心制作,这就是苏州人的特点”。 完全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真实需要 除了家常的“芸手”,现在我们在饭馆里吃到的那些代表性的苏州菜,很多都出自从前当地“缙绅之家”的私厨,更是精益求精。
后者的 “食不厌精”,实在令人发指。苏州女作家朱文颖说:“在苏式的精致里,有些已经完全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真实需要。
”这种脱离了日常生活的真实需要的菜肴,已近失传的蟹粉菜中之极品“秃黄油”应算一道。 苏州方言,“秃”即“只有”或“独有”之意;“黄油”者,高纯度之蟹粉也,不同于包含蟹肉的蟹粉,即出蟹后只取蟹膏蟹黄,用葱、姜及熟肥膘末爆香,再以黄酒闷透,加高汤调味,复淋猪油,洒胡椒粉而成。
如何消受此“黄油盈溢,金脂香软”之尤物?唯捞饭一道也。 比“秃黄油”更为歇斯底里的,是豆芽塞肉:在纤细的绿豆芽里藏进更细的鸡丝或南腿丝,是一个需要用到绣花针的工作。
“镂豆芽菜使空,以鸡丝、火腿满塞之,嘉庆时最盛行。”(<<清稗类钞>>)。
此物仅见于晚清文献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电视剧(前几年,香港人拍过一套<<满汉全席>>,讲的是苏州名厨张东官进宫给乾隆做菜的故事,戏里就曾出现过这道菜。我问扮演张东官的徐峥拍戏时是怎么弄的,他说帮帮忙,电视剧都是低成本制作,那么丧心病狂的东西,哪里做的出来?不过就是随便交代了一下。
在饭馆里仍能吃到的“丧心病狂”之物也不是没有,比如“三虾豆腐”:小暑过后,先对一只青壳虾动一次精细外科手术,将虾脑、虾仁和虾子分别取出,分开三部分,加高汤,笋丁和猪腿肉以猪油热炒而成,虾壳也不浪费,煮汤的干活。
这道菜最考苏帮火工技艺。豆腐经过特别加工,在点盐卤的时候嫩老程度要把握得精准,烧时才不失形,但是吃口又极为细嫩。
早期的豆腐,为灵岩山僧人所制,其自净、细嫩与众不同,配上三虾,色、味俱佳,堪称餐盘中的双面绣。 如果说扬州菜是盐商的通行证,苏州菜就是书香门第和仕宦之家的墓志铭。 浓不鞔胃,淡不槁舌 听苏州人吵架,吃苏州菜,一个外地人会获得相近的感受。
“浓不鞔胃,淡不槁舌”(<<易牙遗意序>>)。这一苏州菜的口感标准,同样适用于苏州人吵架时的“口感”和旁观者的听觉即不像川菜那么“猛”,又没有粤菜那么“生”。
浓郁止于“浓到化得开”,清淡又不至于淡出鸟来。孔子的中庸哲学体现到口感上,就是苏帮菜的这种完整和圆满──说到完整和圆满,苏帮菜的最后一个技术标准“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无疑在“形而下”起到了的关键作用,代表作见“母油船鸭”(又名“母油整鸭”)或“松鼠鳜鱼”。
但是苏州菜的甜,对于外地人来说,绝对也算是一种刺激。苏州菜为什么甜?多方对此聚讼不休,苏州人自己也莫衷一是。
有人说此乃历史上受到“重甜”的宋代中原士族南下的影响,也有人觉得其实苏州菜并不甜,甜的只有那几道,偏偏那几道名气太大,游客又爱,遂有“苏帮菜等于甜”之误。事实上,苏州菜里的甜味集中在红烧及糖醋部份,糖的加入,目的无非是为了厚其味,润其色。
咸甜味型的,必须保持“甜出头,咸收口”,如“樱桃肉”;糖醋类的,酸甜必须保持绝对的平衡,任何一方都不可“出头”,比如“松鼠鳜鱼”。 像喝葡萄酒那样吃苏州菜 不过,我个人倾向于采信“石家饭店”毕师傅的解释,即苏帮菜里许多名菜都出自“堂子菜”,又名“书寓菜”。
这些红尘中一二等风流富贵之地,酒菜一向精益求精,客人又多因吸食鸦片而导致味觉迟钝,堂子里的私厨于是在口味上加重刺激来讨好。
或问:抽大烟不独苏州,旧中国烟馆堂子之盛,一如今日之网吧,何以京、沪等地的堂子菜就不甜?我想到的可能性是,京、沪本身口味偏重,要迎合烟客,再加重就是。
苏帮菜本来清淡,于是剑走偏锋,向甜的方向突围。 对于一道经典的苏州菜来说,“甜”,“软”,“糯”这三个字缺一不可,整合在嘴里就是一个“酥”字,苏州原本是“酥州”。我的建议是,一箸苏州菜入口之前,如果你能把自己的味觉期待和口感分析调整到喝葡萄酒的状态,就不至于被“甜”所淹没,事实上,苏州菜里经常用到的红曲之类,往往甜得虚无飘渺而且变化多端,如果不用心捕捉并耐心“审问”,转瞬间便逃之夭夭,一顿饭吃下来除了一“甜”到底,投箸四顾茫然,不知所云。
理想的“甜蜜蜜”,带来的应该是“在哪里见过你>你的笑容一时想不起”式的荡气回肠和畅然若失,而绝非“是腻,是腻,梦见的就是腻!” 说到底,糖以及糖份在菜肴里的多寡,是权力与富足的象征。
同为川菜,但盆地的成都菜却比山地的重庆菜更加油腻,也是同样的道理。味觉上的遗传基因很难发生突变,不管你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 苏州“最好的饭店”? 1972年,安东尼奥尼在苏州拍摄了一家名叫“复兴回民面店”的小吃店,旁白说“这是整个城市里最好的一家饭店”。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中国>>,也看到了在“复兴回民面店”里吃面条和生煎苏州人。
安东尼奥尼在旁白里还发表感想说,面条的品种之少,很难令人相信意大利面条尤其是fettucine乃是传自中国。 1974年2月,我在学校里参加学习了<<人民日报>>的一系列大批判,苏州市回民面店职工欧阳娟娟在第4版题为<<卑劣手法必须揭穿>>的檄文(也是我撰写“批安”大字报的范文之一)中愤怒地揭发道:“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为了拍摄反华影片<<中国>>,曾经别有用心地闯进我们苏州回民面店,采用卑劣的手法,拍了很多镜头,还在电影的解说词中说什么‘这是苏州最好的一家饭店’。
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和恶意攻击,必须予以彻底揭露…这是故意说瞎话。
我们店的店面小,设备简单,服务员只有十一人,是一家小型面店。在我们苏州饮食行业中,每天接待两三千人的大饭店就有松鹤楼、新聚丰等好几家,在我们面店附近,比我们店规模大得多的面店、饭店也不下三、四家,象我们这样的小面店到处都有,怎么能说成是全市‘最好的饭店’呢?这难道是由于安东尼奥尼无知,把‘面店’说成‘饭店’了吗?不!
这是他蓄意歪曲事实,妄图给人造成我国城市落后、商业萧条的假像,达到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
这就充分暴露了他这个反华小丑的真面目。” 大约在1965-1978年间,我每年都要被我爸带到苏州去看他爸,1972年那次,好像还住了整整一个暑假,所以,这件事我是有发言权的,至少,安东尼奥尼在苏州犯下的错误的确是咎由自取。
70年代,苏州“最好的饭店”又何止欧阳娟娟提到的松鹤楼和新聚丰!不过,同样道理,如果你今天也带着摄影机和一张不在乎的嘴巴来到苏州,看到满大街的麻辣烫和小龙虾,甚至在酒店前台摆放的美食手册里看到KFC,并且不得不相信这就是苏州美食的主流,可能就会犯和安东尼奥尼一样的错误。
老字号都变味了 曾经在松鹤楼工作并长期主管苏州商业的现任苏州市烹饪协会会长华永根感叹道:“老字号都变味了”。
“苏州菜为什么不好吃了?因为外地人越来越多了,连很多厨师都是外地人。传统苏州菜既无野味也无海鲜,以河/湖鲜和当时得令的新鲜果蔬为主。
苏州物产丰富,苏帮菜的厨师,最讲究用时令的鲜货,将菜本身的滋味用合宜的方法呈现。传统苏州菜讲究温文尔雅,吃东西很细,要吃菜的本味。一碗简简单单的阳春面,汤水肯定要好的!新苏州人没有吃过好的苏帮菜,吃到的都是异化简化的。
苏州菜必须要在精致的态度下完成,做出来不会便宜,也不可能匆忙急就。现在的环境怎么可能?”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老字号当年成就其“味”的诸多因素,似乎也正是如今“变味”的原因。
大约半世纪前,“鸳鸯蝴蝶派”鼻祖(也是老资格的美食家)苏州人包天笑先生以黄蘖禅师“老僧到此休饶食,后事还须问后人”结束了<<衣食住行的百年变迁>>。时至今日,这仍旧是对苏州菜的过去现在未来所能做出的最恰当也是最无耐的断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