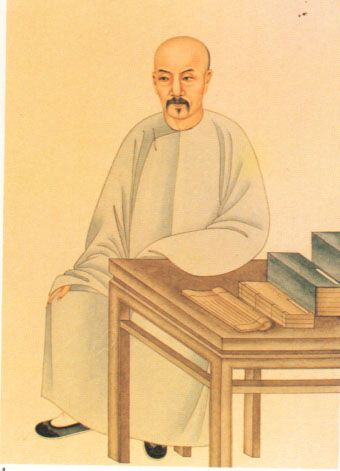金观涛的孩子 金观涛 刘青峰:试论中国式的自由主义──胡适实验主义和戴震哲学的比较
本文为我们接受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资助的研究课题“中国近代自由主义起源与发展之观念史研究──从乾嘉到五四”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在此说明并致谢。
不可否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近20年来最常用的政治术语,其语境是突出中国与西方或苏联东欧式社会主义的区别。我们这篇谈中国自由主义的文章,也冠以“中国式”这一时髦用语,目的则在于分析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的差别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的内在关联。二十世纪中国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者是胡适,而他最感兴趣的中国传统思想家是戴震,我们通过比较他们的哲学和思想方法,探讨中国式自由主义及其起源。
一 从胡适为甚么特别对戴震感兴趣谈起
众所周知,身为知识份子的胡适,一直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自由主义来自杜威(John Dewey)实验主义,而他提出的著名口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更被视为代表其自由主义精神的科学方法。作为学者的胡适,则以提出中国哲学史新框架而奠定他在学术界的地位。
但是,胡适穷其一生努力并没有完成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的撰述。他这方面最重要的着作应是《戴东原的哲学》。根据胡适的日记,他是在1922年3月从刘叔雅那里借来《孟子字义疏证》,途中到一家小饭馆吃饭,把书看了一卷,立即感到此书的厉害1。
1923年底,他即开始撰述《戴东原的哲学》。从此,他后半生的所有学术研究,几乎完全集中在戴震哲学及考证《水经注》方面。
胡适一生并没有留下大部头的学术着作,唯有一百多万字的《水经注》考证是例外。为了推翻历来有关戴校《水经注》乃剽窃赵一清的说法,无论是抗战时期他在美国繁忙的外交事务中,还是在山河变色国共交战之际,他从未忘记过收集《水经注》的版本。
为戴震洗冤,成为胡适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目标。正如周昌龙说,这项考证之所以重要,是胡适力图推翻程朱理学的信徒对戴震的攻击,从戴震学术品质(心术)之高尚来证明其学术之正确2,更显示戴震的新义理学是在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它上接程朱格物穷理之说,旁通西方实验主义哲学,是中国“科学时代的新哲学”之原型母体3。胡适有意无意地视戴震哲学为自己奉行的实验主义的中国源头。
胡适对戴震近于偏执狂的推崇与扞卫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认为,这一事实在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在于:它有助我们分析胡适自由主义的内在结构。如果我们用胡适思想作为五四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典范,而正如胡适所说,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是杜威实验主义的发挥,但另一方面他又把自己的哲学追溯到戴震那里,那么这立即会产生一个疑难:中国十八世纪传统思想家戴震的道德哲学,怎么可能与另一个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在胡适的思想体系中关联起来呢?近几十年来,学术界早已注意到胡适实验主义主张与杜威实验主义的巨大差异,但胡适实验主义的理念形态至今尚没有得到透彻研究,它与戴震哲学的比较也因学科分界而长期被忽略。
我们认为,胡适之所以推崇戴震,正是因为他所认同的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与戴震哲学具有同构性;胡适对戴震哲学同情的了解和共鸣,使得扞卫戴震成为他毕生的学术事业。上述现象,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中国现代思想形成过程中,有哪些我们未曾意识到的传统思想因素,参与了五四知识份子对西方自由主义的吸收和塑造呢?本文力图通过胡适实验主义与戴震哲学的比较研究来揭示这种联系。
我们的讨论分为三个步骤:首先,要弄清楚戴震哲学的方法究竟是甚么?其次,分析胡适所理解的实验主义的理念型态,再考察它与杜威实验主义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比较胡适和戴震的哲学方法,以揭示二者的同构性。
这种比较或许有助于解决另一个难题,这就是中国知识份子接受西方自由主义时,他们本身根深柢固的思想方法是如何参与对外来观念再塑造的。换言之,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与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近代传统到底存在着甚么联系?
二 戴震的“以理杀人”和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
对于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来说,戴震之所以值得重视,因为他是在历史上第一个指出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人,这是五四时代反礼教的利器。章太炎早就指出,戴震是对他生活的时代有感而发。戴震生活在雍正、乾隆时期,雍正最爱做并做得最振振有词的事,就是“以理杀人”。
从思想史内部来看,戴震哲学的出现,与明末以来儒学内部出现肯定人的情感和欲望合理的思潮直接有关。余英时曾指出,自明末以来,不少儒者肯定个人欲望和“私”的合理性,甚至出现新的公私观4。
沟口雄三认为,这股思潮表现为:“一是肯定欲望的言论开始表面化。二是『私』得到肯定性的主张。”5换言之,戴震哲学是对儒学内部出现“天理”和“人欲”之间紧张关系的一种回应。当个人欲望、私人利益和情感被认为是天然合理时,它必然跟普遍的伦理规范发生冲突。
人们用客观的普遍之理来限制扼杀合理欲望(感情),就会出现戴震所说的“以理杀人”。戴震既然肯定人的欲望和情感具有最终合理性,但又不能摒弃儒家伦理,那么他又如何能够克服“以理杀人”这一困境呢?张寿安的研究发现,戴震的哲学建立在三个要点之上:即“以道德践履言性善”;道德的根据是人的自然感情欲望;“理”是事物显现的条理;它是一种与宋明理学不同类型的新道德哲学6。
在儒学中,道德实践、感情欲望、事物质料这三个观念统统可以用“气”来概括,故戴震的道德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气”的一元论;道德规范(理)被视为“气”在生生不息过程中显现出来的条理。正如郑宗义所说7:
大抵东原意谓的天道犹如现今自然科学探索背后所必须预设的运动观念;而条理犹如本于此运动观念探究所得的物理。
因此,我们也可以把气在运行中显现出最普遍之条理称之为共相、规律等。
一旦“理”被视为气化流行中彰显的条理和规律,那么,紧接着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真的存在作为共性和规律的客观之“理”?答案只可能有两种:一是主张“理在气中”(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但它同时也是真实客观的存在,明末清初王船山、黄宗羲的气论正是持这种立场。
如果持这种观点,仍然不能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当真实而普遍的规范与合理的个人欲望所对应的具体情景之理互相冲突时,怎样才能作出正确抉择?这种情况下,为了要避免以理杀人,唯有采取第二种立场,即只视个体为真实存在,共性只不过是“名”而已。这正是戴震哲学的核心所在。
戴震反对程朱理学,正是针对其把“理”看作一种如同物体那样客观存在的基本主张。他指出:宋儒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8之论,不过是来自佛老。那么,对戴震而言,“理”不是物,又是甚么?他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卷首,是这样定义“理”的9: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戴震十分清楚地把理学中抽象的、客观存在的理,看作不过是人在进行主体智力活动(如“区别”、“观察”)时不得不借用的“名”而已。这样,在戴震的哲学系统中,一方面万物都是“气”,“气”(宇宙)的生生不息使任何真实的事物都是可感的、具体的;另一方面,“理”只是“气”在运行中表现出来的条理,任何“理”都离不开具体事物、离不开个人所处的情境。
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抽象的客观的“理”。我们知道,戴震正是企图凭藉这种“唯有个体才是真实可靠”的逻辑,来解决在儒学内部如何避免“以理杀人”这一难题。
为甚么说只要否定普遍的“理”具有客观性,就可以避免“以理杀人”呢?戴震是这样分析宋明儒学“以理杀人”逻辑的:理学把伦常等级视为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它可以独立于具体情境、案例、个人感情而成为一般道德原则,那么用这种“理”来判别是非时,就有可能出现“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
虽失,谓之顺”;而“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10。反之,如果否定抽象普遍原则,把普遍之理只看作是从某种事物中归纳出的“名称”,而对任何真正存在的理,都必须放到具体的考虑、个人感情欲望的情景中,才能判别它是否适当。
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从具体案例来抽取理,它离不开对个别问题情境的具体分析。只要将伦理道德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理”就不再会与正当的“欲”发生矛盾了。
戴震熟谙儒家经典,他是用考证方法来证明自己对“理”的解说更符合儒家原典的。他发现“六经、孔、孟之言以及传记群籍,『理』字不多见”11,故:“六经、孔、孟之书不闻理气之辨,而后儒创言之”12。这些后儒正是他批驳的宋儒。
他认为宋儒创立的理学有两大谬误:一是认同普遍之理,即“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二是将理看作如同物那样的客观实在,即“视之『如有物焉』,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13。宋儒这种“尊理为超乎阴阳气化”14,不是继承孔孟,反而是师承了其对立面的老庄,即“盖有老、庄、释氏之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道,遂转之以言夫理”,显然,“六经孔孟之言无与之合也”15。
破除了普遍之理的抽象性、客观性及儒学正统承续性之后,戴震继而还理以常识性和具体性。他说:“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16。除了我们上面已引用过的,戴震认为“理”只存在于个别具体事物中以外,他还特别强调“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17。
每个人只要“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18,即普遍之理只能通过一个个具体之理归纳得到,据此推出的普遍之理就再也不会陷于“以理杀人”的困境。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是非公正的尺,“心之所同然始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非理也,非义也”19,这样,“以我絜之人,则理明”20。
必须注意,戴震这些对理的定义,都是为了否认“理”的绝对性,排除“理”是可以脱离具体一事一人一境而客观存在的观念。
正因为“理”必须诉诸一事一人一境的具体分析,这样戴震在维护儒家伦理正当性的同时,也就为幼者、贱者、卑者与不合理之“天理”争夺“理”的发言权。
为了验证否定抽象普遍之理的客观存在是不是可以看作戴震哲学的基础,我们粗略统计了《孟子字义疏证》中“理”字的用法,在这本不长的着作中,“理”字大约出现了180多次。其中,大约有近一半是在批驳程朱理学时用的,另一半则是阐释他自己对“理”的看法。
据我们的考察,在这一半中“理”的意义又大致可以分为五类,它们分别为“区分”、“具体事物的条理”、“心情境遇”、“智”以及表达具体感情活动是否“适当、中正”等。值得注意的是,戴震使用“理”字时的这五类意义,统统是具体的、不能独立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
在程朱理学当道的时代,戴震的理论太离谱、太具有颠覆性。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西方唯名论革命(Nominalist Revolution)。今天,已有西方思想史学者将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的唯名论视为现代性的神学起源。
这是因为唯名论认为一切共相(普遍的类和由类组成等级秩序)只是名称,而非真实存在,最终颠覆了中世纪亚里士多德神学的宇宙观。唯名论为西方人带来了空前的焦虑,日后成为新教伦理和个人主义的温床21。
显然,在乾隆时代,戴震这种离经叛道的方法论革命,很难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同。戴震生前大受攻击,郁郁而终。但一百多年之后,当中国文化在西潮冲击下被迫现代转型之际,戴震的思想就将会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