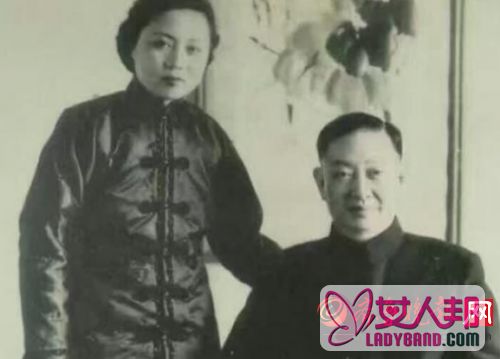叶少兰夫人 叶盛兰叶少兰父子:两代京剧大师的人生际遇
那时候演戏,开场的戏灯光开得不太亮,以后是上一个好角儿加一道光,再上一个好角儿再加一道光,到梅大师上的时候,灯光“啪”的一下就全亮了。所以小时候就是想做一个好演员,做灯光开得最亮的演员,做一个唱大轴的领衔主演,有前途的演员。
——叶少兰《岁月——叶少兰从艺六十年之感悟 1950-2010》
叶金泰生下来一百天就跟着父亲跑码头了。父亲是京剧小生叶盛兰,他后来成为京剧小生叶少兰。
叶金泰上学的时候改了一个跟得上新时代的名字叫叶强,1962年戏校毕业正式改名叶少兰。“文革”破四旧,连姜妙香先生都宣布改名“姜永革”了,叶少兰改回叶强。“文革”好歹结束了,叶强回归舞台,再次改名叶少兰,从此名满天下。
叶少兰从七岁开始学小生,但是在满师出科的时候碰到了大麻烦。一来他的变声期比较长,受嗓音所限只能改学导演;更糟糕的是,大致上从1964年现代戏会演起,京剧就慢慢往样板戏演变了。
京剧一变成样板戏,就没小生行什么事了。那会儿,英俊小生都同时必须膀壮腰圆,武生出身的李玉和就是标准形象,而风流倜傥是和革命互不兼容的,小生于是成了行当之外的行当。从同光十三绝的徐小香开始的京剧小生风流史,从南戏滥觞的戏曲小生风流史,被“文革”腰斩车裂,雨打风吹去。
当时的几位京昆小生艺术的代表人物——姜六爷妙香战兢兢如惊弓之鸟,俞五爷振飞栖遑遑似漏网之鱼,“摘帽右派”叶四爷盛兰身心俱疲,连基本的医疗都得不到保障,遑论练功课徒、教子成名。
于是,叶少兰本应在氍毹上挥洒的汗水都流到沙岭子农场的稻田里了——因为无霜期特别短,必须冒着料峭的春寒插秧,及至开镰收割,又得踩着冰碴子下地:“‘两层冰,一层水,中间夹着热大腿’,……上身穿着棉袄,俩腿泡在冰水里。
插秧时,往往要用脚先把冰泥踩软,再插秧苗;到收割时,由于放不掉水,稻子就湿漉漉的,你镰刀磨得飞快,照样割不下几根,只能硬揪。天气冷,上下牙冻得嘚嘚作响,嘴唇冻紫,五指冻得合不拢,手脚全冻僵了。
”三年下来,武小生扳朝天蹬的腿生生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后来一到上台做繁难动作必须咬牙硬挺。先从老一辈那儿断了京剧小生的流脉,再驱逐传人劳其筋骨行弗乱其所为,京剧小生行就这样被彻底地“革命”和专政了。
伴随着“革命样板戏”的豪迈旋律在神州大地的角角落落奏响,多少流派创始人被凌辱和迫害,多少流派传人被迫抛掷流年、断送青春。京剧的血脉就此被割断。嗣后虽经拨乱反正,百花重放,却已是盛年不再来,盛兰不再开了。
我第一次知道叶少兰的名字是在1983年。那时,叶强已经结束了不堪回首的“劳改”生涯(叶下放的农场原先是个劳改农场),回到舞台,并正式改名叶少兰了。
那年我十一岁,既不会唱歌,也不会唱戏。我被音乐老师判定为“音盲”,就是那种怎么唱歌都跑调的人。但是,那时候叶少兰带着几出大戏来到上海,电视里放的《周仁献嫂》让我震惊并且痴迷了,我开始看京剧。
《周仁献嫂》讲的是舍生取义的故事,周仁妻为救义兄之妻杜娘子代嫁严府,杀贼未成自尽身亡,周仁埋葬了妻子,顶着卖友求荣的恶名盼到了义兄杜文学沉冤昭雪的一天,却被当堂毒打,险些丧命。
传统的京剧里,《刺汤》、《刺虎》、《青霜剑》等剧也有为复仇假意允婚、洞房行刺乃至杀身成仁的情节,但是《周仁献嫂》更激情四溢,更感天动地。叶少兰在乃父遗作的基础上整合关目,疏通情节,请原作者翁偶虹老又专门增写了“西皮调底”和“反二黄”两个繁难的唱段。
由是,从遭遇胁迫的惶恐万状、夫妻诀别的痛苦不堪、吃“喜酒”洞房惊变、葬妻归来迷离恍惚,直至沉冤昭雪扬眉吐气……大起大伏的故事,大悲大喜的情绪,换来至真至美的艺术效果。
诚然,京剧是写意的艺术,它要求疏离,安详,甚至启发了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学说。但是,京剧从来都不排斥真诚的表演和由真诚表演带来的美感。叶少兰整理的《周仁献嫂》就是这样一部杰作,剧中不仅能听到动听的唱腔,还能看到各种步法和技巧的展示:跪步、搓步、甩发、抢背、僵尸,不一而足,非四功五法俱备的全才小生不能演出。
特别是新创的“反二黄”:“迷惘惘葬埋了我的妻,悲切切一路行来不敢啼……”周仁葬的是自己的妻子,世人却以为他逼死了嫂夫人,虽然是内心独白,却依然怕人听到,一个“妻”字唱得深情、哀婉、欲诉还休,到“悲切切”的“悲”字,声音已经在颤抖,所以,唱出来是“悲、悲切切……”,叠字和情绪天衣无缝,浑然天成;到“昏暗暗问天天不语,黑、黑、黑沉沉问地,地也无言空唏嘘”,已是天愁地惨,神人共哀了。
那正是在1983年,叶少兰完美地演出此剧,一举征服上海滩。我呢,正在小升初考试的无聊岁月里疯玩,一次次守着电视机看这出戏的重播,看得两眼放光,欲罢不能。多少年过去了,上海电视台这场《周仁献嫂》的录像早就无处寻觅,但是那些影像和声音已刻录在我的脑海里,一闭眼就能见到。
后来听说,叶少兰曾经说,给小孩演出也不能懈怠,因为小孩的头脑是一张白纸,让他们对京剧有一个良好的印象,京剧才有希望。这时,我不由回想起自己十一岁的时候在自家阁楼上,对着那台九英寸的黑白小电视,竖起耳朵给《周仁献嫂》的每个场次数掌声的情景。
“黑夜里闷坏了罗士信,西北风吹得我透甲寒……”苍凉凄怆的唢呐二黄,走投无路的绝叫,这是《罗成叫关》,叶盛兰不世的杰作。我总觉得叶盛兰在无端被扣上“右派”帽子时心里会有同样欲说难诉的大悲大恸。
不同的是,舞台上的罗成能把这一腔愤懑喊出来,让观众和他分担;批斗台上的叶盛兰却只能唯唯诺诺而已。但是,在平静的外表之下,心里又会是怎样的翻江倒海呢?章诒和曾经在《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这篇文章里复述了一个细节。
那是一个和英气逼人的周瑜、潇洒儒雅的梁山伯、风流倜傥的张君瑞……这些艺术形象都判若两人的叶盛兰。她说,“叶盛兰每次从批斗会上回到家里,什么话也不说,就把自己关进卧室。
继而,就听见他在里面跟喊嗓子一样,用小生念白的声音大喊:‘我是谁?’‘谁敢惹我?’……抑扬顿挫,且一声高过一声。……叶盛兰喊够了,自己开门出来,也恢复了常态。全家和和气气地吃饭。”这段描述让我联想起很多友人不约而同地描述过的路翎在被关押期间和平反释放后的漫长岁月中不间断、不自主的怒吼和哀嚎。莫道英雄气短,实是世事堪哀。
我生也晚,听戏从少兰始,没赶上听四爷唱戏,只能从旁人的回忆中构拟1958年叶四爷在上海演出《罗成》的盛景。受章伯钧牵连,叶盛兰被中国京剧院划为“右派”,但因为他是小生的“独一份”,台上离了他不行,所以又让“戴罪立功”,要求四爷随团演出,但是,不能贴海报,不能写水牌,不能谢幕,演出前要一趟一趟跑老虎灶泡开水,演出后要挽起衣袖打扫剧场。
那天,原定演出《罗成》,但是不能贴叶盛兰演《罗成》的海报,所以先贴了李少春《野猪林》(一说《响马传》)的海报,演出前两小时贴出告示,称演员生病(一说演员真的生病了),临时换戏。
于是,一个窗口退票,另一个窗口卖票。即便如此,也抵挡不住上海的观众奔走相告的热情,很快《罗成》连站票也买不到了。
从很早的时候起,不管什么角儿,必须在上海被认可了,才能算唱红了。上海的观众很挑角儿,轻易不会认可,一旦认可,则不吝惜最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罗成》首演于1946年,是育化社的打炮戏,育化社首演成功不久就风靡上海滩。
但是,这一次,叶盛兰满怀着寄人篱下的屈辱和前途无望的迷惘,演一个黑夜里、黑煞日满腹冤屈无处诉的勇将罗成,以这样的心理体验完成一次因扭曲而更臻完美的舞台展示,上海观众疯狂了。
我的朋友方薏清阿姨是一位资深叶迷,她这样追述两年后在北京看叶盛兰演《罗成》的情形:“《叫关》一场,叶先生一条嗓子盖过唢呐,音高而远,在剧场回荡,那种悲壮的气氛油然而生。……《淤泥河》一场,在身中敌箭后,把箭拔下,用宝剑自刎,在长长的撕边锣鼓声中,把眼珠一直翻上去只见眼白,观众掌声四起,宝剑缓缓扔下,最后一个漂亮的僵尸。
”把这段永不褪色的影像叠加回1958年上海的天蟾舞台,漂亮的僵尸后,终场唢呐响起,大幕缓缓落下。
幕再次打开,罗春、李元吉、苏烈、大刀手上台谢幕,唯独不见罗成。观众不干了。上海观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拗劲头至今还是常常能够见到,为等一位演员返场,甚至只是再露一面,他们可以齐心协力地有礼貌地鼓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那天就是这样。“叶盛兰!叶盛兰!叶盛兰!”观众有节奏地呼喊,鼓掌,再呼喊,再鼓掌,直到大幕再次拉开,舞台上,已经脱下戏装、换上扫地工作服的小生泰斗诚惶诚恐地向台下久久地深深地鞠躬。
叶少兰的祖父是富连成科班的创始人叶春善先生,叶氏一门出了十几位京剧名家,这是造化加熏陶,基因加苦练的结果。叶少兰说,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就是和哥哥叶蓬、表哥刘玉林一起在家里的铜制大床上唱戏玩。
大床单当幕布,小床单当出将入相的门帘儿,操练起来一台“大戏”。最贪恋的是剧场的灯光照明——“那时候戏院里靠前面的戏或主演未上场之前,灯光是不开足的,就等主角儿上场才全开。”哥儿几个想出点子:先关上里屋灯,作为压光;开外屋灯,打开一点门缝儿,透进光亮来,作为垫戏;门开到一半大,就是倒第二;等到说:“爸爸出来啦!
”或者说:“梅兰芳出来啦!马连良出来啦!”门就大开,里屋外屋每一盏灯大放光明,好似真正的大轴戏开演一般。
后来,叶少兰说:“小时候就是想做一个好演员,做灯光开得最亮的演员,做一个唱大轴的领衔主演,有前途的演员。”他做到了。
我虽然1983年已经知道叶少兰,正式进剧场看他的演出则是1992年以后了。那天,他演的是《三堂会审》的王金龙。从那天之后,我现场看过四次他的《三堂会审》,竟然每次都在小细节处看到不同,这才领会了业精于勤和艺臻于道的哲理。
有篇报道说:“叶少兰每次演(《群英会》)之前都要看父亲的电影、自己的录像,找出不足的地方,然后默排一遍、实排一遍、统排一遍、响排一遍,最后才能上台演出。”这决非诳语。
最后,我要说,虽然在“粉丝”掉价的时代,自称是某位演员的粉丝显得十分矫情,万分悖谬,我还是以做叶少兰先生的粉丝而深深自豪。皮黄声里,龙音激越,虎音豪放,凤音婉转;剑影翻飞,昂首凝眉,人在戏中,戏比天大。他就是那个灯光开得最亮的演员,京剧小生叶少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