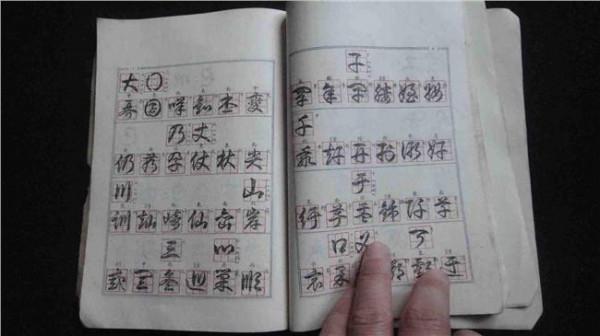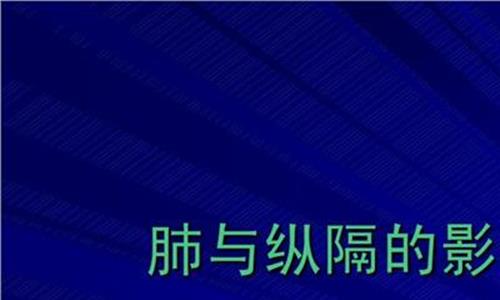张晖维舟 维舟 :萧条异代不同时——评《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
词学是张晖进入学术研究的入门途径。自十六岁矢志于学,他最初用心之处便在于此,也是其最早出成果的领域;而在词学之中,他又独对晚清民国时期最感兴趣,起因则是高中时对俞平伯的兴趣、以及摩习龙榆生《唐宋词格律》后发现龙氏资料晦暗不明。
在南京大学求学的七年间(1995-2002),词学是他学术活动的主要重心,他最初赖以成名的龙榆生年谱(大三学年论文),以及本科论文(梦窗词接受史)、硕士论文(晚清词学考论)均无一例外可划入“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范畴。
直至2002年到香港求学,才发生了一次对他而言重要的范式转变,转向诗学研究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及问题意识亦为之大变。概言之,本书虽在其著作中较迟出版,但可视为他前半阶段学术生涯的主要结晶。
结构与书写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是其硕士论文的扩展。这篇论文的原题为《晚清词学考论》,全文6.4万字,上编三部分:晚清词籍校勘兴盛的原因、《宋词三百首》与朱祖谋词学的建立、况周颐与词籍校勘;下编则是两篇资料考证汇编:况周颐著述年表、朱祖谋年谱简编;最后是139种参考文献的列表。
这其实原本就不像是围绕某个问题展开论述的单篇论文,而更像是一本书的雏形。上篇的三部分亦可彼此独立,后亦分别发表(除《宋词三百首》研究一篇改动较大,其余两篇通常只有少数字词调整,但“况周颐与词籍校勘”第四小节“超越校词的词学目标”为新写);下篇的朱祖谋年谱也已基本成形,收入本书,但“况周颐著述年表”和原参考文献则未收录。
当时其谋篇结构和写法,无疑仍是相当传统的治学方式,注重扎实细致的考证,而非问题先行,强调问题意识并以此总领全局,也很少以现代的文学理论介入讨论;实质上,这三篇考证除了时代背景一致,并未从整体上回应某一问题,或许也因此,他最终将之一拆为三。
若与其《中国“诗史”传统》(基于其博士论文)相较,其间差异一目了然。后者是集中讨论一个问题(“诗史”),充分发挥其考证功力的同时又从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角度入手,将之视为中国文学批评上的一个重要理论资源来探讨,重心是文学批评而非考证。
自然,考证并非不讨论问题,他原本是通过考证,回答了三个问题:词学的兴盛为何在晚清体现在词籍校勘领域?朱祖谋集词籍校勘之大成,但他的词学思想与理论体现在哪里?况周颐反对词籍校勘而致力于词学理论,其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虽未回应单个大问题,但这三个看似零散的问题其实是相互递进交织的。
现在的全书结构已被调整为四部分:文献、理论、世变、书评。
第一二部分是核心,无一例外都是2002年之前在南京时期写成的;第三部分是由对词学与词人身处历史背景的理解而来,注重的是“社会”而非“文本”。三四两部分倒有不少是在2002年之后所写,但那时他治学的重心已有所转移,那时不如说是对词学领域兴趣的延续性关注,且显露出他在后半期治学中的一个特点,即关注特定时代下学术与学人的处境。
他对这本词学论文集原已拟定书名《附庸遂成大国》,意指词学作为“小道”,至晚清民国时期达致高峰,成为国人所熟知的文学经典。
但天不假年,他的匆匆离去,使其未能完成其全部构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部未完成的遗作。他有许多庞大的设想,如重新评估近代的“旧文学”、梳理清代词学的传承脉络、词学由古典批评向现代文学批评的转折,如此等等,都来不及实现。
自21岁以《龙榆生先生年谱》少年成名之后,他在南京的最后几年其实很长时间都处于苦闷挣扎之中,除了经济上的困窘,更多的则是学术上如何自我突破的问题。
那时他一度有意再整理赵尊岳(叔雍)年谱,但最终将这一残稿锁在崇明老家箱内,多年未再继续,因为他意识到这只是学术成果上量的增加而难成为质的突破;本科毕业论文《价值的发现与理解的深化——论梦窗词的逐渐被尊崇及其文学史意义》,长达1.
6万字,阐明朱祖谋等晚清词家对梦窗词的接受,颇获师友好评,但他私下里对我说,自己并不十分满意。这两篇与“况周颐著述年表”均未收入本书,或确非其本人最满意者,但不免也有遗珠之憾。
未被继承的遗产 我们今天所知的作为文学经典的唐宋词,在很大程度上是晚清民国以来的研究传统所塑造的。概言之,我们不但接受了词和诗一样是文学经典,而且我们对哪些词作是最经典篇章的认识,实际上都受到了这一传统的塑造与影响。
然而在另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词学,又可说已成为绝学,它与现代研究机构中古典文学批评之下的词学研究,并不是一回事,在向现代学术研究的转换中,它是处在学科分类边界线上的学问。
这种状况,龙榆生1930年在《清季四大词人》一文中已道及:“念词至今日,渐就衰微。偶以现代词人,询诸学子,甚或不能举其姓氏。……晚近号称研究词学者流,又往往专注于两宋词人轶事之考索,苟叩以最近词人之性行,亦瞠目不知所对。
……特考今之难,不亚考古。” 十一年后,他在《晚近词风之转变》中又说:“晚近二十年来,士不悦学,中华旧籍多遭摈弃,而诗歌、词曲,幸因比附于西洋之纯文艺,得列上庠,为必修之科。
”这里已标举出几个重要的问题:词学在现代的生存空间,是因比附于纯文艺而得到生存空间的(但词学实有音律的一面,故龙榆生长期执教于上海音乐学院,而非某校中文系);现代人即便是研究词学者,也多是专注于宋词,对清代以来的词学词人,反倒更陌生。
正因此,当张晖由少年时代自发的强烈兴趣进入这一领域时,当他深入进去之后,便自然而然地遭遇到新的问题,并对他之后的学术生涯产生深远的影响。
这其中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所知的作为文学经典的词,是怎么形成的?“旧文学”与词人,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寻求自己的位置?这两个命题,前者促使他思考梦窗词的接受史、朱祖谋等人的校勘与词学理论,已开他后来对文学史书写研究的进路;至于后者,他后来所关注到的问题,如龙榆生的生命中的挣扎、南明诗人在战乱中的选择、以及古典文学在现代社会的变革与处境,大抵都由此而来。
本书中,在其硕士论文诸篇之外,最可注意的是这篇:《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
它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越出了词学批评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文化史与媒体生态的范畴。这也显示出他一个更广泛的关怀,那就是:在新文学的霸权之下,古典文学若要得到存续,则必须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和自我拯救能力,且最好是在公共空间得以存续的活的传统。
这里虽讨论的是近百年之前的状况,他也并不像当时的人所思的是“保存国粹”,但结合《朝歌集》中“追寻古典文学的意义”一文可以看出,他关注古典文学对活着的人的意义,若非如此,这一传统终将死去。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无疑已是一个断裂了的传统。更确切地说,现代的古典文学批评的成立,是奠基于对传统的距离感之上的——“文学遗产”在此是一个被研究的客体,而不是我们浸润于其中的传统,那是一个未被继承的传统。
也正因此,陈寅恪才说“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这句话本身就针对特定的语境,即古人的学说对我已成不带感情的对象。
陈氏强调我们后人应对“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须“完全明了”,这样“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张晖深知这一点。他在学术研究上的早熟,不仅表现为他扎实的基本功和洞见,还在于他对“理解之同情”的体悟。
书中对况周颐反对词籍校勘的解释,足可见之。他在文中指出况周颐的反对,实有另一层隐情:那就是,词籍校勘须耗费巨资,那不是清贫如况周颐所能负担的,因而他早年虽也曾从事校勘,但之后却被迫放弃而转向词学理论。
学者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其理论观点,有时是其自身行为的合理化解释,而未必完全只是观念的差异。写这篇论文时,他也不过25岁,但此前编撰《龙榆生先生年谱》,已使他颇能体察学术研究的甘苦,他之所以能察见况氏的弦外之音,无疑也是因为他自己对现实有诸多体会。
在此可以讨论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词籍校勘为何在晚清兴起?除了当时文坛注重用典、朱祖谋其人这一偶然性因素之外(校勘词籍需要大量资财,且须能完全沉静,又具经史校疏功底,这些朱都完全具备,别人则未必),我觉得还可补充的是:经过清代长期的传承,这时词已被承认为高雅的文学形式,完成了其经典化,并成为社会上文人阶层的普遍修养,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词学作为专门学问才会意识到进行完整校勘的必要性;这与当时文坛另一个现象——重视用典——在内在是一致的,即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丧失了与受众的直接性,而需要借助于特定的文学修养或大量注释来阅读。
从这一角度来说,词籍校勘既是高峰,又埋下了衰落的因子。 前人的这种处境,与我们现实中古典文学的尴尬处境,正相呼应。近百年来,中国的新文学与旧文学日渐分离,鲁迅等那一代新文学家还普遍多能写旧诗词(郁达夫等甚至相当出名),但如今,基本不再听说哪位现代小说家与诗人也擅长旧体诗词了。
两者的分途已势成必然。George Steiner曾说在英国,“没有古典素养的前提,就能研究现代文学,就能诚实地编撰现代文学,这简直令人震惊,难以置信。
”但在中国,这却是事实——同属“文学”,古典文学是专门学问,而新文学才为公众广泛接触。书中说:“‘风流未歇’实际上暗示着当时读书人的一种文化焦虑,即对于传统文化消亡的恐惧。
对文人来说,传统文化的载体就是诗词古文之类,而对欧风美雨的袭击,如何不让诗词‘歇了’,始终是一个困扰人的大问题。”这一段,不如说是他的夫子自道。 不说别的,即便是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易刊布——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尤难为世人所知。
书中谈到女词人张珍怀先生的著作颇有价值,而多在身后才得刊布,其实张晖本人著作,在某种程度上岂不也是如此?其硕士论文,2002年写成后即被评为同年“江苏省优秀硕士论文”,但拆分后的三篇,分别在2006年和2008年才得在学术杂志上刊发(故有些地方增补了2002年之后出版的资料)。
这本书能面世,也有赖他身后亲人及师友的诸多协助。
诸多细节地方的订正、补注(如《郑孝胥日记》的日期与页码)均可见心力,只极少地方略有小疵,如页278“结沤盟沧波如沸”,应是“鸥盟”;《尽吾身力不彷徨——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文化政治活动》一篇,在收入《朝歌集》和《忍寒庐学记》时均作《徘徊在文化与政治之间——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活动》,全文并无差异,不知标题何故不一。
至如页137注“越南的阮朝于1907年灭亡”,这应是张晖自己的错,阮朝1884年沦为殖民地,但真正终结普遍认为是在1945年,1907年发生的事是“东京义塾”的成立,国人知其亡国之恨当由于此。
书中某些观点亦可商榷,如认为“两广地区是近代词学的发源地”,理由是晚清词学四大家中,王鹏运和况周颐都是广西人、且朱祖谋曾担任过广东学政。
但这三人的活动中心都不在两广,朱祖谋任广东学政只三年,均未在两广开创学派,仅此实不足以说两广是“近代词学的发源地”,两广与“近代词学的起源”只能说有关联,而无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