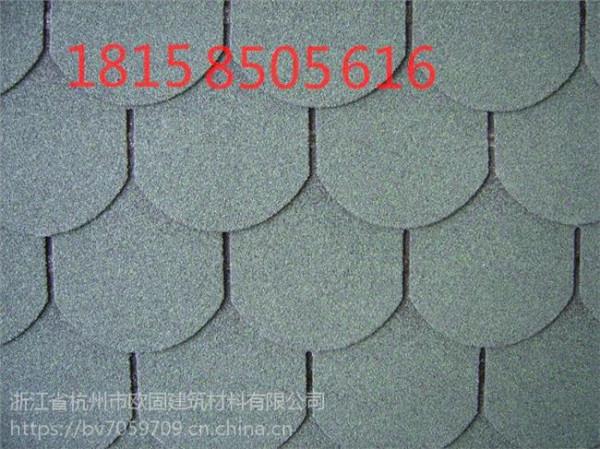张波的艺术空间 新型艺术空间:生存是次要问题?
[“站在行业的角度看,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呈现主要靠商业来带动,机制肯定有问题。如果社会主要靠它们来热闹,那么也很奇怪。”]
沿着上海的南京西路走过黄陂北路,如果你有余暇东张西望,可能会留意到东侧不远一个与众不同的空间。在寸土寸金的市口,这里不售卖商品,行人可以随意进入,或欣赏影像,或蹭到水果大餐,或观赏一场激烈拳击赛。
最近,这里成了一个路边阅览室,1979年至今整整300期的《艺术世界》杂志,摆放在室内供观众翻阅。
人民公园旁这个闹腾的小空间,叫艺术亭台。今年3月30日启动以来,它通过多个互动性极强的艺术项目,聚集起年轻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
与艺术亭台相比,4月成立、位于上海福州路弄堂里的激烈空间没那么热闹。进行中的“上交会”是一个长期项目,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展览,而是“艺术家自我组织的、一种介于艺博会和展示两者之间的工作方式”。用组织者石青的话说,激烈空间想做的事情与常见的美术馆活动“不是一个系统”,谈论起来难免抽象。他认为,激烈空间更像办公室,是工作的场所,而不是美术馆式的展厅。
尽管与大型艺术机构相比受众有限,这些新空间仍有滋有味地从事着艺术活动。免费是它们最直白的邀请公众参与的方式。
而在北京、广州和重庆等地,这类新型的艺术空间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运作,给艺术和公共生活带来不同的时间和体验。它们或是独立的艺术机构,或是美术馆的附属空间,也可能干脆就是一家特立独行的画廊。
它们为何出现?想做什么?希望解决哪些问题?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访了多家新型艺术空间和机构。
生产性的项目
这个周末,在瑞象馆举办的展览“上海·神圣”即将结束。“上海·神圣”的基础是英国摄影师尹黎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魏明德合作的研究项目,主题是定位并呈现当今上海的精神空间。
瑞象馆并不是个新机构,它成立于2008年。那一年,各类艺术机构伴随着艺术市场的高峰出现,其中就包括诸多新型空间,如北京的箭厂空间。这一波高潮,很快随着经济危机沉寂下来。赵成帅在《独立艺术机构的高潮与替代性》一文中认为,“2008年这个模糊的节点时间,(源于)中国当代艺术在2000年后的全面机制化在遭遇2008年金融危机时,部分年轻人在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动摇和质疑。
这种内部驱动力决定了(这些独立艺术)机构的组织者以青年艺术家、策划人为主,同时也决定了机构的角色与定位。”
最初的场地一年后即被收回,此后瑞象馆主要以“瑞象视点”网站为载体存在,持续征集和发布影像写作文章。2013年,创办人肖睿的老朋友施瀚涛回国加入瑞象馆。2014年5月,定位于影像研究、教育、展览等工作的瑞象馆在位于花园路的空间举办了开幕展。
展厅比很多人家的客厅大不了多少,但与展览相关的写作、讲座、纪录片放映等活动,以及与不同背景机构的合作,让艺术呈现非常丰富。“上海·神圣”展出的摄影作品数量不多但容量极大,而项目涵盖了展览和线下活动、学术研究和出版等,对包括宗教在内的上海当代精神空间进行探索。
项目制,这也是石青作为组织者赋予激烈空间的最重要特征。“我们不做纯粹的展览,不做个展、群展。我们做项目,可以是一个项目,也可以是几个项目混合。”
“腹地计划”是激烈空间的项目之一,不同城市的艺术家和从业者在各地游走,开展研究和创作。虽然目前它被冠以展览的名号,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呈现,但石青说,腹地计划其实是一种工作方法。
激烈空间寻找计划外的艺术家,与有农业、写作和媒体等背景的人合作,“因为项目式的工作方式,很多艺术家不是很适应,他们还是习惯创作可以在美术馆展示的作品。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种工作方式。”
位于北京草场地的二楼出版机构也推出了一个不太具备传统艺术形态的调查项目——六环比五环多一环。这一项目及其今年7月的展览,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呈现出这个地区所包含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是我们最想做的。”负责人之一葛磊说。
瑞象馆负责人施瀚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至少从去年开始,我们希望自己运作的是生产性的项目,能刺激产生一些新东西。”“生产性的意思是说,要禁得起推敲,结出一些成果。成果未必要达到学术研究的深度,但至少是经过消化的。”他希望以“生产性”对抗私人美术馆热潮中那些粗制滥造的内容。
年轻人的艺术飞地
艺术亭台所在的空间,曾是上海当代艺术馆的衍生品商店。临街,位置虽好,生意一般。而美术馆策划青年艺术家群展的经验显示,此类群展会令作品有所损失。“于是决定把这个空间改造为青年艺术家的项目空间。”上海当代美术馆策展人、艺术亭台负责人王慰慰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艺术亭台在大街上,观众可以免费进来,艺术家与观众交流有特别好的效果。
因为空间不在美术馆里,相对没那么严肃和郑重,不仅可以做实验、探索性的项目,也可以做特别接地气的项目。”
王慰慰说,比如高铭研和王懿泉的“一团乱麻”项目,在艺术亭台设计了十几天的日程,从空间发散到周边,安排了与观众互动的各项活动。艺术亭台隶属于上海当代艺术馆,是“支持青年艺术家的试验性艺术空间”。王慰慰希望它能为美术馆带来更多的观众和影响力,也希望进行更多探索,帮助艺术家发掘空间的可能性。
与艺术亭台相比,位于五原路弄堂里的元画廊以另一种空间存在形式连接上海的地气。元画廊创办人元雅静几乎每个月都会去北京、广州、重庆等地与艺术家交流,她同样关注年轻艺术家。除了青年艺术家的个展,非营利取向的室外项目也已经展开。
元画廊去年4月25日开幕,而非“圈内人”的元雅静过去一年一直在寻找方向,“办画廊的初衷,就不是以商业为主要目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要做常规展览?我没有办法回答自己。”与艺术家和策展人朋友交流的结果是,觉得应该在空间特别是院子上做文章,便有了室外项目的设想。明年,元雅静准备室内和室外空间一起策划,“展览做成项目式的,发现问题,探讨问题。”
“想真正推一些年轻艺术家,这样的一家画廊,自我循环不是首要目的。”虽然名为画廊,也需要收入推动自身发展,元画廊希望与青年艺术家的合作能跳出常规的展览模式,体现独立艺术空间的某些特质。
“艺术家的优势在于个人化的观察视角,这是艺术的根本……我们并不排斥集体的工作方式,但如果没有成熟和独立度做保证,这种集体是可以被怀疑的。”石青对机构工作方式的描述也说明,相对于服从市场与商业规则的艺术机构,它们希望尽可能保证艺术家的独立性。
改善土壤的机会
说起特立独行的艺术空间或机构,鉴于它们渺茫的盈利机会,人们往往简单地将其归入非营利机构的范畴。但与中国的其他领域一样,非营利艺术机构的标准也非常模糊。尽管如此,施瀚涛认为应该立足现实,以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关键看最后留下什么东西。是美术馆还是画廊不是那么重要。”
2014年,瑞象馆帮K11艺术空间策划了一年的公共活动,包括莫奈展、新媒体艺术展等的衍生活动。“收取一定的服务费。与其他机构的合作也有一些收入。”施瀚涛说,但收入与机构运营成本相比还相差甚远。
有研究者发现,上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非营利艺术机构要么向商业妥协,要么转瞬即逝。华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黄边站负责人之一黄小鹏以广州维他命艺术空间为例,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维他命空间在国际上那么有名气,跟它的经营模式有很大关系。
国外的非营利机构面临政府基金和私人基金的缩减,觉得维他命空间一边营利一边搞学术(的模式),会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2008年我写过文章介绍维他命空间,当时觉得它确实在游走。很多艺术家都要搞非营利空间,然后靠某个外来资本,这是不可靠的,那还不如推销自己的东西。”
2008年以来,到2014年,国内又出现了一波“独立艺术机构”开幕的高潮。据统计,去年一年,仅在北京就有7家空间出现,而北京活跃的独立空间有17家。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的基金会比如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也开始支持独立艺术空间。
显然,新型艺术空间尽管有可持续性的问题,强调更多的是自己的艺术、文化乃至社会责任。“站在行业的角度看,如果一个社会的文化呈现主要靠商业来带动,机制肯定有问题。如果社会主要靠它们来热闹,那么也很奇怪。没有艺博会,文化生产还在不在?什么在促使文化生产者做事情?”施瀚涛的话颇能代表此类机构和参与者的立场。
他说:“文化是权力的呈现,假如每个人、每个群体都有发言的需求,到底谁的声音能发得出来就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了。在中国,基金会和社区非营利机构这样的组织很弱,完全不能与官方和商业资本抗衡。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海前一段可能很热闹,但丰富性和均衡性有问题,有的甚至根本没有被激发出来,因为没有机制。
”谈及机构工作的意义,他说,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意义蛮模糊的,但“商业的世界已经够热闹,而它们的操作也存在问题,虽然正常,但我们换一种方式做做看,能留下文本也好,展览也好,对学生和其他群体的教育、辐射都有,也有意义。”
“社会太大了,就算有十个K11也不能覆盖。”可以展望的是,就算众多新型艺术空间的运作不能长期持续,但它们的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将在不断出现的类似空间身上得以传承、延续。
“改善土壤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黄小鹏从艺术家培养的角度入手,希望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改善发挥作用,这应该也是众多新型艺术机构共同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