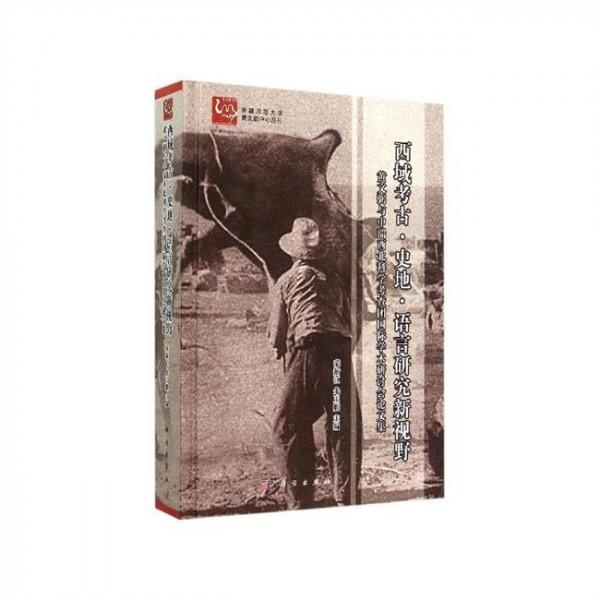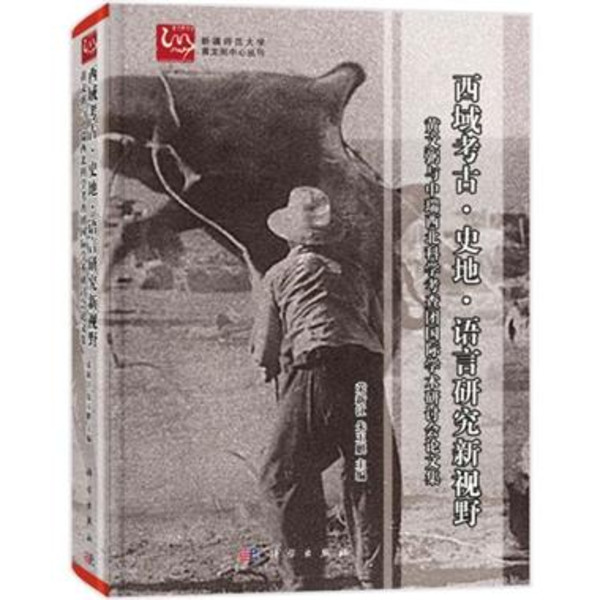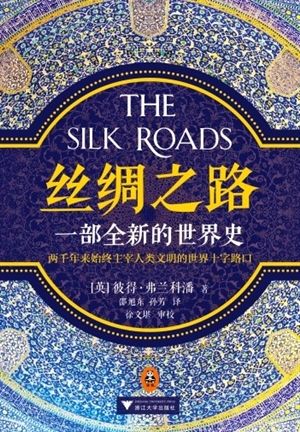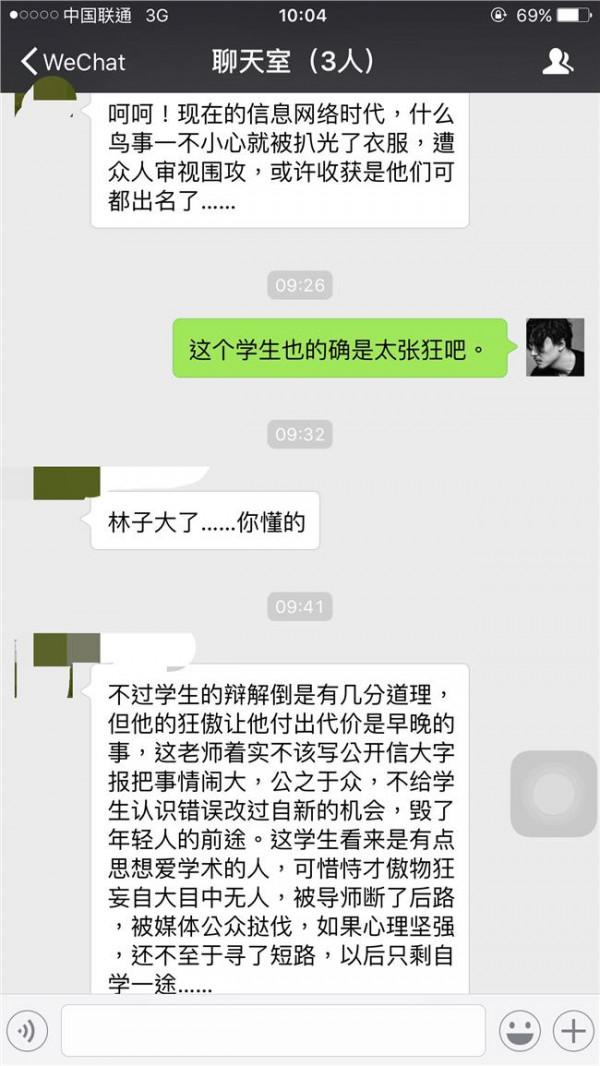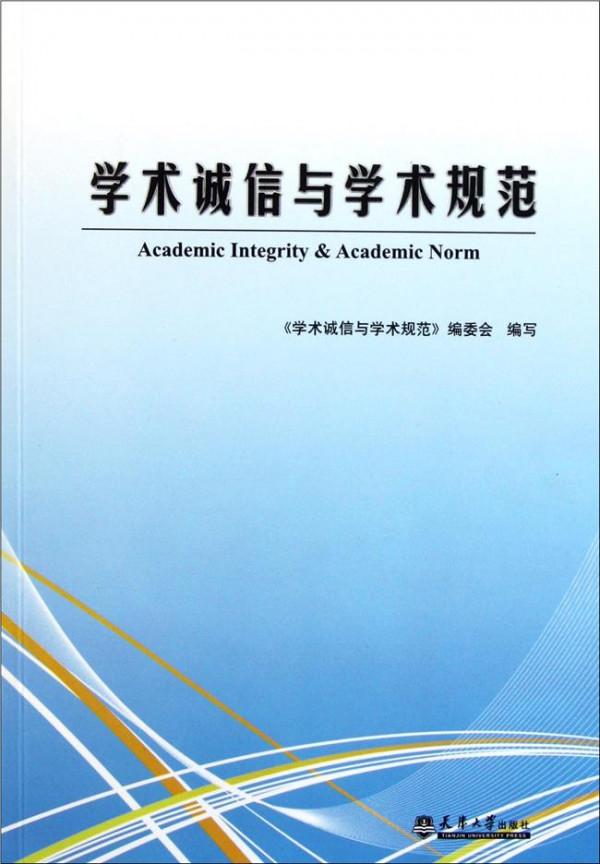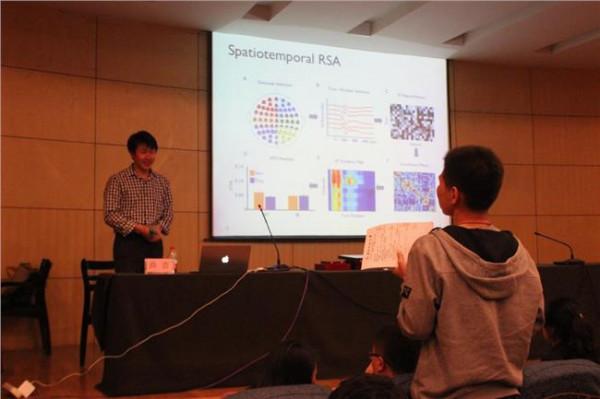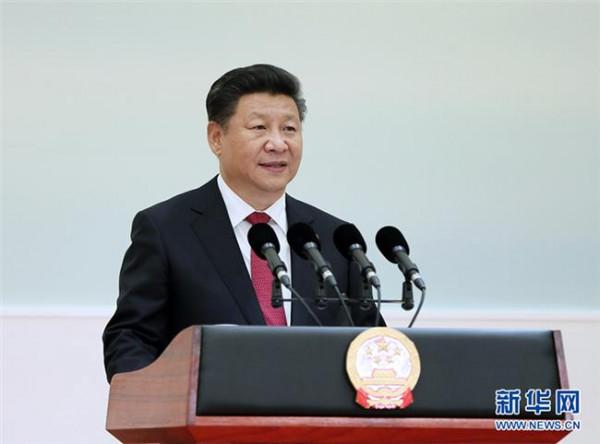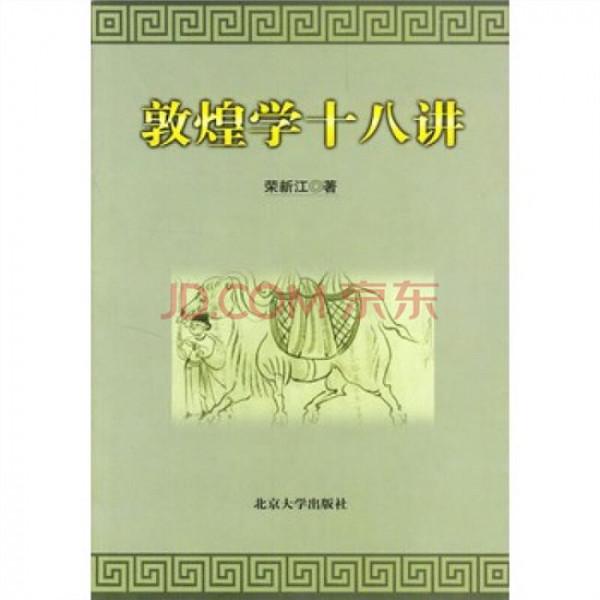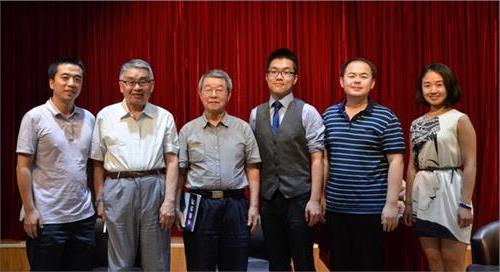写论文的心法:荣新江教授教你写论文
博硕士论文的写作,除了要遵守各自专业领域里的权威写作要求之外,还必须遵守所在学校的具体要求,要事先仔细阅读研究生院和所在院系的指南规定,不要事后再改正。
硕士生三年,当然主要是打专业基础,要做的事很多(前九讲所列举的也不完备),但与三年的博士生相比,时间是比较充裕的,所以我觉得不宜较早地确定题目,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很专的范围里,而应当在专业范围里广泛阅读,扩大专业基础和相关知识。
硕士论文的选题最好是一种以小见大的类型,即从小处入手,但能够联系到大问题的题目。这样的题目也需要一定的功力才能发现。一般来说,课堂作业、读书札记、学士论文和自己的硕士论文,甚至博士论文都有一定的关联。所以,应当注意自己的学术积累,做到有连续,也要有突破。
我有时觉得硕士论文不那么重要。硕士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应当在硕士的大好时光里做深厚的学术积累,积累得越多,以后产出的越多。所以硕士论文不要写的过长过大,可以把考虑成熟的问题分开,分别准备论文。当然,若是一个有机的组合,还是一口气写出来,则更方便读者。
我指导过不少硕士论文,参加开题、答辩的论文就更多,其中有成功的,也有很一般的。比较好的论文也有几篇,现在以2009年毕业的林晓洁的论文《中唐文人官员的“长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刘柳为中心》为例。这篇文章前面是绪论,交待学术史、规范术语,还有理论的探讨。
然后正文四节,分别是:一、长安初印象,二、迁谪书写中的长安:抽象与生活,三、京官与外任:两条道路的选择,四、家·国和两京之间。每一节里面再细分若干小节,分别讨论四个文人在不同时期的长安印象,每节后有小结和配图。
最后是结语,加以总结提高。这篇文章用了很多文学的材料,写的是历史学的文章,文字凝练,逻辑谨严。我原本担心这样四位重要的诗人都要讨论,是否可行。
她在处理具体的诗句时,考虑的是“长安印象”这个大题目,所以可以以小见大;又从长安的角度,驾驭四个文人丰富的资料,结果按时交卷,圆满完成。这篇硕士论文受到我主持的“隋唐长安读书班”的成员、硕士论文审稿人、答辩委员会的先生们的一致赞扬,又顺利通过匿名评审,得以全文发表在《唐研究》第15卷(2009年12月出版)上。
这篇长文虽然删掉了参考文献和后记,但还是很长,可是文章的逻辑性极强,不宜把它割裂开来,所以就一次发表,以便读者参考。
因为中国古代的典籍留存下来的很多,考古资料又极其丰富,加之近年来研究成果剧增,使得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生在三年之内都是非常紧张地度过的,甚至失去了做学问的乐趣,钻进去了,但跳不出来。论文的完成情况也不理想。有时是材料准备好了,但文章写得十分粗糙。有时是文章的前一半写得很好,很丰厚,但后一半却很草率。
因此,撰写博士论文首先要早些确定题目,题目要有一定的限度,不宜铺张得太广阔。早些确定了题目以后,在以后的读书过程中,就可以不断地积累素材。
因为博士论文的篇幅一般在十万字以上,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要早些安排好文章的篇章结构,这样可以有计划地分类收集资料,加以排比、分析,撰写初稿。不要把什么事情都等到最后再做,以为到最后再写可以一气呵成。博士论文是体大思精的作品,史学研究需要做很多前期的史料分析工作,不容易在最后半年时间里完成论文的写作,因此最好早些写出一些片段的成果。
最后的时间,应当更多地放在把片段的成果连缀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要从宏观上多加考虑,多做思考。也就是说,从材料中跳出来,考虑一些宏观的问题,把具体的研究升华提高。
总之,博士论文经过修改以后,往往是一个年轻学者的第一本著作,也常常是这位学者的成名作,因此应当充分重视这一名山事业。
博士论文既然是一篇论文,就要以论为主,叙述主要是作为过渡和辅助论述的部分。但博士论文又是一个整体,所以论文的各个篇章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这是比较难做到的一点。当然,有的博士论文就是几篇文章或一组札记的合集,那也未尝不可。但历史学的论文最好要有一定的联系贯穿其中。
我所指导的博士论文也有一些了,其中余欣的博士论文《唐宋之际敦煌民生宗教社会史研究》获得了2009年度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我就举他的论文为例,给以后的博士生提供一种类型的模本。当然,每个人的主题不同,内容、结构也不会完全相同。下面是余欣论文的目录:
从敦煌的具体事例出发,可以观察中古中国宗教社会史的许多微观与宏观的问题。这篇论文从“民生宗教社会史”的新视角来观察、整理、分析敦煌的材料,由具体的材料,论证敦煌民众受不同宗教信仰支配下的社会生活史。有些问题和材料虽是前人讨论过的,因为有新的视角,所以可以重新论证;有些材料是前人没有处理过的,因为有新的视角,所以可以重新论证;有些材料是前人没有处理过的,则用敦煌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
以上是我近年来指导或阅读博士论文的想法。其实,我自己没有撰写博士论文的经验,虽然我戏称自己的《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是“准博士论文”。因为该书的构架和撰写过程像是博士论文的做法,其中的篇章是陆续写成的,是我系统研究唐宋西北历史的组成部分,有的章、节本是原来的一篇文章,后来把它们按章节体系编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种方式有点像博士论文的做法,把一篇一篇陆续完成的论文连缀成一个比较大的构架。
另外,我还撰写过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先生的博士论文的书评,即《森安孝夫著评介》,也可以参考,特别是从中可以学习到一些篇章结构的安排和强调论述的写法。这本论文严格按照学术规范,以论文组成,发掘新史料,对原有的史料给出新的解释。
比如作者在文中说到,因为S.6551敦煌讲经文已经被张广达、荣新江论证为西州回鹘的材料,他原来的准备就没有必要发表了,只是在判定年代上有不同意见,拿出来讨论。这就是真正的论文,有论才写文。
自从对文科量化的管理体制实施以来,博士生在毕业之前,必须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或被接受)两篇论文,才能毕业。我是反对这种量化管理文科的做法的,但我一直主张学生可以发表文章,而且应当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和压力。
投给期刊的学术论文的准备和写作,和硕博士论文的基本原理没有什么不同,但应当遵守各个杂志不同的学术要求和规范。各个杂志是有自己风格的。比如《历史研究》比较注重大的问题,所以那些兼带着整理文书的敦煌学论文,往往是要被退稿的。
而某些强调实证的杂志,则不喜欢那些看上去有点云山雾罩的文章——即使里面有些思想的火花,也会被扑灭。把什么样的文章投给什么样的杂志,应当是要有所考虑的,但不能迁就杂志而改变自己的文风和论题。
一般来说,做敦煌研究的人,在第一次把一个文书录出来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成果,所以往往按照敦煌学的学术规范按行录文。但这样的做法,在一些看惯了一般史料引文方式的杂志编辑眼中,是白白浪费篇幅,也就往往难以通过。所以像这样录文较多的文章,你就应当选择像《敦煌吐鲁番研究》、《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这样的专业杂志,而不是《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
在学术刊物上第一次发表论文,是展示自己学术功力的重要手段,做得好,可以使自己在学术界站稳脚跟;但做不好,也就失去了学术界对你的信任度。所以这是一件要十分认真对待的事情,不可掉以轻心。这其实是业师张广达先生对我的教导,他说第一篇文章最好是实证性的,结论要极其扎实。
这就让我想起他在“文革”结束开始学术新生后所写的《碎叶城今地考》一文,该文针对郭沫若、范文澜等史学权威的西域两碎叶说,首先立论,根据遍检可资印证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献和资料,证明焉耆之地无碎叶;然后依据汉籍和阿拉伯、波斯文穆斯林地理文献有关碎叶城的记录做详细的换算和比对,把碎叶城锁定在托克玛克西南8-10公里处的阿克·贝希姆废城或托克玛克以南约15-16公里处的布拉纳废城;最后根据苏联学者对两处遗址的考古发掘,判断布拉纳为八剌沙衮城遗址,阿克·贝希姆为碎叶城遗址,而且把考古学者发掘的一座佛寺,根据其中供奉弥勒像的情形,判定即杜环《经行记》所记碎叶之大云寺。
碎叶只有一个,即阿克·贝希姆遗址。这个论证可以说天衣无缝,因而其结论基本上成为定论。
这篇文章发表十多年以后,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那时张先生已经移居海外,宿白先生在路上看见我,把我叫到他家里,说日本学者菅谷文则给了他一件阿克·贝希姆发现的有关碎叶的汉文碑刻拓本,要我给张先生寄去,可惜他的书和资料太多,怎么也没有找到。
这件新发现的“碎叶镇压使”杜怀宝造像记和一方残碑的拓本,随后发表在加藤九祚执笔的《中亚北部的佛教遗迹研究》第6章第6节,并有内藤みどり撰写的《关于阿克·贝希姆发现的杜怀宝碑》一文加以论证。
此后,周伟洲先生撰《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题铭考》,《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残碑考》,更加坚实了碎叶就在阿克·贝希姆遗址的结论。可以说,《碎叶城今地考》是一篇论证极其严密的实证性论文,而且幸运地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
其实你如果看张先生文中在讨论焉耆无碎叶时说到的一段话:“遍检可资印证的唐代西域地理文献和资料,包括粟特语国名表(Nafnāmak)、敦煌卷子中的汉文地志图经之类残卷、所谓‘钢和泰卷子’中反映925年情况的和阗—塞语行纪部分、伯希和编号1283号藏文卷子,特别是与焉耆有关的回鹘文《弥勒下生经》(Maitrisimit)题记等等,直到目前,都找不到碎叶位于焉耆的任何线索。
”你就知道作者在研究这个问题时下了多大的功夫。
粟特语国名表、于阗文钢和泰卷子、P.t.1283号藏文卷子、回鹘文《弥勒下生经》题记,这些西域、敦煌出土的相关材料,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学术界,有的是闻所未闻的,加上后面作者提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撰《道里与诸国志》、库达玛·本·贾法尔撰《税册》、波斯佚名作家撰《世界境域志》、波斯作家加尔迪齐撰《记述的装饰》、马合木·喀什噶里撰《突厥语词汇》,你可以想象作者检索了多少文献材料!
这当然还要包括所检索的汉文文献。这就是一篇文章透露出来的功力!而由于这样一篇文章的写作,我们也就可以知道作者为什么大致先后发表了《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和《嗦里迷考》这样两篇文章。
后者正是用回鹘文《弥勒下生经》题记来考证焉耆在回鹘时代被称作“唆里迷”,从而澄清了西域地理上的又一个疑问。张先生的“两篇半”处理的都是非常具体的问题,但从中可以看出功力有多么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