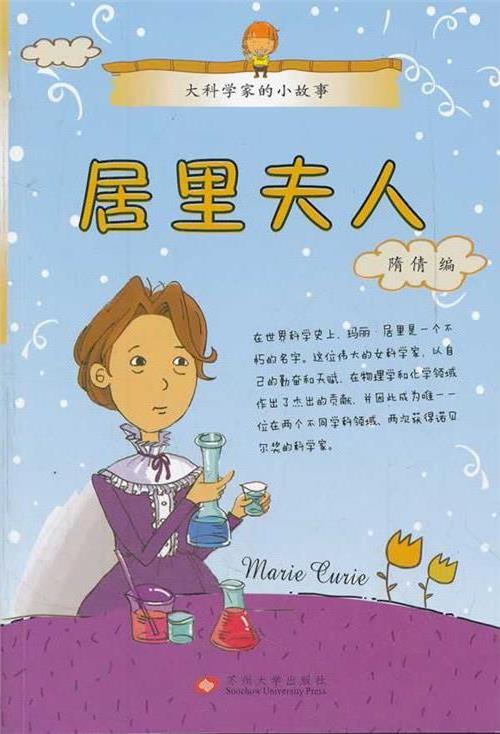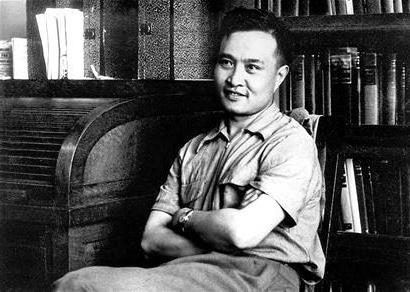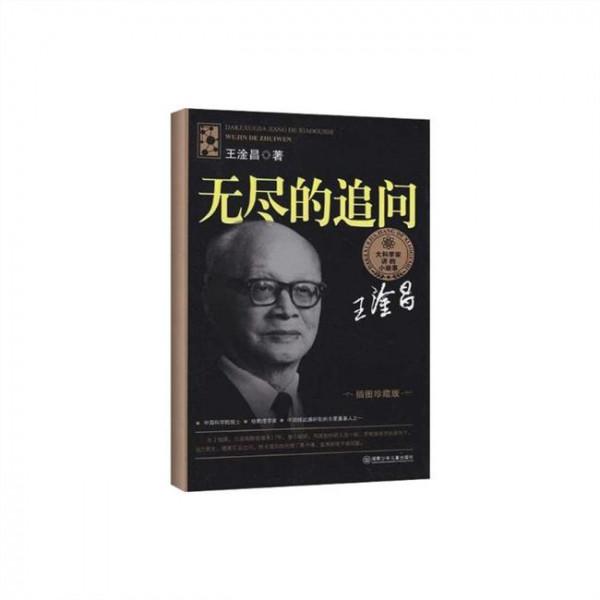王淦昌的孙子 王淦昌——大科学家的懿言嘉行
王淦昌(1907—1998),江苏省常熟县人,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50年5月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
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 药工艺、近区核爆 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 炸试验等都取得重要成果。
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
积极指导原子能研究所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翻开20世纪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册,我们会看到一个闪光的名字——王淦昌。他的科学生涯,和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壮大密切相关;他的科学功绩,深深镌刻在中国科技史上。他是惟一一位以第一获奖人身份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物理学家;他是既在核物理研究中做出优异成就,又在世界上开辟激光惯性约束聚变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他还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
这里,我们呈献给读者的是王淦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点滴懿言嘉行。
做一个好党员
1979年10月20日,72岁的王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志愿书上这样写道:“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蹂躏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是一个10亿人民、8亿农民的大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
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端正航向,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因此,我决心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在吸收王淦昌入党的会议上,他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经历深深教育了年轻的同志。“入党,可以多做工作。
”这是王淦昌的入党动机。入党之后,王淦昌好像变得年轻了,干劲更足了。他每天很早起来,一直工作、学习到深夜,甚至外出开会坐在汽车里时,也在思考科学问题。他经常督促科研人员说:“要快,要快些拿出成果来!”他抓紧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有一次,他在一份文件上写了这样一段批语:“依我看,时间就是生命,我们上年纪的人对此深有感受……要来个‘拼命地工作’,把科研搞上去!”
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前夕,王淦昌在《我们都要热爱祖国热爱党》的文章中写道:“我们每一个党员一定要牢记入党誓词,随时随地都应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埋头苦干,任劳任怨,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反对自私自利、假公济私,贪污浪费、消极怠工,争名夺利、搞特殊化,走后门、带头向‘钱’看,甚至不顾党的影响、不顾革命利益、不择手段地捞取个人私利的错误思想和作风,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1981年10月30日,在原子能研究所第四次党代会上,王淦昌被选为党委委员。他在发言中却首先作了自我批评。他诚恳地说:“我对原子能事业有深厚的感情,对原子能所也有深厚的感情,总希望把她搞得更好一些。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因为自己能力太差,年龄太大,力不从心,没有力量去各方面奔走,深入也不够,在所里的时间很少……第二个缺点是我虽然心里想把工作搞好,但由于水平的关系,没有达到我的愿望。原子能研究所的工作距离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还很远。
我作为所长,工作做得很不够……”就在这次会上,王淦昌十分谦虚地说:“今天又把我选进新的党委会,我年龄最大,党龄最短,内心有愧。我决心作为一个小小的分子,贡献自己的力量。”
王淦昌在党内始终把自己看作一名普普通通的党员。他始终按照党员干部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一言一行为人们做出表率。只要不外出,他必定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而且踊跃发言。有时党小组长还没有通知他,他就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询问组织生活会的内容。
一次,他听了党委书记《为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而奋斗》的党课之后,连声说好。回到宿舍,刚巧女儿来电话,他拿起电话,不问东,不问西,开口便说:“我刚听了党课,我想问问,你是不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1985年,王淦昌见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的唐孝威时说:“小唐,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
我们正在进行整党登记,你给我提提意见。”对此,唐孝威深受感动。与某些人以走过场的态度对待整党的情况相比,王淦昌是那样的真诚。他非常认真地按照党组织的要求,写了四千多字的整党总结,内容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全盘否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坚决拥护、自己的努力方向,最先交给了党支部书记。
王淦昌坦荡磊落,不谋私利。在个人生活上,他满足于“过得去”就行,从不向组织伸手要什么。1978年,他还没有入党,从四川调回北京后,全家老少三代五口人挤住在塔院的两间屋子中。夏天,王淦昌在家里穿着背心,一边摇扇子,一边看材料。当时,他已是二机部副部长,秘书看到这种情况,感到过意不去。王淦昌却说:“这没什么,国家有困难,我们要体谅。”直到一年后,他才搬进了组织上安排的住房。
入党以后,王淦昌更是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由于工作需要,国家为他配了专车,但他从不随便使用。早些时候,他从中关村和塔院的家里去京西宾馆或建国门外看望朋友,尽管路途比较远,他常常是乘公共汽车来回。他还讲这样做的好处:“可以锻炼身体。
”平时因私事打电话或发电报,他都自己付款,不允许秘书“公私不分”。他绝不允许家里人私用公车,但他的专车却又是谁都可以搭乘。他认为座位空着是一种浪费,有同志同坐还可以了解一些情况,实在是一举两得。
1982年,王淦昌与丁大钊、王祝翔一起因为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王淦昌获得了3000元奖金。1983年10月,他在给原子能所党委的信中说:“发给我的奖金3000元,我自愿全部捐献给原子能所子弟中、小学,愿祖国的娃娃们能茁壮地成长,从而能为娃娃们的父母减少些后顾之忧,为原子能事业多做工作。
”原子能所党委研究后决定,收下王淦昌的赠款,并把成果奖中留在所里的2000元拿出来,共计5000元设立“王淦昌奖学金”,作为奖励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奖励基金。
王淦昌时刻想着国家的困难,为国分忧之心感人至深。为国家,他注意节约每一度电。一次,青年科技人员小高到他家请他在一份材料上签署意见。已是晚上7点多了,王淦昌家里的灯一个都没开着,他正与老伴坐在沙发上看新闻联播。
看完电视,小高说明来意后,王淦昌先关掉电视,然后摸着黑走进书房打开写字台上的台灯,坐下来阅读材料。为国家,他注意节约每一滴水。有一次,他到外地出差,住在招待所里。半夜里,王淦昌被汩汩的流水声闹醒了。
他连忙叫醒熟睡的秘书说:“听!哪里的水箱漏水了?”秘书说:“这么晚了,明天再说吧!”“不行,”王淦昌说,“等到天明要浪费多少水呀!”就这样,他和秘书一起从三楼开始查寻,最后在一楼找到了那个漏水的水龙头。
为国家,他注意节约每一分钱。一次出国访问,大使馆为他安排了高级房间,他不去,而是住进了普通旅馆。国外朋友请他吃饭后,作为答谢,他自己花钱买礼物送给朋友,而将国家给他的几千美元全部上缴。在国内,有一次他去邮局买报,工作人员粗心,多给了一份,回家发现后,他连连怪自己太马虎,又立即下楼到邮局送去一份报钱。
1992年4月,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第六次学部委员(院士)大会闭幕词中指出:“我们有很多的老科学家,他们非常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做了很大的贡献,但他们从来没有拿他们的贡献向国家、向人民提出什么要求,他们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科技人员,在那里努力地工作。
……如钱三强先生、王淦昌先生,他们所做的贡献远比一般的学部委员要来得大、来得多,但他们今天仍然和普通的科技工作者一样地在工作、在生活……我们自己应该向钱三强先生、王淦昌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学习,在全社会提倡艰苦奋斗的传统,而不能把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反过来向人民要求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淡漠“生前身后名”
自1997年8月7日外出散步时被自行车撞倒骨折以来,虽经近半年的治疗,骨伤痊愈,但王淦昌的身体每况愈下,并且体重减轻了近10公斤。几次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原因。1998年9月11日,王淦昌因咳嗽、咳痰伴消瘦入住北京医院。
一年时间内,他已是第三次住院了。对此,王淦昌自嘲地说:“我这个院士,可成了老跑医院、老住医院的‘院士’了。”在被自行车撞之前,尽管已年过九旬,他的身板、气色都很好,每天坚持上、下午两次下楼散步,上、下楼梯也不要人扶,偶尔还打一打自编的简易太极拳。
秘书和家里人为王淦昌的身体担心,知道他一向工作起来不要命。一周七天,对他来说只有星期七,没有星期日。他从来不知道休息,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在生活上也非常节俭。这次住院前,秘书每次去王淦昌家里看望或协助工作,就劝他多注意休息,吃得好一点,以增加营养。
他却说:“用不着吃那么好,也不能总休息,光吃饭,不干活,这怎么行?我们的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工作起步并不晚,但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却落后了,如果不拼命努力,急起直追,心里不安哪!
”住院后,他仍然坚持要秘书每天都给他送书报、期刊,并认真阅读,时刻关注着世界核物理学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动向。他说:“我自己感觉身体还可以,闲坐着、闲躺着就是浪费时间。我虽然不能到实验室搞研究了,但还可以看一些资料,还可以想一些问题,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听他这么说,家里人和秘书也希望他这次能和上次住院一样,诊断结果只是肺部的轻微炎症,过半个月、一个月就可以出院,继续从事他念念不忘的能够造福全人类的核聚变科研事业。然而,经检查、化验,9月底出来的诊断结果却是低分化胃腺癌,而且已向远处转移,属胃癌晚期了。
秘书心情沉重,不忍将这不好的消息告知王淦昌。但他自己已有所察觉。如果只是一般的病症,怎么会有那么多专家前来会诊、一次又一次地检查?他首先就想到了肺癌,因年轻时得过肺结核,现在又总是咳嗽,所以猜测肺部有问题。
王淦昌不断地向秘书询问诊断的结果。这令秘书十分为难。说吧,担心他不能承受这样大的打击;不说吧,随着病情的发展,想瞒他也瞒不住。最后还是大夫说,像王淦昌这样的大科学家,对生老病死应该是非常达观的,没有必要一直瞒着他。
确如大夫所言,王淦昌对患了胃癌显得非常平静。他说:“人总是要死的,我已经91岁了,也做了一些工作,虽然微乎其微,但总算没有交白卷。”
王淦昌自称“微乎其微”的工作,其实都是令世界瞩目的科学成就:提出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领导建立云南落雪山宇宙线实验站,并开展富有成效的宇宙线物理研究;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理论;参与组织领导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地下核试验工作。
一个人的一生,即使只取得这其中任何一项成就,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但王淦昌总是那样谦虚,当人们赞誉他是“科学泰斗”、“一代宗师”、“中国原子弹之父”时,他就急忙辩解:“不能这样说,这样说完全不对!”急得仿佛要跟人吵架似的。
躺在病床上,他这样评价自己的一生:“我聪明不够,勤奋也不够,致使这一生没有做出令我自己十分满意的成果。现在回想起来,越想越觉得过去如果能够更加刻苦、更加勤奋的话,就有可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又对秘书说:“我们的国家现在还不够强大,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祖国的兴衰,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要以国家利益为重,要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对此我还做得很不够,希望你们年轻一代做得比我好,使祖国早日强大起来。”
许多人将自己的“生前身后名”看得很重,生死为此所累。王淦昌却荣辱不惊,对此举重若轻,豁达从容,心中想的只是国家和科学事业。具有这样胸怀的人,对于生命本身的自然过程,自然是泰然处之。
事业永恒
1998年11月初,王淦昌的病情开始恶化,经常呕吐、发高烧,渐渐发展到不能进食,只能靠静脉输送营养液维持生命日常所需。医院给王淦昌用一些贵重药品,他坚决不同意,说这是浪费,完全没有必要。人们送来花篮,祝愿他早日康复,他也不接受,说对他最大的安慰是工作上有成绩,早日拿出成果来。他对科研人员说:“你们不要总到医院来看我了,这样影响工作。我不能连累你们。你们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
对前来探望的领导同志,王淦昌没有为自己提任何要求,也没有为家属提任何要求,而是再三嘱托,要把工作做好,要把我国的科技事业搞上去;落后就要挨打,腐败就要灭亡,这样的教训太深刻了,我们不能重蹈覆辙。
在住院期间,每当原子能院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来看望时,王淦昌一再强调,要把研究工作做扎实,把年轻人带好,特别是要形成团结协作能打硬仗的队伍。12月5日,已经十分虚弱的他,吃力地对上海激光联合实验室的同志说:“一定能成功。”12月9日下午,当原子能院的科研人员汇报在氟化氪激光装置上抓紧进行激光束输出能量和系统同步动作调试时,他从被子里伸出扎有输液针头的双手,吃力地合手击掌,表示祝贺。
12月初,王淦昌病情急剧恶化。他明白自己已经来日无多,这时才流露出一丝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遗憾。他说:“从国际上看,激光聚变的点火试验,可能会在下个世纪初。激光聚变‘点火’意味着惯性约束聚变的科学可行性得到验证。我要能看到激光聚变的点火试验该有多好!”
12月10日21时48分,王淦昌带着对核聚变事业的无限牵挂,与世长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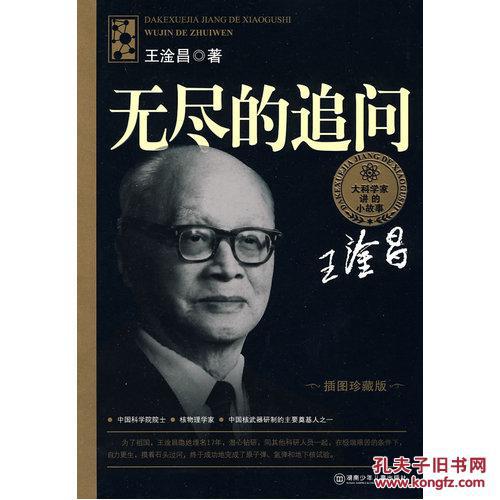



![郭宝昌的养母 [转载]《大宅门》编剧导演郭宝昌其人其事](https://pic.bilezu.com/upload/b/25/b25b55da60b4e81b5b0544ff5ba4ee3b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