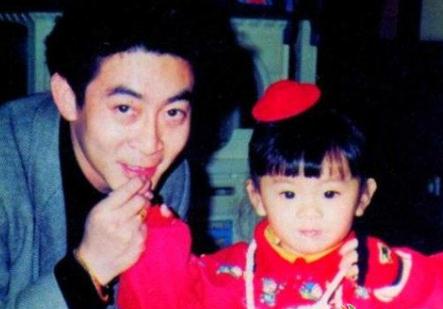童庆炳文集 童庆炳:一代文学家的集体导师
那一天,莫言正在第三届东亚文学论坛的会上,他的手机响起,来电者为北师大文学院的张清华教授。接通电话后,莫言听到一个令人悲伤的消息:“童庆炳老师去世了。”意外、难过、震惊,莫言半响无语。张清华还在电话里讲述,莫言回过神来说:“太突然了。”
2015年6月14日,著名文学理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因病在京去世,享年79岁。童庆炳被誉为中国文艺学理论领域泰斗级人物,目前,大陆仍有近五百所高校在使用他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而更让他声誉卓著的,是他曾担任过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严歌苓等当今中国最知名作家的老师。
这些已成文坛大腕的弟子,虽然在昔日课堂上汲取的知识和受到的启发不一,但几乎都对童庆炳师恩难忘。
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合作,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童庆炳正是这个班的辅导员和导师。被请来参与授课的,还有秦兆阳、何镇邦、林斤澜、宗璞、韶华、谢冕、牛汉等知名学者和作家。
研究生班的举办,实则是为解决鲁院学员的学历问题。文革十年,中国的教育全面废弛停滞,许多有志于文学的青年,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文学训练。即便1977年后恢复高考,十年的教育断层仍难以接续。而在此时,已有一批非科班出身的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开始登上文学舞台。
1986年、1987年,鲁迅文学院曾两次向国家教委申请备案,开办文学青年培训班,却未得到批准。于是,鲁院转而谋求同高校联合招生。
鲁院相关负责人找到时任北京师大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的童庆炳。童后来回忆,“那时我们跟教育部门说得很清楚,这些作家虽然有才华,但是文化程度限定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所以需要系统的课程教育,看看人家外国人是怎么写作的,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写作的。”
1988年6月22日,北师大研究生院向国家教委呈送《关于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申请报告》,其中提到举办研究生班的主要目的是作家的学者化,“如果能办成‘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将为中国作家学者化的工作尽一份力量。”得到国家教委批准之后,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开办。
为招收到真正有文学才华的学员,童庆炳等人为招生设立的硬性条件极低,他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发表一篇作品,这篇作品经得起推敲就可以被录取。”因此,小学毕业的莫言、中学毕业的余华,都得以进入这个“研究生班”,他们在当时已小有名气。
其他的学员当中,迟子建是西北大学的在读大学生;毕淑敏是鲁迅文学院第四期文学创作进修班学员;刘震云是《农民日报》的机动记者,因住所离鲁院较近,得知消息也报了名;严歌苓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李准介绍进去的,之后不到一年,就退学申请出国了。
这个研究生班只办了一届,总共招收了44名青年人,多处而立之年,如今都已成为文学界或文学理论界的顶梁柱,占据着中国文坛的半壁江山。童庆炳“中国文坛教父”的名号,也就由此而来。
在研究生班,这批处于知识“贫血”状态的学生们,努力汲取文学理论知识,一些人渐渐成名。
童庆炳开设了一门《创作美学》的新课,一个学期十六讲。莫言对这门课印象深刻,“童老师在课堂下是蔼然长者,端重慈祥;在课堂上却是青春生动,神采飞扬。他讲课时的样子经常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童庆炳在讲授“形式情感”和“内容情感”的互相冲突和征服时,曾以俄国作家蒲宁的小说《轻轻的呼吸》为例,来说明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之间的对抗所产生的审美愉悦。当时莫言就很兴奋,“似乎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东西,但朦朦胧胧,很难表述清楚。十几年来我经常地回忆起这堂课,经常地想起蒲宁这篇小说,每次想起来就产生一种跃跃欲试的创作冲动。”
但莫言并不是一个“好学生”,他常常逃课,逃课的原因他后来回想道,“一般来说,研究创作美学的书,与作家的创作不会发生什么关系,作家更不会用创作美学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当年我之所以逃课,大概也是存有这种心理。回头一想,遗憾良多,逃童老师的课,当然是一个重大的遗憾。”
不仅如此,莫言甚至还请了一个月假,理由是回高密老家盖房子。当时鲁院的负责人周艾若(周扬之子),因此事要开除莫言。莫言听说了,就找童庆炳说情,这件事才得以化解。后来,莫言带着一份检讨书回到学校,当时的童庆炳并没有太多责怪他。
这届研究生创作班,学员普遍面临的问题是英语基础不佳。莫言也为英语头疼,毕业考试的英语试卷,仅有58分。随后,北师大又安排莫言补考,结果又一次考了58分,还是不及格,但最终北师大和鲁院经过研究决定,还是让莫言通过了。
童庆炳与莫言的关系,先师后友,莫言的学位论文《文学创作与童年经验》,就是在童庆炳的指导下完成的。毕业之后,莫言谈起在北师大系统学习对他的影响,说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走了很重要的一步”。
而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一次和童庆炳聊天,他说道,“我真后悔,可以说是后悔极了。我那时很年轻,还不能理解老师们的话,没听从老师们的劝告,应该好好地学理论,好好地学外语。”
这一届研究生班,还有一件喜事,就是两名学员余华与陈虹结为夫妇。研究生班毕业后,陈虹在空政文工团创作室参军从事创作,余华则为了和陈虹在一起,最终放弃了在嘉兴文联的工作,留在了北京,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
余华追忆童庆炳时说:“我在1993年辞去浙江的工作定居北京以后,童老师为我操心,当时程正民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童老师和程老师做了学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调入北师大中文系教书,后来是我自知教书不行,主动知难而退,辜负了童老师和程老师的美意。作为童老师的学生,我深受其益。”
这届学员毕业之后,北师大与鲁讯文学院再次申请继续举办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教育部没有再批准。因此,1988年北师大的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是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培养出了日后在中国文坛大放异彩的作家群。
或许,童庆炳也没有想到,这批学生会有如此的影响力。他后来欣慰地说:“这还是一届幼芽,我希望将来有那么十个八个人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文坛的顶梁柱。现在来看,这个作家班没有白办。”
童庆炳与人交往,平易和善,不论对方名气大小,均以君子度之。比如说,童庆炳与季羡林的来往。用童的话说,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完全是无功利的。“我送给季先生书,他送给我书。我问候季先生,他问候我。”
2000年夏天,季羡林居所不远处的古莲花开之时,童庆炳第一次去拜访季羡林。童在后来回忆道,“我们的谈话几乎是漫无边际的,谈到文坛的风气。最后,季先生兴致勃勃,又亲自挽着我的胳臂,走出家门,以他亲手栽种的一池正在盛开的古莲花为背景,肩靠着肩,又合照了一张,就像两个亲密的朋友那样。”
童庆炳个性和善、耿直、谦虚,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和他交往的人,也往往具有相似性格。尤其是与大书画家启功相交的趣事,童向他的学生们多有讲述。启功当时还是北师大的副教授,他将自己的课程称为“猪跑学”,童庆炳打趣道,所谓“猪跑学”就是讲到哪里算哪里。
上世纪80年代,启功住在小乘巷,童庆炳住在月坛北街,两家相距很近。童常常去找启功,或是请教问题,或是聊天。启功的书房,在童看来,非常简朴,仅有一些古书,一张书桌,一把硬椅子,此外就是一个条凳,专门招待客人坐。
童庆炳去找启功,每次都是童坐启功的椅子,启功坐条凳。童就对启功说:“启先生,我是你的学生啊,干吗和我这么客气。”启功则往往一笑而过,并不答话,直接问:“有什么事,说!”然后推过来一碟子五香花生米,让童庆炳尝尝。
后来,童庆炳和启功成了邻居,童住北师大8号红楼,启功则住6号红楼。家近了,启功有时就主动和童庆炳打电话,说:“请你过来,有件事找你说说。”到家里来,清茶两杯,两个人就开始聊天。
有一次谈到老舍的话剧《茶馆》,启功说:“那算是好吗?连写话剧的方法他都没有掌握。”童庆炳连忙问,这是怎么讲?启功说:“幕帘一拉开以后,台上好几十甚至上百人,这让观众看哪个人说话呢?哪有话剧这么写的啊?话剧啊,像曹禺那么写,才像是话剧的样子。”
童庆炳后来回忆和启功的交往,称“启功对古今许多人物和正统的看法不一样。可是这些他不拿到外面去说,只是跟说得来的学生聊聊天、讲一讲。”两个耿直的人,遇到一起,就是这么有趣。
值得一提的是,启功的书法作品,标价颇高,向他求字的人也多。童庆炳有一次受朋友之托,请启功题写青岛大学的校名,当时还想要送些土特产酬谢,结果启功告诉童,“千万别送东西和钱。”说完准备纸笔,就手为童庆炳题写校名。这件事,童庆炳后来常常感慨说,“大家就是大家,非常人所能为。”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文艺界有一个主流观点,即“形象和形象性就是区别文学和非文学的特征”,以此为创作指导,大量作品出现公式化、图解化、概念化的倾向。
童陆续发表了《关于文学特征问题的思考》、《评当前文学批评中的“席勒化”倾向》、《文学与审美》三篇学术论文,认为过去的很多创作,只是用形象作为传声筒来传达思想,因此这些作品往往不能感动人。因为它是在配合某种观念、某种政策来写某种作品。一个作家要表达一种观念,然后围绕这个观念,设计出一组形象,讲一个故事,这就变成小说了。在这种文学观念影响下,文学就变成了讲一种思想或概念的工具。
当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学界主流观点仍然认为文学是某种宣传工具,特质是社会生活的反映,而童提出文学的特质是审美,被视为离经叛道,在当时是有巨大压力的。童的观点在当时引起极大争议,但最终被慢慢接受。后来有人归纳说,“童庆炳做的事情,是把文学的形象特征论,改造为文学审美特征论”。
童庆炳的学术成就中最广为人知的,就是《文学理论教程》的编写。1990年,教育部决定高校要编两部文学理论教材。一部是由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合编的“综合大学教材”;另一部是“师范院校教材”,由北师大童庆炳牵头,联合陕西师大、山东师大编写。没想到的是,综合大学的那本教材没编出来。于是童庆炳主编的教材,不仅在师范院校使用,综合大学也使用。
当时的高校招生,无论是报考哪个专业,都要考一门文学理论,指定用书就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
此后,童庆炳又陆续编写了《文艺心理学教程》《马克思与美学理论》《西方文论发展史》《美学》等教材。童庆炳的多部文学、文艺学教程,有近五百所高校至今仍在使用,影响广泛。
童庆炳逝世之后,北师大文学院的一位老师说出了对童庆炳的评价,他是一位亲切和善的长者。在治学方面,现在的学校教育是有些浮躁的,童庆炳老师,则堪称学术界的一股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