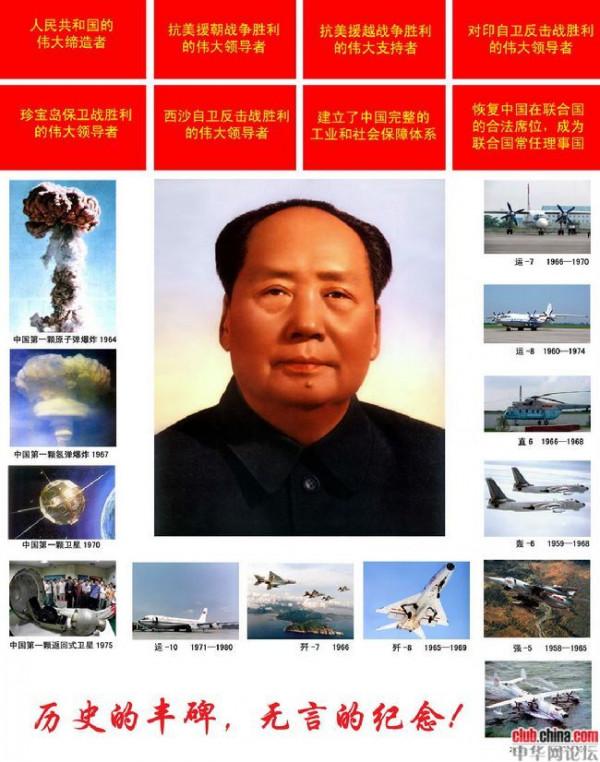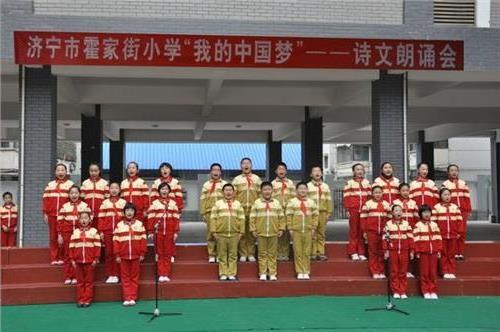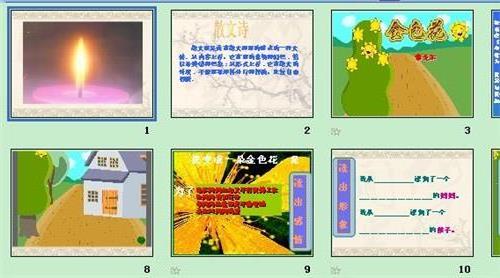娜夜诗歌 从黑夜走向白昼——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中国女性诗歌的崛起期,以翟永明、唐亚平、伊蕾、海男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诗人掀起了猛烈的性别风暴,女性诗歌犹如奔腾的江水经过险峻的三峡,呈现出重岩叠嶂、激流澎湃的景观;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后直到21世纪初则是女性诗歌的转型期,王小妮、蓝蓝、荣荣、路也、冉冉、娜夜、鲁西西等人的作品,淡化了性别对抗的色彩,以深厚的人文关怀展示了新一代女性的宽阔胞襟,这阶段的女性诗歌则像出峡后的长江,潮平岸阔,豁然开朗,但其一往无前、奔流到海的气势,同样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一 1985年,翟永明在完成《女人》组诗之后,还写了一篇《黑夜的意识》作为序,内称: 一个个人与宇宙的内在意识——我称之为黑夜意识——使我注定成为女性的思想、信念和情感承担者,并直接把这种承担注入一种被我视为意识之最的努力之中。
这就是诗……黑夜作为一种莫测高深的神秘,将我与赤裸的白昼隔离开,以显示它的感官的发动力和思维的秩序感。黑夜的意识使我把对自身、社会、人类的各种经验剥离到一种纯粹认知的高度,并使我的意志和性格力量在种种对立冲突中发展得更丰富成熟。
同时勇敢地袒露它的真实……站在黑夜的盲目的中心。我的诗将顺从我的意志去发掘在诞生前就潜伏在我身上的一切。[1](PP.140~142) 很明显,翟永明所说的黑夜意识,正是新潮女性自觉寻求的精神上的独立,即女性觉醒的意识,也是一种神秘的、极度私人化的意识。
20世纪80年代中期,翟永明等女性主义诗人,正是以此观念为主导,在诗歌中确立了女性的主体意识,建立起女性诗歌的话语体系,特别是以身体语言为重要特征的言说方式。
以“黑夜”为标志的女性主义诗歌作品,充满了女性的自我崇拜和自恋情结。她们的作品或是冷艳圣洁,有一种可远观而不可近睹的神秘感;或是性感魅惑,在对身体的“自我抚摸”中显示其魅力的不可抗拒;或是如处子般的纯洁,在对女性成长过程的细腻描述中,展示出一种真纯的“女儿性”。
当翟永明最早标举“黑夜意识”的时候,那是振聋发聩的“登高一呼”,就女性诗歌的发展而言,无疑具有开拓性意义。
但是一旦“响者云集”,一种群众运动式的后遗症也就随之而来——女性作家彻底洞开自我,凸现激进的躯体经验,编织纯粹的女性寓言,性别大战越演越烈,女性崇拜,矮化男人。不一而足。
如果任这种一窝蜂、极端化的局面持续下去,必然把女性写作引入另一条死胡同。有鉴于此,一些女性诗人开始思考往后的路该怎么走。于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女性诗歌出现调整与转型也就十分自然了。
当年提出“黑夜意识”的翟永明,十年后又写了一篇文章《再谈“黑夜意识”与“女性诗歌”》,其中有这样的话: 尽管在组诗《女人》和《黑夜的意识》中全面地关注女性自身命运,但我却已倦于被批评家塑造成反抗男权统治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形象,仿佛除《女人》之外,我的其余大部分作品都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过于关注内心”的女性文学一直被限定在文学的边缘地带,这也是“女性诗歌”冲破自身束缚而陷入的新的束缚。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摆脱“女性诗歌”即“女权宣言”的简单粗暴的和带政治含义的批评模式,而真正进入一种严肃公正的文本含义上的批评呢? 要求一种无性别的写作以及对“作家”身份的无性别定义也是全世界女权主义作家所探讨和论争的重要问题……女诗人正在沉默中进行新的自身审视,亦即思考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
女诗人将从一种概念的写作进入更加技术性的写作。
无论我们未来写作的主题是什么(女权或非女权的),有一点是与男性作家一致的:即我们的写作是超越社会学和政治范畴的,我们的艺术见解和写作技巧以及思考方向也是建立在纯粹文学意义上的。我们所期待的批评也应该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发展和界定。
[2] 翟永明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指出女性诗歌冲破了自身束缚却又陷入了新的束缚的现象;一是提出一种“新的写作形式,一种超越自身局限,超越原有的理想主义,不以男女性别为参照但又呈现独立风格的声音”。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超性别写作。很明显,此时的翟永明已经在从“黑夜”走向“白昼”了。 从黑夜走向白昼,不是倒退到当年那种在“男女平等”的旗号下漠视性别差异,以及性别意识被政治意识、阶级意识所遮蔽的时代,而是在充分意识到性别差异,充分尊重女性的性别特征与个性特征的基础上,对女性社会定位与社会属性的重新思考,是对女性意识的一种深化与升华。
实际上,女性不是仅仅拥有黑夜的,她们同样拥有白昼,她们要在白天生活、恋爱、思考、写作……仅仅在黑夜中出现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女人,仅仅表现黑夜的诗篇也是不完整的诗篇。
因而从黑夜走向白昼不仅是翟永明等女性主义诗人在走的道路,同时也是女性诗歌的自然发展趋势。
走向白昼的女性诗歌仍然是女人味十足的,只不过不再过分张扬“黑夜意识”,淡化了性别对抗色彩,而是侧重表现当下社会中女人的生存状态——她们的感情,她们的愿望,她们的生命体验。比起20世纪80年代的充满亢奋的宣言和强烈的抗争色彩的作品,21世纪的女性诗歌整体色调较为明亮,在对女性世界的复杂性与多元性不断地予以探索的同时,还渗透了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女性主义诗人,很少人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但她们在诗歌中的形象,却毫无例外地都是以精英女性的姿态出现的:或是振臂一呼的女性先知,或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女巫,或是圣洁无瑕的处子……然而也有始终不以精英为然的女诗人,王小妮就是一个。
当诗坛卷起女性主义的狂飙时,王小妮并没有去凑热闹,而是选择了独立的写作姿态。随着性别风暴尘埃落定,王小妮的形象在世纪之交诗坛的混沌背景中也分外地清晰起来。
王小妮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生活不是诗,我们不能活‘反’了。我们要先把自己活成一个正常人。”[3](p.223)她的丈夫、诗评家徐敬亚曾这样描写她的写作状态: 她,像街头上任何一个人那样活着,安详地洗衣、煮饭。
读一些书,写一些字……一日三餐,她和顺地从她的天空之梯上按时走下来,在菜市场、洗衣机和煤气炉之间,她带着由衷的母性,为她的两个亲人烧煮另一种让双方心理温暖的作品。
在这一切之后,她才是一个世界上全职的诗人……一个不会下任何棋打任何牌的人,一个拒绝唱卡拉OK的人,一个没有饰物没有化妆品的人,一个连自行车也不会骑的人……在最看重名声与利益的年代,她几乎不用与自己的私念战斗就可以安然地写作。
而王小妮认为,她这样活着,已经十分美好。[4] 对王小妮而言,她最看重的是自由。她要按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为此她宁可辞去公职;她要按自己的本性去写作,为此她从不拉队伍、扯旗号、发宣言。
她随意地生活,真诚地写作,在她的诗歌《重新做一个诗人》中写道: 每天只写几个字/像刀/划开橘子细密喷涌的汁水。/让一层层蓝光/进入从未描述的世界。//没人看见我/一缕缕细密如丝的光。
/我在这城里/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 “把自己活成一个正常人”,“无声地做着一个诗人”,这就是王小妮对诗与人的关系的理解。在世纪之交,王小妮奉献给诗坛的《白纸的内部》、《我看见大风雪》、《和爸爸说话》、《十枝水莲》等诗篇。
是新时期女性写作的重要文本。王小妮的诗和她的活法,她的不趋时、不做作、不追潮流、不怕被遗忘的定力,她的自然松弛、不急不躁的写作心态,使她对当下的女性诗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小妮之后,越来越多的女性诗人加强了“内功”的修炼,诗歌的写作从漂浮的空中回到地面,诗歌的主体由女神、女巫、女先知还原到普通女人。 蓝蓝曾写过一首很有影响的诗,题目叫《让我接受平庸的生活》,比起小女子的青春浪漫,这是一种对生活更深刻的理解。
荣荣也曾在《诗刊》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让诗歌拥有一颗平常心》。她说:“诗更多地潜在我的内心而不是一个面具……我写我的发现,我的感觉,我的心动,我的诗大多是随感类的,很多是随手写下的。
唯一的好处是,这样的诗不那么急功近利,不空,不无病呻吟,不虚情假意。没有恢弘的篇章,没有长篇巨制,这是我对诗的态度的必然结果,对此,我并不感到特别遗憾。”[5]正是在这种平常心态下,荣荣以女性最熟悉的厨房生涯为题材,写出了一首《鱼头豆腐汤》: 用文火慢慢地熬/以耐心等待好日子的心情/鱼头是思想豆腐是身体/现在它们在平凡的日子里/情境交融合而为一/像一对柴米夫妻/几瓣尖椒在上面沉浮/把小日子表达得鲜美得体/当然鱼最好是现杀的/豆腐也出笼不久/像两句脱口而出的时话/率真直白本色/最耐得住时间和火/身在异乡时鱼头是个故己/豆腐像心情落寞/锅上这道菜啊否则/有心人会将餐桌上那种吸溜/误认作抱头痛哭声。
当诗融进了一个诗人的生命,当她不再刻意为诗的时候,诗的题材似乎也就俯拾皆是了。日常生活中最缺少诗意的鱼头、豆腐,到了诗人的笔下,竟与诗人的生命融为一体,一道鱼头豆腐汤,成了柴米油盐的夫妻现实生活的写照。
你不能不佩服诗人的眼光,她能在最琐屑的生活中,在一般人认为最没有诗意的地方发现诗。这也正印证了荣荣的诗观:“这么些年的坚持,是缘于内心对诗歌的热爱,因为这份爱,便特别喜欢那种由心而生的随意的诗歌,自然的诗歌。
技巧总要退而居其次……”[6] 比荣荣、蓝蓝更年轻些的路也,则批评那些凌虚蹈空的诗作:“一个诗人不该把自己架空,跟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呀岁月呀流浪呀马呀月光呀荒原呀梦呀心中的疼呀黑暗呀永恒呀搅和在一起,我害怕那种诗,在那种诗里生命大而无当,连谈一场恋爱都那么虚幻,没有皮肤的触摸的快感,仿佛爱的对象是万米高空上的云或者峰顶上的雪莲——写诗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离地球越来越远,而离火星和天王星越来越近么?”[7]她的诗纯情、自然,她喜欢通过具体的事物来展示其生命的底蕴。
她的爱情诗《地图册》、《我想去看你》,显示了抒情主人公为爱而义无反顾,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她的另一首诗《单数》,则写尽了一个单身女人的心境: 如今,一切由双数变成了单数/棉被一床,枕头一个/牙刷一只,毛巾一条/椅子一把,照片保留单人的/窗外杨树也只有一棵/还有,每月照例徒劳地排出卵子一个/所有这些事物都是雌的/她们像寡妇一样形影相吊/像尼姑一样固守贞操 如今。
一个人锁门。一个人下楼/一个人逛商店,一个人散步,一个人回屋/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大摆宴席,一个人睡去/一个人从早晨过到晚上/还要一个人走向生命的尽头/布娃娃在书架上落满灰尘/跟我一样也没有配偶/我离异了,而她是老姑娘/我们同病却无法相怜 电话机聋哑人似的不声不响/谁能在夜深人静时拨通我的心弦/我连心跳的每一下都是孤零零的/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引起回音/我是韵母找不到声母/我是仄声找不到平声/我是火柴皮找不到火柴棒/我是抛物线找不到坐标系/我是蒲公英找不到春天找不到风 我是单数,我是“1”/以孤单为使命/以寂寞为事业 路也说:“我从来都认为诗歌是一种主观的、不要命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文体。
这种表达在我的诗中比比皆是。写诗我要让自己感到痛快淋漓,有一股子‘狠’劲,语感节奏要有乘坐着波音747起飞的感觉,否则我不快乐,不愿意写。”[8]从《单数》,我们可以领略到这种极致的表达。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诗人以象征为主要表达策略适成为明显的对照。
三 爱情,永远是女性诗歌的第一主题,21世纪初的诗坛依然如此。但是古今中外的爱情诗名篇实在太多了,突破已有窠臼,谈何容易?不过在大量的浮泛的爱情诗之作中,我们仍不时能读到让我们的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这是女诗人李见心的《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 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像艾略特的妻子一样的疯/像罗丹的情人一样的疯//那时我就会/不用沉默而用语言/不用语言而用行动/去爱你/毫不留情地爱你//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向你展示我全部的美丽而不忸怩/向你展示我全部的丑陋而不知耻/把尘土当作粮食/把花朵当作伤口/把生当作死/把死当作生……//你如果是人/我就是你的神/你如果是神/我就是你的人//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我要是个疯女人该多好/可理智已像穿过耶稣身上的钉子/钉在我身上/从不松动 有一种说法,诗人和恋爱中的人都是疯子,这不无道理。
李见心这首诗的别具一格之处,就是强烈,正因为强烈,感觉压倒了理智,才可能说出在正常情况下说不出来或羞于开口的“疯话”。
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光自爱、自恋是不行的,光爱一个人也不够,他还要以一颗爱心拥抱世界。 进入21世纪后,翟永明把眼光投射到社会上的弱者身上。她的《雏妓》一诗,对一个未成年少女被蹂躏的遭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她12岁瘦小而且穿着肮脏,眼睛能装下一个世界/或者根本已装不下哪怕一滴眼泪”。
她的《老家》一诗,则真实描写了河南农村由于贫困而卖血导致的令人震惊的场景: 蜂拥而至的/除了玉米肥大的手臂/还有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小孔/它们在碘酒和棉花的扑打下/瑟瑟发抖/老家的皮肤全都渗出/血点血丝和血一样的惊恐/吓坏了自己和别人/全世界的人像晕血一样/晕那些针孔/……全世界的人都在嘲笑/那些伤口他们继续嘲笑/也因为老家的人不能像换水一样/换掉血管里让人害怕的血/更不能像换血一样换掉/皮肤根部的贫贱。
读着这样的诗句,真让人欲哭无泪,我们也由此看到了走出了黑夜的翟永明的博爱胸怀。
刘虹长期生活在深圳,面对灯红酒绿的消费社会,她保持了诗人的良知与爱心。她说: 一个人之所以选择诗,首先来自于他历万劫而不泯的率真与求真的健康天性;其次是超乎常人的敏锐的疼痛感,和一颗朴素灵魂对世界深切而悲悯的抚触。
对于我,写作最直接的内驱力,则来自于对异化人性的传统价值和中心文化的不认同,是自觉地边缘化精神生存下人性的持守与抗争,是自我放逐中对丰美生命的积极吁求和无奈喟叹……作为女性诗写者,我秉持“先成为人,才可以做女人”的存在逻辑,不在诗写中把自己超前消费成“小女人”。
追求大气厚重的诗风,贴地而行的人文关怀,理性澄明的思想力度和视野高阔的当下关注。[9]刘虹也确实是照她的宣言去做的。
信息时代与消费时代的种种标志,诸如电视、小车、网络、复制……进入了她的观察视野;而诗人则不满足于仅只是把它们描绘出来,更重要的是借这些新鲜的甚至是光怪陆离的意象,抒写出当代人的真实的感受。
她的《小车时代》,体现了对小车带来的文明的反思。她的《笔》,则是对键盘、复印取代了笔的功能的思考: 笔的语言不同于嘴巴和手指/激情退去便不留痕迹/生命需要承诺、时光需要检点时/笔能挺身而出,作呈堂证供……/一个时代因笔的缺席而失语/被扁扁地塞进打印机/隔着B3或A4,人的面孔模糊走形/复印过的爱情丧失体温/传真去的信誉怕留指纹/一切都可以拷贝/只是真诚,不能设副本…… 网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与生活方式。
这首诗真实地反映了传统的笔正从办公室淡出的情况,在一种怀旧情怀中,表现了对人间真情的呼唤。
四 由关注身体的欲望写作到关注精神的灵性写作,是世纪初女性诗歌写作的又一重要变化。 诗人,因为所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经验,但这些具体琐屑的人生经验永远满足不了诗人理想与情感的饥渴,他渴望超越。
灵性书写,就是诗人实现精神超越的一种途径。对女性诗人来说,诗是与世界对话的一种方式,是由身体通向精神的桥梁。如何在保有鲜明的女性意识的前提下,寻找一种从身体出发但又不囿于身体,基于欲望但又不囿于欲望,在日常生活和普通生命中所蕴含的那些属于永恒性的哲学层面的东西,这是当下女性诗人正在探索并有所体悟的课题。
诗人蓝蓝在《写作手记》中说: 一块从泥土里挖掘出来的碎陶片,从它可得到我能够描绘的整个陶罐的形状,那优美的,盛满奇思异想的容器。
当我写阳光时。我仅仅是在写灿烂的阳光吗?在秋天,我所写下的悲伤的树叶仅仅是树叶吗? 树林中的阳光容易使人想起《牧神的午后》(德彪西根据马拉美诗作谱写),它迷离斑驳的光线与树阴深处莫测的气味、悬尘,构成半梦半醒的氛围。
某些诗歌(例如里尔克的作品)的不朽魅力便有这样的特征——敞开又隐蔽,正如强光,吸引又阻拦人的眼睛一样。[10](pp.334~335,p.344) 这虽然只是蓝蓝的创作思想的不完整的表述,却体现了这位女诗人对艺术的深刻的领悟。
她的近作正是这种艺术观念的体现。蓝蓝从小生活在农村,她的不少诗作是以农村的寻常景象为题材的,像这首《歇晌》: 午间。村庄慢慢沉入/明亮的深夜。
//穿堂风掠过歇晌汉子的脊梁/躺在炕席上的母亲奶着孩子/芬芳的身体与大地平行//知了叫着。驴子在槽头/甩动尾巴驱赶蚊蝇。//丝瓜架下,一群雏鸡卧在阴影里/闭或骨碌着金色的眼珠。/这一切细小的响动——/——界深沉的寂静。
读这首诗,很自然想到王维的《鸟鸣涧》,王维诗用“月出”、“鸟鸣”之动,反衬山涧之静,在一片静寂中蕴含着出世之思。蓝蓝的《歇晌》亦深悟动静的辩证法,诗人捕捉了农村歇晌这一常见现实,以知了鸣叫、驴子甩动尾巴、鸡雏骨碌着眼珠等细小的响动反衬世界的寂静,所谓“静故了群动”,全诗通体脱俗透明,一种对人生的彻悟之感,油然而生。
鲁西西也是一位善于从平凡的生活现象得出不平凡的人生体悟的诗人。
1、2、3,这是今天幼儿园的孩子就认识的最简单的数字了,鲁西西却从中发现了诗: 让我先说说1吧,这是多美的第一天。/我不得不把1当作一个章节。/凡歌里有2的,这歌就不是孤独的。//当我说到2,我们就开始含笑,因为有了爱情,就有了指望,/特别那爱情,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3是众人,土地,是大多数,/这么多的儿女,果园,和香柏树,我爱他们,/但是没有感到心满意足。 这首诗题为《创世纪》,这么大的题目,鲁西西写来,却举重若轻。
在她看来,1、2、3是一切事物的起点,却通向无穷,通向永恒。诗人用三个简单数字架构全诗,这与老子《道德经》上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也正是中国诗人笔下的“创世纪”。鲁西西具有一种把哲理的思辨溶入到她的艺术知觉的能力,当她面对外部世界的时候,她所捕捉与描绘的意象通常与她内心的感悟浑然一体: 每天早晨,当我醒来,/都听见有个声音对我说:把手伸出来。
/太阳光满满地,落在我手上,/一阵轻风紧随,把我的手臂当柳树枝。/还有那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你都当礼物送给我。/我接受的样子多么温柔啊! 这首题为《礼物》的诗,表面上写的是清晨所见所感,却不同于一般的即景之作,人与自然是那样的谐和,充满了一种博大的胸怀和感恩的心念。
偏居西北的诗人娜夜,远离女性主义性别风暴的中心,作为一个孤独的、敏感的女人,她顺从内心感觉的召唤,她的先天的素质与对诗的真诚使她能通过自身的体悟达到与自然的某种契合。
这是她的《起风了》: 起风了我爱你芦苇/野茫茫的一片/顺着风//在这遥远的地方不需要/思想/只需要芦苇/顺着风//野茫茫的一片/像我们的爱,没有内容 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11](p.164)诗人却说:“在这遥远的地方不需要/思想”,换句话说,当爱情来临的时候,只要投入地去爱。并细心体味这爱就行了,不必去问为什么,爱是没有道理可讲的。
自然的意象与诗人内心的体悟就这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了。 总之,由女性隐秘的内心欲望的倾吐到对人类整体命运的领悟,由女性生命体验的强化到对女性生命体验的超越,这是21世纪初的中国女性诗人正在走的道路。
这是一条崎岖的,每一步都要经过艰难攀登的路,也是中国女性诗歌通向真正的辉煌之路。 参考文献:[1]翟永明.黑夜的意识[A].吴思敬(编选.磁场与魔方——新潮诗论卷[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翟永明.再谈黑夜意识和女性诗歌[J].诗探索,1995,(1)。 [3]王小妮.诗不是生活我们不能活反了——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问[A].王小妮的诗·半个我正在疼痛[M].
北京:华艺出版社,2005。 [4]徐敬亚,王小妮的光晕[J],诗探索,1997,(2)。[5]荣荣,让诗歌拥有一颗平常心[J],诗刊,2003,6(上半月刊)。 [6]荣荣,诗观[J].
诗刊,2003,5(下半月刊)。[7]路也,诗歌的细微和具体[J],诗刊,2003,8(上半月刊)。 [8]路也,答问[J].诗选,2004,(12)。[9]刘虹,为根部培土[J],诗刊,2004,6(上半月刊)。
[10]蓝蓝,静止与移动[A],汪剑钊(编.中国当代先锋诗人随笔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1]帕斯卡尔,思想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