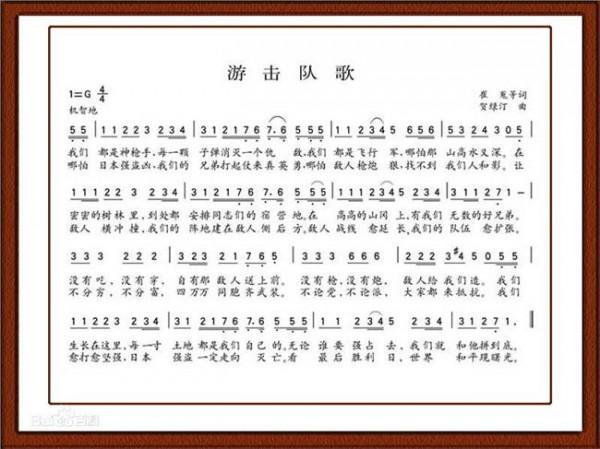暖光许钧 许钧:独特的目光和多重的选择
——安德烈·纪德在中国的历程以及对我国的启示作用 如果说卞之琳对纪德的译介与接受具有某种互动特色,那么盛澄华同纪德的精神交流和他对纪德的研究则为中国学者选择纪德、理解纪德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从1934年在清华研究院读研究生期间开始接触纪德起,盛澄华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潜心于与纪德的精神交流之中:潜心读纪德,译纪德,悉心领悟纪德的思想艺术精髓,全面研究纪德。
盛澄华与卞之琳一样,一方面全面阅读纪德作品,选择翻译有关作品;另一方面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纪德作品的理解和研究中去。
在翻译方面,盛澄华主要翻译了纪德的三部重要作品:《地粮》、《伪币制造者》和《日尼薇》(Genevière)。在对纪德的研究方面,应该说盛澄华的努力是继张若名之后中国学者与纪德的又一次精神交流。
据北塔的资料,早在1934年就读清华研究院期间,盛澄华就写过一篇题为《安德烈·纪德》的介绍性文章。此后15年间,盛澄华从结识纪德、阅读纪德、翻译纪德到研究纪德,一步步接近和理解着纪德。
我们知道,盛澄华与纪德的交往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关系,达到相当的深度,而这一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他对纪德作品的研究和独特见解。事实上,盛澄华不仅多次当面向纪德请教,还有不少通信往来。
在对纪德长达十余年的研读、翻译和思考中,盛澄华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在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盛澄华将他主要的研究心得汇集成书,取名《纪德研究》。关于盛澄华与纪德的关系及他对纪德的研究情况,钱林森在《法国作家与中国》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特别谈到三点,即盛澄华的研究具有一般研究者不具备的三大优势:一是“认真地阅读纪德,并且以自己的批评观点”,因为在盛澄华看来,“对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应予以理解,而非衡量,他的作品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尺与秤”;二是盛澄华“真切地通过迻译了解纪德”;三是“由于对作者的熟稔因而可以更多地借助于作者本人的阐释洞烛作品真髓”。
并由此得出结论:“在中国的许多研究者所砌的攀向纪德的无数面墙中,只有盛澄华最接近纪德。
”对一这结论,我们可以持不同看法,如北塔在《纪德在中国》一文中就提出了不同观点,但细读盛澄华对纪德的研究文章,我们会发现盛澄华确实为我们认识、理解纪德,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
首先,盛澄华基于对纪德作品全面、深入的阅读,从整体上把握和评价纪德在艺术与思想两个方面的发展。在《纪德艺术与思想的演进》一文中,盛澄华以纪德的创作为依据,将其思想与艺术的演进分为相对独立但又相互影响的三个阶段:由《凡尔德手册》至《地粮》的创作,是“纪德演进中的第一个阶段,也即自我解放的阶段”;而《窄门》、《梵谛岗的地窖》、《哥丽童》、《如果麦子不死》等作品的问世标志着演进的第二阶段,即“对生活的批判与检讨”的阶段,要回答的是人“自我解放”了,“自由了又怎么样”这一本质问题;而《伪币制造者》则代表着纪德进入了其思想与艺术演进的第三个阶段,即“动力平衡”阶段。
盛澄华明确写道: 不消说,《伪币制造者》在纪德的全部创作中占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以篇幅论,这是纪德作品中最长的一本;以类型论,这是至今纪德笔下唯一的一本长篇小说;以写作时代论,这是纪德最成熟时期的产物。
它代表了作为思想家与艺术家的纪德的最高表现,而同时也是最总合性的表现。纪德在生活与艺术中经过长途的探索,第一次像真正把握到一个重心。由此我们不妨把纪德这一时期的演进称之为“动力平衡”的阶段。 其次,基于对纪德思想的深刻理解,盛澄华突破了纪德在艺术与思想等方向表现出的种种矛盾的“表面”,试图以辩证的手法揭示纪德的精神本质。
他指出:“纪德是那种人:他重视争取真理时真诚的努力远胜于自信所获得的真理。因此他不怕泄露表面的矛盾,因此他教人从热诚中去汲取快乐与幸福,而把一切苟安、舒适、满足都看作是生活中最大的敌人。
在这个意义上,纪德才在尼采、陀思朵易夫斯基、勃朗宁与勃莱克身上发现了和他自己精神上的亲属关系。
尼采所主张的意志说,陀思朵易夫斯基所观察的‘魔性价值’,勃朗宁所颂扬的‘缺陷美’,勃莱克所发现的‘两极智慧’,以及纪德所追求的不安定的安定,矛盾中的平衡都是对人性所作的深秘的启发,都是主张在黑暗中追求光明与力,从黑暗中发现光明与力,藉黑暗作为建设光明与力的基石的最高表现。
”由此,盛澄华对纪德艺术与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轨迹的把握可见一斑。对“不安定中的安定”和“矛盾中的平衡”的追求,构成了纪德思想与艺术内核的独特因素。
在对立中寻找平衡,也正由此得到发展。面对“艺术的真理”和“生活的真理”这两种互不相让的真理,纪德所追求的是“协调与平衡”。“多变”与“一贯”,不安定与执著,矛盾与平衡,在盛澄华看来,正是这种种丰富而深刻的对立性和纪德对其深刻的把握,构成了纪德艺术与思想的内核。
再次,基于对纪德思想与艺术发展的全面把握,盛澄华针对纪德的后期创作,表达了自己独立的思想和与众不同的观点。上文我们已经谈到,于1936年11月发表《从苏联归来》一书之后,纪德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国外,都遭到种种责难与误解,超越了文学层面的种种批评甚至谴责一度淹没了其他声音。
但盛澄华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从纪德思想与艺术的演进角度,评价了《从苏联归来》表达的观点及所谓的思想“突变”。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但当纪德到了六十岁以后突然思想明朗地走入左倾的道路,这是一九三○年代轰动世界性的一件事情。其实这对一个一生中追求自由与解放,同情被压迫者痛苦的作家如纪德原可看作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盛澄华看来,纪德从苏联归来产生的失望以及他对苏联的批评恰恰证明了纪德的一贯态度,即追求真理的态度。在这一点上,盛澄华对纪德的理解确是深刻的。
从张若名到卞之琳再到盛澄华,我们看到,中国学者对纪德的理解与把握,不是对法国文学界的盲从,也不是各种声音的简单回响,而是从各自的角度走进纪德的世界,表达不同的观点,表明对纪德的不同理解。无论是对纪德思想与作品的评价,还是对作品的选择,中国学者都充分表现出目光的独特性和选择的多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