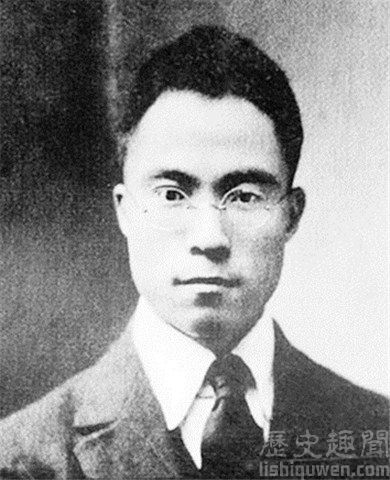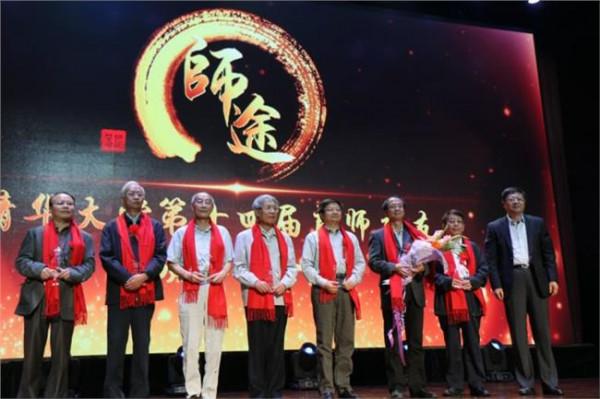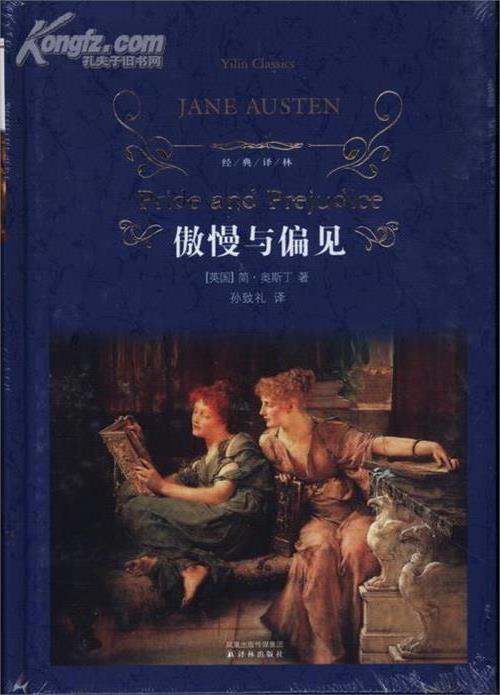钱文忠的老师是谁 钱文忠忆恩师季羡林:他是中国梦的标志性人物
郭超/摄影 7月10日,季羡林的学生钱文忠(左)与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右)等人从外地赶到临清市,一起缅怀季先生。图为他们在参观季羡林纪念馆。
■ 周末人物 2014魅力文化
季羡林逝世五周年。五年过去了,今天再看季羡林,这样一位文化泰斗、文化标杆式的人物,我们看到了什么?钱文忠忆恩师季羡林——
7月10日上午,天空飘着小雨。
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憩园内,凭吊者成群。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钱文忠着白衣黑裤,在雨水打湿的水泥地上,面对着季羡林墓,双膝跪地,行叩拜之礼。
值季羡林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季羡林的儿子季承,学生钱文忠、卞毓方等人从外地赶来,和家乡人一起缅怀季先生。
“我是季先生的学生,理应叩拜我的老师。有人觉得,怎么还搞这套封建的东西?我不认为这是封建。
按照中国传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晚辈叩拜长辈,天经地义。”钱文忠说,三十年前,十八岁的他拜师时三跪九叩,这点他从不讳言。当年,季羡林待他亲如家人,那种纯粹的师生关系,至今令他无限怀念。
不忘初心——鲜为人知的明珠之学
因在央视《百家讲坛》讲《三字经》、《弟子规》等儒学经典,钱文忠在大众中知名度颇高,所到之处有学术明星效应。在临清的纪念活动中,人群中不时有人认出钱文忠,要求与他合影,他一一配合。
但对于和他本人有关的提问,他不愿过多回应。
从上海专程赶到临清,他所谈到更多的,是他与季羡林先生之间的旧事。
1984年,钱文忠从上海考到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追随季羡林先生读书。
季羡林先生学生很多。他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并一直在北大执教。如果按学术界规矩,但凡北大的毕业生,只要听过季羡林的课,读过季羡林的书,都可以称季羡林为老师。
在众多学生中,钱文忠有其特殊性。
“当时我年少无知,不知道天高地厚,从高二开始,我就和季羡林先生通信。”季羡林收到这位求知少年的来信时,并不感到唐突,反而因为这个年轻人对语言研究的热情感到欣喜——这个年头,还是有孩子愿意学习梵文的。
钱文忠后来才知道,他所考取的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是自1960年后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第二次招收本科生。
踏进北京大学时,钱文忠十八岁,季羡林七十三岁。钱文忠比季羡林当时的孙辈还要小。因此,学生出入季羡林家中,称呼变得有趣。钱文忠等学生称季羡林为先生,称季羡林的夫人为季奶奶,称季羡林的婶婶为老祖。
钱文忠本科学习时,并没有直接上季羡林先生的课,却因为季羡林对他的爱护,常常出入家门“蹭吃蹭喝”。与今天的学生称导师为“老板”不同,季羡林门下亲如家人的师生关系,润物于无声。钱文忠说,季先生怕耽误学生学习的时间,从不把生活琐事交给学生代劳,他自己七八十岁时,借书都是一个人走去图书馆借来再送还。
“季先生一生学术研究非常广泛,但他有好多学术研究是被迫作的,比如中印文化交流,是因为回国后失去了古印度语言研究的条件,他只能另找饭碗吃饭。
很多领域季先生都作出了了不起的贡献,比如比较文学研究,英文德文著作翻译,甚至马恩全集里,都收录了季羡林先生的译作。此外,还有散文创作、印度史研究、中国文化史佛教史研究等领域,季先生都成就非凡。
”钱文忠说。但是,回溯到季羡林先生的青年时代,他最早从事的、也是一生最愿意做的学问,是当时欧洲学术界最困难的学问:印欧古代语言的研究,其稀有和艰深,堪比洋人学问皇冠上的明珠。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钱文忠踏入北大校门时,下决心继承季先生年轻时代最看重的学问。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跟季先生之间有特殊的师生感情。当年招收的八个本科生,只有他目前还从事着相关学术研究。
钱文忠说,他继承了季羡林所研究学问中最重要的一套学术。他一直称自己是季门弟子,不是一般的学生。
“我本人乏善可陈,但是,我有幸从十八岁起就一直追随季羡林先生,在季羡林先生门下求学。
这是我个人生命史上最为珍贵的一页。”在人生的学习阶段,得遇良师,钱文忠自认是一生的幸运,现在回想起来,往日情景犹在眼前。
故土情浓——“你有没有见过北方的农村”
季羡林先生离开我们已满五周年。
五年前的7月11日,钱文忠正在中央电视台录制《百家讲坛》。
“我刚刚换完衣服登上讲台,手机还没有关,有一个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文忠,你现在方便不方便接受采访?我说不方便,马上要录像。
他说:很紧急,老先生走了。”
钱文忠目瞪口呆。他马上跟中央电视台的导演说,今天的录像必须取消。他换了衣服就赶去医院。
想起五年前的这一幕,钱文忠心里非常难受。
他原打算当天中午去医院探望季先生。不要说学生弟子料想不到老先生的离去,就连季羡林先生自己都不认为一百岁能挡得住他的生命。
“按照中国传统风俗,季先生虚龄已经一百岁了。
在我们眼里,季先生是个奇迹,我们始终相信,不能用常理来判断季先生的生命轨迹。季先生七十多岁时,我陪着他骑自行车,从北大一直骑到琉璃厂,来回两个小时不在话下。我们盲目乐观,甚至相信,季先生活到120岁都是正常的。
”钱文忠说。
季羡林去世后,按照医学程序,北京301医院对他进行了病理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季先生的血管中没有任何杂质,但血管壁已经薄到透明,这是因为老人年纪太大了。
在季羡林走过的将近百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在家乡临清的时间不过六年。
但他对故土的深沉眷恋却伴随了他一生,这给钱文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1年,季羡林九十大寿,钱文忠第一次陪季先生回到老家临清。
他清楚地记得,车到了官庄村口,季羡林要求下车步行。那天刚下过雨,雨水经太阳烘烤,村路格外泥泞,一不小心鞋都会被粘下来。钱文忠和倪萍两人一左一右,一起扶着季老先生,深一脚浅一脚往官庄村里走。
“老先生刚进官庄村,眼睛就含了泪。
他问我:文忠,你是南方人,你有没有见过北方的农村?”
钱文忠知道老先生想说什么。他想说:我生长在这里,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的祖父母葬在这里,我的父母,特别是魂牵梦萦永远忘不掉的母亲,依然葬在这里。
那一刻,钱文忠感受到他对家乡的由衷的眷恋。
齐鲁重教——
在没有梦境的年代实现梦想
五年过去了。今天再看季羡林,这样一位文化泰斗、文化标杆式的人物,我们又看到了什么?
“我想,他的一生,大致的轨迹正是实现中国梦的一生,他是中国梦的标志性人物。
”钱文忠说。他回顾了贯穿季羡林一生的中国梦的力量。
生于官庄,一个曾经富有而后破落的家庭,季羡林最初想象不到自己能走出这片土地。
他的母亲这一生走过的路,就是从娘家到官庄的一段路,走回来又走回去,一辈子没有走出这段路。季先生能想象自己会走多远吗?
但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季羡林的叔叔有机会到了济南,当时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大的变动。
那时候,有的人因生活所迫,有的人因不愿意在家呆着,愿意出去看更大的世界,看更精彩的世界,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为自己闯出一片天地。
季先生的叔叔就是那个时代的成功者。
季先生的叔叔没有儿子,按照旧时传统,侄子过继来就相当于儿子,叔叔就相当于父亲,于是叔叔把季先生接了出去。少时的这个偶然,让季羡林的生命轨迹一下改变了。
季羡林被接到济南,读书的环境大为改善。在济南新育小学,他开始学英语。当时的小学课堂,并不提供英语课程。恰巧一个小学的老师,他会英语,他愿意在课后开班,教学生学英语,但是要额外收费,每个月一个学生三块大洋。
这是很大的一笔钱。季羡林的叔叔,本来很保守,但这次毫不犹豫,他重视教育并且很有远见。
季先生曾对钱文忠谈到自己学习语言的经历,并且写过一段文字,讲当时的痴迷:
“每次回忆起学习英文的情景时,我眼前总有一团凌乱的花影,是绛紫色的芍药花……白天走过那里,紫花绿叶,极为分明。
到了晚上,英文课结束后,再走过那个院子,紫花与绿叶化成一个颜色,朦朦胧胧的一堆一团,因为有白天的印象,所以还知道它们的颜色。
但夜晚眼前却只能看到花影,鼻子似乎有点儿花香而已。这一情景伴随了我一生,只要是一想起学习英文,这一美妙无比的情景就浮现到眼前来,带给我无量的幸福与快乐。”
即便到了济南,季羡林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去德国留学。
他中学毕业时,曾经想到要去考取邮局,找一个铁饭碗,居然没有考上。正因为没有考上邮局,他才去考北大清华。
季羡林考清华,数学只考了四分。这个成绩其实并不罕见,由于教育条件、兴趣爱好的差异,当年数学成绩差者大有人在。
钱文忠家族的长辈钱伟长,后来是著名的物理学家,他考清华时,数学和英语都是零分;钱锺书先生数学是十五分;吴晗先生数学是零分。“但是,他们居然都能考进清华,清华居然接受了这样的学生。
”钱文忠说,这为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实现梦想打开了一扇大门。
重教的传统,是齐鲁大地宝贵的文化传统。季羡林先生的梦想才刚刚开始。季羡林读清华时,并不富裕的老家清平县政府,为这个少小离家的学子,每年提供一百五十块大洋的奖学金。
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季羡林的母校省立济南高中,邀请他回到母校当语文老师,开出了每个月一百六十块大洋的高工资。
回到济南,家人团聚了,既有社会地位,又有经济保障,按理说,可以安安静静地过下去了。
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突然出现在青年季羡林面前。刚工作不久的季羡林,还没有什么积蓄,要放弃这个饭碗,再花上一大笔钱,远行万里去留学,家庭能接受吗?
出乎季羡林的预料,叔叔表示愿意倾家荡产举债全力支持。
离家时,思绪万端的季羡林把眼泪压在肚子里,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他眼前一闪。彼时家国皆窘迫困苦,还没有做梦的条件,但在那个没有梦境的年代,他一步步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到了季羡林的晚年,特别是“文革”以后,季羡林真正地在补做自己的中国梦。
“当这个民族一旦有了做梦的条件以后,在能够展开想象的时代,季先生完全用自己生命,用所有的努力,去实现他的梦想。
他想补自己最好的壮年时代失去的时光,他想补自己回国后,没有完全实现的学术报国的梦想,他想让东方学的正统能够回到中国,使中国的东方学,像他在德国留学时梦想的一样,能够占领世界的鳌头。
他一直在补做这个中国梦。”
钱文忠说:“中国百年来,一直做着一个梦。这个梦盼望着积弱的祖国能够富强,盼望着每一个人的愿望能够成为事实,希望个人的生命能够融汇到整个民族的生命当中。
我想,季先生这一辈子,真正是实现中国梦最好的注释。”每个行业都有中国梦,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也有中国梦。今天中国文化的梦想,希望重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核心价值,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高扬于世界,成为全世界全人类认可和共有的文化财富。
季羡林就是中国梦的代表人物,他的地位有待重新被国家和民族所认知。
无条件爱国——
顺境逆境都不放弃
7月10日,走进临清季羡林纪念馆,迎面的白色大理石碑上镌刻着季羡林生前名言: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是爱国的。
钱文忠说,在今天这个价值观多元化、高度自由、高度开放的年代,重新认知季先生的爱国情操,显得格外重要。
“今天,有很多学子、很多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国家有意见。确实,今天中国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有些甚至非常严重,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能构成我们不爱自己国家的理由。
相反,我们这个国家的问题越严重,我们越要爱它,越要努力去解决它。因为我们依然要生活在这里。哪怕去移民,我们在海外的子孙后代,也要知道自己的祖先来自哪里。”钱文忠说。
今人故人两相对比,季先生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过他对祖国、对故乡的热爱,他的单纯的热忱,尤为可贵。
在钱文忠与季羡林的交往中,季先生不管多大岁数,只要谈到自己的母亲,都会流下眼泪。在德国的日子里,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多么想吃家乡的花生米。
他想着祖国,想着家乡的味道。
回国以后,季先生的境况起初非常顺利。作为一个贫农出身的归国知识分子,他曾当过北京大学工会主席,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完美的学界形象。理所应当,他胸怀学术报国的梦想。
顺境中如此,逆境中又如何?“文革”中,季先生几乎被殴打致死,多次爬着回家。打他的人里面,有他非常尊敬的学校工作人员,也有他深爱着的学生。
这些人他都知道是谁,但是他一辈子不说。
当年在冤屈下,季先生曾经打算自杀。支持他活下去的,是他深爱的国家和事业。当他被安排到学校宿舍看门时,他就像普通门卫一样,天天给人收信、叫公用电话。
境况如此,他居然每天从家里抄十行《罗摩衍那》的梵文,带去门岗翻译。他曾对钱文忠忆及此事,说:“不然,我坐不住。像我这样一个人,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些什么呢?那就是学术的事情。关于学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梵文,我怕把梵文忘了……”
“文革”以后,有人来调查当年的打人事件,季先生说,我都忘了,我记不得是谁了。
他依然爱着这个国家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季羡林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声誉,令人尊敬。
在最权威的梵文词典中,有数个词条缀有季羡林的名字,因为这些字词他是全世界第一个搞清楚的。不仅如此,他对古印度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贡献亦非常巨大。
学术上的研究,有可能被后来者超越,但钱文忠强调,季先生作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历史进程中一个历尽艰辛的梦想者,一个敢于追求的造梦者,一个坚持把梦想变成现实的人,这样一个中国梦的标志性人物形象,永远不可能被超越。
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学生,钱文忠坦言,今天他自感惭愧。
“季先生的精神和人格,以及他对国家的爱,我会勉励去追寻。今天追思季先生,我们更要牢牢记住自己的梦想,牢牢记住我们这个民族的梦想,去做一些自己能做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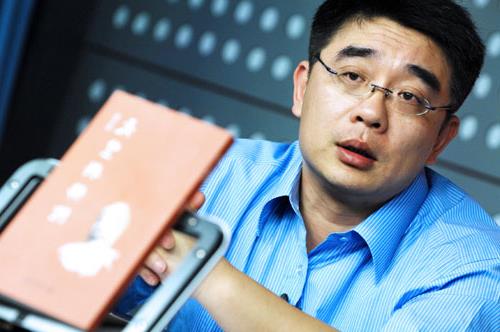







![钱壮飞子女 钱壮飞的妻子张振华]钱壮飞张振华](https://pic.bilezu.com/upload/1/4e/14e41086c49d4ec4613132420d11c019_thumb.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