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师郑宇 “中国人对摄影师恶意最少”
[曾长期关注南非种族隔离和民主运动的玛格南图片社摄影师伊恩·贝瑞来中国不下20次,他最喜欢中国的一点竟然是“变化快”]
伊恩·贝瑞(IanBerry)很喜欢女人。在上海摄影艺术中心接受采访时,一位虔诚的男粉丝为了与他交流,足足等了一小时,但当他们结束寒暄,粉丝要求合影时,他却指了指一旁的两个姑娘,故作严肃地说:“不好意思,她们比你好看,我想先和她们拍。”
作为玛格南图片社的摄影师,伊恩曾长期关注南非种族隔离和民主运动,并因记录南非沙佩维尔(Sharpeville)和平抗议引发的暴力事件而成名。由于拍摄敏感社会议题,他常常经受皮肉之苦甚至牢狱之灾,有些旧疾至今没有痊愈。
他的另一组代表作品是受罗伯特·弗兰克(RobertFrank)《美国人》(TheAmericans)影响而拍摄的《英格兰人》(TheEnglish),与前者不同的是,他有计划地拍摄了整个英格兰岛,而且有意识地将各个阶层——工人阶级、中产阶级和贵族的日常生活都容纳其中。
伊恩的情感经历也和工作经历一样丰富。
有一次,他接到去美国南部拍摄的任务。“我遇到一个女人,与她共度了两个礼拜,她有那种奇特的得克萨斯口音,这本应该像伯明翰口音一样可怕的,但是和她结合在一起却那么美好!”伊恩回想起来至今难掩兴奋:“两周之后,我几乎要喜欢上得州口音了,某种程度上,口音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东西。”
“我结过三次婚,”他又主动分享道,“第一个老婆是波兰人,第二个是德国人,我自己也长期生活在国外,这让我对不同国家人的性格有了更多认识,也能够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英国人。”也许正是因为从未停止过享受生活,伊恩镜头下的世态人情,才那么鲜活生动。
喜欢改变的老人
伊恩来过中国不下20次,这位已经82岁的老人,最喜欢中国的一点竟然是“变化快”。2014年,他听刘香成提起创办上海摄影艺术中心的计划,心想也许等中心建成,应该来办一次展览。“我问刘,筹备期大概是几年,他反问我,几年?明年就开了!”结果他与布鲁诺·巴贝(BrunoBarbey)的“玛格南大师”双人展,也在中心开幕一年之内亮相了。
伊恩第一次来中国,是受总部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周日时报》(SundayTimes)委约拍摄深圳专题。那时候,大批工厂开始撤出香港,向深圳转移,因为内地的劳动力更便宜。“当时深圳只是个小村子,二十几年时间过去,它已经变成了超级大都市。在你的生命中,能够真切地经历一些人事物的巨大改变,是一种很棒的体验。但是在伦敦,街道和建筑跟我的曾曾曾曾祖父活着时几乎没有差别。”
后来为了拍摄全球水问题专题,他又沿着长江来回跑了好几趟。这么多年来,在伊恩眼里,中国唯一没什么变化的,是人们对镜头的态度——要么完全不介意被拍,要么装作没看见,最不济也只是默默躲开。“美国人会和你谈肖像权问题,现在连英国人也开始强调‘私人领地不准拍摄’了。
”在为年轻的中国摄影师点评街拍作品时,伊恩鼓励他们大胆地去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用中长焦镜头远远地拍一张美丽的脸,因为中国已经是对摄影师恶意最少的地方了。
由于一切变化太快,伊恩很想在中国住上一段时间。“年轻时你很难注意到事物的变化,你只关注与自己有关的东西;当你老了,离开了一段时间再回来,才会对周围巨大的变化感到震惊。”最近他拿到了中国的两年签证,每次可以停留90天,为此他十分高兴,计划离开自己经常拍摄的城市,到山区走走——趁膝盖的伤还不至于影响行动:“能待在这儿太好了。这里一切都那么年轻,太好了。我喜欢改变。”
“不是受伤多就是好摄影师”
“南非,德兰士瓦,沙佩维尔。1960年3月21日,星期一。警察向村民开枪,村民们用外套挡住头部来躲避子弹,纷纷逃离村子中心。”
在这张令伊恩爆得大名的作品面前,总是聚集着最多参观者。然而他自己却觉得这是一张糟糕的照片,充其量只是合格的新闻摄影而已:“那之后很多人都说我拍得很棒,可当时我根本只是个运气不错的孩子,尽管作为摄影师你必须有点运气。”
当年,伊恩和一大批外国记者都得到了沙佩维尔有人开枪的线报,但因为白人进入南非的种族隔离区是需要许可的,他们最初都在村口等着。直到一队装甲车开进隔离区,他们也纷纷跳进车里尾随了进去。开了大约一百码,就有官员过来要求他们离开,否则逮捕他们,大部分车子掉头走了,剩下的车子继续开了一会儿,官员又出来威胁了一次,就只有伊恩所在的那辆车还坚持向前开。
车子最终停在距离警察局的围栏不远的地方,伊恩爬上围栏,看到警察和抗议人群都很安静,估计不会有什么事发生,于是掉头向停车的方向走去。
就在那时,警察开枪了,人群突然四散狂奔。“我身上只有两台徕卡相机,一台装配标准镜头,一台是广角镜头,只是本能地对着朝我跑来的人们按下快门。同时我意识到南非警察最恨有激情的记者,于是也很快跳上车离开了。”
1985年,在好望角,伊恩又一次报道警察强硬介入有色人种抗议示威,这次他运气稍微差了一点,被警察逼到小巷里打断了三根肋骨。不过他强调:“不是受伤多就是好摄影师,我就认识一个经常受伤的摄影记者,他的照片真是无可救药,受再多伤也没用。我告诉你,有些记者经常被枪击是因为他们经常磕嗨了!
说起自己被捕的经历,伊恩也完全是调侃的语气:“有一次我在中非共和国因间谍罪被捕,但实际上,只是你愿意付多少钱的问题。你知道,我们英国人不擅长贿赂这件事,给多了怕他们更贪,给少了怕报复。同一个牢房里的犯人倒是挺友好的,但是食物,真让人想死!我比较喜欢意大利的监狱,食物很不错,咖啡更棒。”
和玛格南的“婚姻关系”
伊恩是被布列松钦点加入玛格南的,但是五十多年中,他大概有一半时间都在考虑退出。
报纸和杂志的黄金时代,也是玛格南图片社的黄金时代,与伊恩一同办展的布鲁诺·巴贝说,那时候摄影师就像皇帝一样被媒体捧在手心,一组照片常常被多本杂志争抢。《英格兰人》则同时得到伦敦Whitechapel画廊和一家德国画廊的支持,令伊恩有足够的资金持续拍摄三个月。
他说,以往向玛格南报选题,玛格南一般都会预支几千块钱,让他先去看看,究竟要不要正式拍,等实地了解了情况再说。而如今他们只祝你旅途愉快,不再提前提供经费,而拍回来的照片,也不一定能卖。“现在的市场环境,对年轻摄影师来说太困难了。”
就像所有机构一样,玛格南也变得越来越大,同时面临分化。“玛格南曾经是独立摄影师显而易见的选择,但是时代改变了,有的摄影师更愿意与画廊签约,也有越来越多摄影艺术家(PhotoArtist)加入并改变了玛格南。”
玛格南是为所有摄影师拥有的,每一位成员都拥有自己的股份,共同承担图片社的日常支出,都知道彼此在做什么、赚多少钱,也都可以影响图片社的决策,但在伊恩看来,这有时候反而使事情变得令人困惑。他曾想雇两个助手自立门户,也考察过别的图片社,却始终没能下定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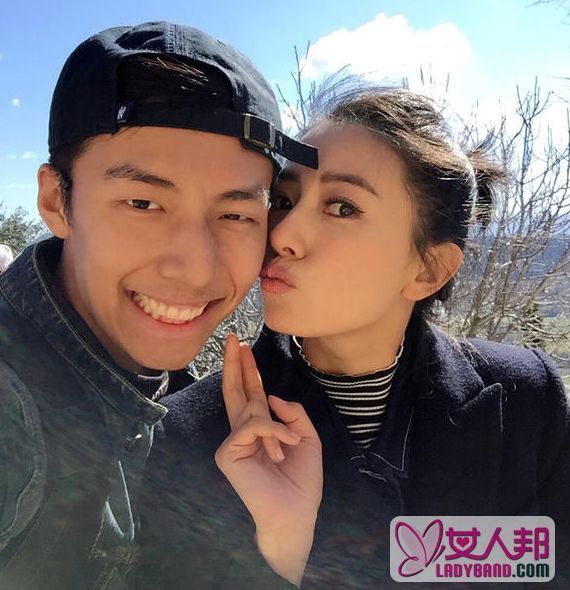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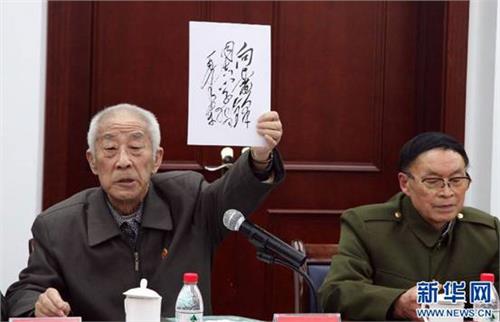
![>周思源周怀宗 [小摄影师教学反思]周思源[摄影师]:周思源[摄影师]](https://pic.bilezu.com/upload/a/83/a8331537f456835f8a2fa03b16a195ec_thumb.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