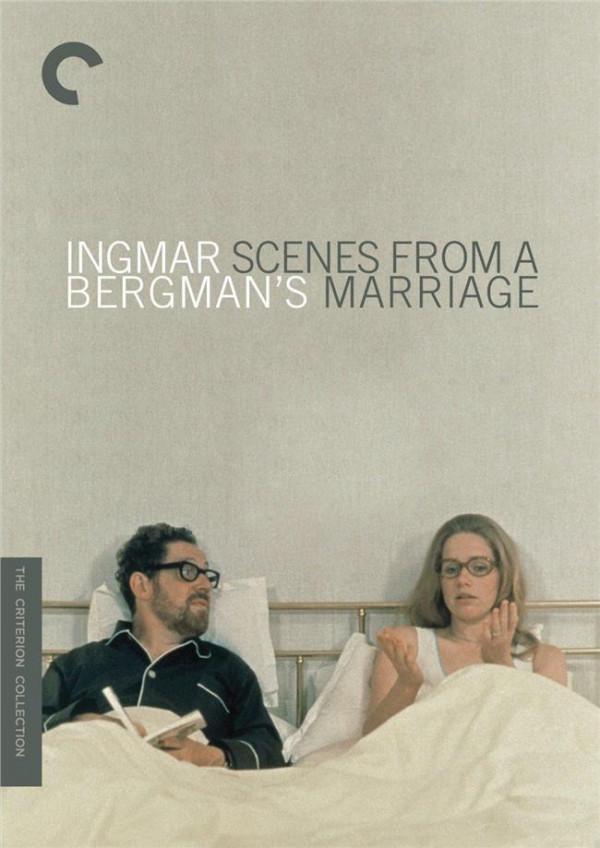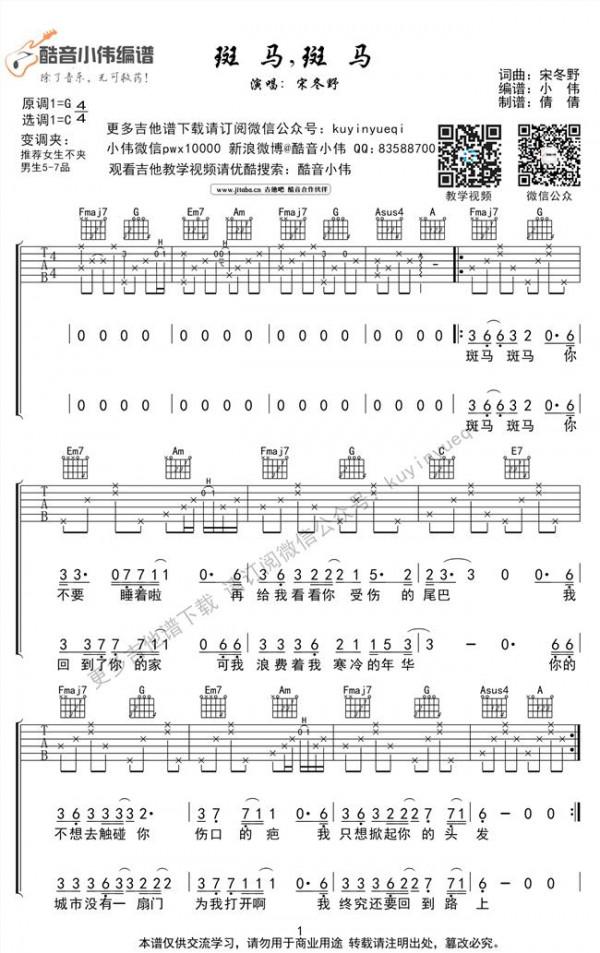野草莓伯格曼 《野草莓》:伯格曼的“阉割焦虑”(李若水)
影片开始就是主人公伊萨克的内心直接独白,强烈而明显的意识流色彩,关照内心。对于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来说,这种在死亡面前直面自己的真诚,可以称之为忏悔。
已经摸着生命尽头的伊萨克,在一个获取荣誉的日子的清晨梦到了死亡,故事从此开始,于是作为一种诚实的回望——忏悔,就此蔓延开来。 一、被逼迫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转移 伊萨克决定自己开车去兰德,而不是原定的飞机旅行。
他是为了用自己最后不多的时间来抚摸一下这一生,哪怕仅仅是抚摸。
于是,他来到了人生前二十年的每年夏天都会去的那所房子。这所房子承载的是他的童年,但最重要的其实仅仅是一个姑娘——曾经的未婚妻“萨拉”。 就像每个精彩的故事都会与一个姑娘有关一样,伊萨克的故事也是这样。
伊萨克在得到死亡的托梦后,首先的反应就是来寻找心中的萨拉。萨拉之于伊萨克远远不止是“永恒的情人”那么简单,实际上,萨拉曾经拯救了伊萨克。
从影片的暗示中,我们可以得知伊萨克自幼缺失父爱,影片只提到了他的母亲。
但是从他母亲晚年的孤独以及对其众多子女的描述中,使我们可以想象到伊萨克小时候并未得到多少母爱。然而,俄狄浦斯情结的存在是没有人能够避免的,伊萨克也是。但是,他无法在自己母亲身上实现这种情结的完整发育,她的母亲太冷漠,于是俄狄浦斯情结顺其自然的转移到了其他异性身上。
对于伊萨克来说,这个异性就是萨拉,所以说,萨拉对伊萨克的生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她帮他完成了生命的成长,帮他度过了童年时期恋母危机。
某种程度上,也是萨拉激励了伊萨克对于知识的兴趣,才有了他后来医生事业的成就。当然,这一点电影没有交代,但是切·格瓦拉曾经承认过,他在年轻时的滔滔不绝,只是因为有个姑娘在场,他想让她看到。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革命是由爱情引起的”。
这种来自异性的不自觉的激励,肯定帮伊萨克度过了年轻时的自我否定的危机。 但是,悲哀的是,伊萨克的俄狄浦斯情结并没有最终完成转移。
萨拉被他的堂兄西格弗里德抢去了,伊萨克失去了心爱的姑娘,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是一种耻辱,他被再次“阉割”(伊萨克在此之前已经被“阉割”过一次了,下文中会提到)。
这次的“阉割”是致命性的。我们在影片中压根就没有看到任何关于他妻子的描述,可以想象他婚姻的失败;他与管家之间的隔膜;与儿子之间的隔膜等一切他在人际方面的失败,表现的是他的冷漠,他的儿媳也肯定了伊萨克与其儿子在这一点上的相同,但是冷漠的背后隐藏的是他的“阉割恐惧”,冷漠只是一种孱弱的掩饰罢了。
这种“阉割恐惧”,他一生都未能克服,所以他的一生都未能真正地融入身边的亲近人中去。这个时候他的冷漠,反而使他显得可怜。
但这归根结底是由于伊萨克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失败转移而引起,对母亲的依恋、对萨拉的爱,都没有得到回报。
这对于少年的伊萨克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很大程度上,伊萨克自己对此无能为力,他是被逼迫的。 二、被阉割的——男人一生的对手是父亲 弗洛伊德认为,男性在童年时期,由于恋母情结,会被父亲以阉割相恫吓。
此后,男人总是处于被阉割的焦虑中,害怕失去阳具,当男孩儿发现女孩儿没有阳具时,得到了阉割证实,这就是“阉割焦虑”。
这是男性一生中心理发生重大转折的关键。由于担心被阉割,某些男孩儿会有“弑父”的念头,或者与父亲有思想、言语甚至肢体的冲突。 我们在电影中看不到有关伊萨克父亲的直接描述,这种剧情设计其实是伯格曼自己内心的写照。
伊萨克的父亲的缺失,暗示了伯格曼内心中对于父亲的怨恨看法。伯格曼曾在70年代接受瑞典电视台采访时说:“一种巨大的怨恨建立在我和父亲之间。
有一天,他打了我。”伯格曼将自己的弑父冲动演化成了电影中父亲形象的缺失,他通过电影达到了“弑父”的目的。 伊萨克的第一次“阉割”来自于父亲,所以这位电影中根本没有的人物角色——伊萨克的父亲,反而是最重要的角色。
是他给予童年时的伊萨克强烈的阉割焦虑,这种焦虑困扰了伊萨克一生。
伊萨克之所以失去萨拉,根因在于童年时来自父亲的阉割焦虑,使他没有足够的作为男人的勇气。他已经习惯了以冷漠和自私过活,这怎么能够抓住一颗萌动的少女心呢?伊萨克后来对于自己妻子的出轨,反应冷漠,这是阉割后的麻木。
他以冷漠试图告诉外人,他不在乎,其实他很在乎。冷漠背后是孱弱,外表的坚硬恰恰是因为内心太柔弱。 伊萨克一生都没有走出“阉割焦虑恐惧”,在面对男人一生的对手父亲时,他完全失败了。
他父亲的早已去世,更使得伊萨克在有生之年失去赢得父亲的机会,也就永远失去了走出阉割焦虑的机会。
当“弑父”因对象的缺失而不可能实现时,出路在哪?伊萨克在失去父亲的那一刻,被第三次“阉割”了,这也是最彻底的一次“阉割”,因为他再也没有取胜的机会。所以,伊萨克通过梦来寻找他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无法找到的——父亲,他试图通过梦来克服阉割焦虑,得到父爱。
由于伊萨克内心中父亲形象的缺失,所以他并没有学会如何做一个父亲,这就直接导致了伊萨克自己作为一个父亲的失败。
这种失败我们能从他儿媳转述的伊萨克儿子对他的失望评价以及儿子像伊萨克一样的冷漠中得到证实。伊萨克的儿子艾瓦尔德作为一个父亲,承袭了他父亲的冷漠,而阉割焦虑在艾瓦尔德身上体现得更加彻底,他干脆就不想成为一个父亲,不想去给予父爱,所以他要消灭父爱的给予对象——儿子,因此他反对妻子生下孩子。
而伊萨克听到儿媳说,儿子不喜欢他时,特写镜头中正在开车的伊萨克满脸吃惊与无奈。
他后来见到儿子时,试图弥补,但是这种弥补的努力已经太过无力。 三、伯格曼的内心 伯格曼在《伯格曼论电影》中这样说到:“驱使我拍《野草莓》的动力,来自我尝试对离弃我的双亲表白我强烈的渴望。
在当时我父母是超越空间、具有神话意味的,而这项尝试注定失败。多年后,他们才被转化为普通的人类,我从儿时就怀抱的怨恨也才逐渐烟消云散。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和睦相处,彼此融洽。”这种对父亲的怨恨心理情结一直贯穿着伯格曼的电影生涯。 在《魔灯——伯格曼自传》中,他自己说到:“今天,我伏在童年时的照片上,用放大镜仔细端详母亲的面容,我试图重温那长久流逝的情感。
是的,我爱她。照片上的她非常迷人……我4岁的心灵里充满了像狗一般的忠诚。
然而,我和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很单纯。我的忠诚使她烦恼和焦躁。我亲近的表示和强烈的情感爆发困扰着她。她经常用冷漠讥讽的话语赶我走,我只能怀着愤恨和失望的心情去哭泣……我不久便开始试着以自己的行为去逗她高兴,去迎合她的兴趣。
病痛能立即引起她的同情心。让自己浸泡在永无休止的病病中,这的确是一条痛苦的,却真正能引起母亲关怀和体贴的捷径。另一方面,由于母亲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护士,把戏很快就被戳穿,我受到当众惩罚。
” 我们可以看到童年的伯格曼有着多么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但是他的母亲却没有给予他足够的爱。
在俄狄浦斯阶段,父位具有了象征功能,代表着一种社会性的压制力量。而恰恰伯格曼的父亲则对他非常严厉,伯格曼曾因为像尿湿床这样的过错而被锁在黑暗的衣橱中。他的父亲是一位地位极高的牧师,位至瑞典国王的专属牧师,在伯格曼心中就是他的上帝,像神一样使人敬畏。
可以想象,来自伯格曼父亲的“阉割焦虑”曾多么强烈地困扰着伯格曼。在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宗教传统的家庭,伯格曼后来承认竟然在八岁就已经丧失了信仰。
伯格曼一生经历了五次婚姻,与七八位女性关系密切,这种复杂的的情感关系背后其实是伯格曼在异性中不断寻找转移俄狄浦斯情结的最合适对象,并试图克服“阉割焦虑”的尝试。 “每当我心神不定或忧伤的时候,我总是以回忆我的童年来求得平静。
”[ 英格玛·伯格曼著.《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上)》第203页.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电影的最后伊萨克再次这样做了,他做了一个梦并使他“感到几分轻松”[ 英格玛·伯格曼著.《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上)》第204页.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梦里是和谐的童年,有父亲、有母亲、也有萨拉……最后,伯格曼通过电影才得以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阉割焦虑”,通过对父亲、母亲的刻画,在某种意义上战胜了父亲,达成和解。 参考文献: [1]英格玛·伯格曼著,韩良忆译.
《伯格曼论电影》[M].远流出版社,1994 [2]英格玛·伯格曼著.
《夏夜的微笑——英格玛·伯格曼电影剧本选集(上)》[M].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3 [3]英格玛·伯格曼著,张红军译.
《魔灯——伯格曼自传》[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8 [4]弗洛伊德著,赵蕾、宋景堂译.
《性欲三论》[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10 [5]严泽胜.《穿越“我思”的幻象——拉康主体性理论及其当代效应》,东方出版社,2007,7